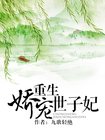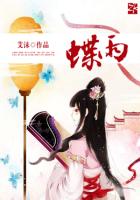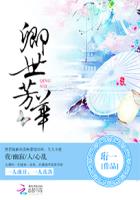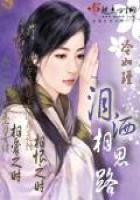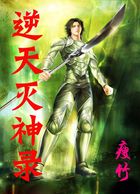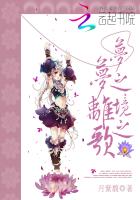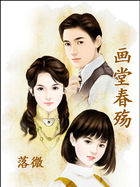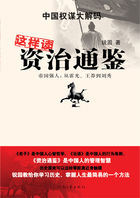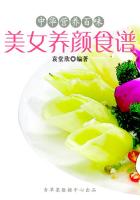柳逸被腰斩的当天,步摇因极度悲痛而数次昏厥。而我也实在不忍心去目睹那惨绝人寰的画面,柳逸就在一群陌生百姓的围观之下被残忍地处决。柳逸死后,长安的空气中都似有一丝淡淡的血腥味,而且一连两天都是一片凄风苦雨,像是在哭诉着这起爱情悲歌。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为柳逸的惨死而默默垂泪。高阳公主的这起丑闻成为贵族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与百姓们街谈巷议的焦点。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房家也因此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柳逸死后,皇上单独召见了父亲房玄龄,善加抚慰了一番,并表示要更加器重房家昆仲。而父亲只是一味说“犬子遗爱无德无能,辱没公主,公主情有可原,请皇上收回对公主的责罚。”于是皇上恩准,恢复步摇的俸禄和自由。父亲虽然得到皇上的安抚,却依旧每日愁容满面,心情沉重,时常唉声叹气,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
二哥房遗爱作为尴尬中的尴尬,自然成了很多人暗地里嘲笑奚落的对象。然而他却不以为意,似乎这一切和他毫不相干。他唯一的抱怨,是出了这等事使他不能再像往常那样肆无忌惮地到处游荡玩猎,飞鹰走狗。如果不是还有这点不同的话,他简直和平日一点变化都没有了。心死之人果然是六根清净,四大皆空。和柳逸比起来,他的心境或许更像个出家人。
大哥房遗直,是“当之无愧”的刽子手。毫无疑问,是他在得知步摇将宝枕送予柳逸后,用某种手段将宝枕弄到手,然后指使手下扮作“盗贼”连同宝枕一起“主动”落网,遂将步摇的私情牵引出来。如果不是因为李恪的道高一丈而使其漏出了马脚,几乎可以称得上天衣无缝了。然而房遗直还是令人小觑不得,他居然有办法让“盗贼”这个关键人物永远地闭上了嘴。加之皇上一怒之下处死高阳的贴身侍女,所有可能知情的证人全部丧命,无意中竟帮了房遗直的大忙。
无辜者的惨死掀起的血雨腥风却不能让房遗直有一丝的良心不安。他反而摆出一副处变不惊的架势,越发的“兢兢业业”忙于公务,俨然是房家顶梁柱的形象,众人对他纷纷投以同情的目光,甚至为这位官场“明日之星”有可能受牵连导致仕途波折而唏嘘不已。所谓欺世盗名,想必也莫过于此了。没想到世间真有这般道貌岸然之人。
而房遗直这个貌似无辜的刽子手,却阴差阳错地成为这起惨剧的最大受益人。高阳公主的丑闻令皇上感到自己亏欠了为自己效忠半世的老臣,为了安抚父亲,也是作为补偿,遂将更大的荣耀加诸房家长子之身,诏令晋升房遗直为银青光禄大夫,房遗直由原来的从四品一跃成为从三品。房遗直阴谋告发步摇,不仅宣泄了一己之私愤,还收获了这份意外之喜,真是颇为讽刺。想必此时的房遗直一定得意忘形到了极点。
公主府一片愁云惨雾。在柳逸罹难之初,步摇终日以泪洗面,神情恍惚,憔悴不成人形。思之再三,我还是将步摇成婚前夕柳逸让我代为转交的那幅画交给了步摇。谁能想到,这幅画竟成了步摇所拥有的柳逸的唯一遗物。
步摇捧画在手,泪如雨下:“墨姐姐,是我的疏忽大意害死了柳逸!”
我尽可能地安慰着步摇:“这不能怪你,是房遗直诡计多端,防不胜防。我们都是君子,他是小人,越是小人,越喜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连恪哥这样聪慧机敏的人也一时间都奈何不得他。”
步摇抬起泪眼,茫然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悔不听三哥之言。不然,柳逸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我默然。
步摇愤恨不已道:“我不杀房遗直,誓不为人!我要报仇雪恨!”
我劝道:“那个受指使的盗贼已死,皇上又处死了兰香她们,房遗直如何得知宝枕之事恐怕一时难以查明。下一步怎么办,还是听恪哥的安排为好,公主不要轻举妄动。”
自那以后,步摇时常对画饮泣,追思柳逸。也只有在看画的时候,她的眼中才会显现出一丝幸福的光芒,在她的身上才能依稀看到曾经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公主的影子。除此而外,她完全像换了一个人,变得深沉冷漠,寡言少语,阴冷的目光中时时闪现着复仇的寒光。
贞观十八年就要过去了,距离皇上拟定的出征日期越来越近。此时,朝野盛传,皇上已经着手草诏任命李恪为征讨大将军。看来,李恪随驾出征几成定局。
“恪哥,皇上真的会要你随驾出征辽东吗?”我不无担忧地问李恪。
李恪的回答并无一丝犹豫:“皇命一旦下达,我会全力以赴。”
我知道无法打消李恪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好试探地问道:“此一战,恪哥胜算几何?”
李恪露出成竹在胸的淡淡笑容:“我对辽东的局势与战术运用已经有十足的把握,务求一战成功,岂有不胜之理。”
也许是我将满腹的心事都写在了脸上,李恪抬起我的脸庞,无限温情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在担心些什么。虽说战场瞬息万变,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但是,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我会多加保重的。”
这番类似话别的言语让我忍不住掉下眼泪。
“如果我果然离京出征,反倒是你留在长安要多加小心,在房遗直面前要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还有高阳,要劝她暂且忍耐,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一切等我回来再作定夺。”
我点点头:“恪哥,你放心,我会万分留意的。”
李恪抹去我眼角的泪水,含情脉脉:“如果我能大胜而归,届时一定向父皇请旨赐婚,娶你做我的王妃。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知道吗?”
一听此言,我羞涩万分地扑入李恪的怀中,破涕为笑。
几天后,诏令下达,李恪果真被任命为征讨大将军,太子李治为监国,父亲房玄龄留守长安权全掌管朝中政务,长孙无忌与李绩、李道宗等众将随驾,岑文本负责督办粮草事宜。大军定于贞观十九年三月开拔。
“嗖嗖嗖──”
吴王府的庭院中传来一阵风生水起的响动。我闻声而至,眼前的景象使我惊呆了:原来是李恪在全神贯注地舞剑。一身白衣的李恪敏捷快速地舞动着寒光闪烁的利剑,剑与人浑然一体,充满了力的美感。一招一式尽显优雅,潇洒飘逸中不失凶狠有力。确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英雄气概。
当李恪定格在最后一剑时,我忍不住击掌喝彩道:“人言吴王剑术甲天下,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也许这样的赞扬他已经听的太多太多,而丝毫不能让他更满足,哪怕是出于第一次大饱眼福的我的口中。他不动声色地一手持剑,一手轻轻拂着剑身,淡然道:“对风而舞,又有何用?”
李恪一向都是喜怒不形于色,他的话分明显示他此时心境不佳。
我拿起岩石上的剑鞘,递给李恪:“墨儿知道恪哥志向高远。恪哥出征之日,就是宝剑出鞘之时,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也算是大慰平生了呀!”
李恪无言地接过剑鞘,“噌”地一声,将宝剑用力收入剑鞘,挂在腰间。那绝然的表情与动作,让我心中生出一种不安的预感,莫非李恪正为何事烦恼?
这时,小兴进来禀报:“殿下,纥干承基求见。”
“让他进来。”
一脸焦躁之气的纥干承基大步流星地来到庭院中,对李恪行了一个军礼,猛地看到一旁站立的我,这个曾经差点杀死我的莽汉吃了一惊,一脸狐疑,不明白我这个险些作了他刀下鬼的人为何现在却成了李恪的座上宾。
我也感到很不自然,尴尬地朝他点了点头,算是见过。
“纥干承基,你来所为何事?”李恪对部下永远是一成不变的冷峻威严。
纥干承基躬身答道:“殿下可曾听说,军中──”
话说了一半的纥干承基忽然闭口不言了,他疑虑地看了我一眼,很明显是不希望有我在场。
李恪皱眉道:“为何这般吞吞吐吐!?”
纥干承基有些犹豫着说道:“可否请殿下屏退左右......”
李恪打断了纥干承基的请求,正色言道:“她无需回避,你但讲无妨。”
纥干承基见状,忿忿不平地禀告道:“殿下是否已经听说,现在军中谣言四起,说皇上处死李君羡实则是因为君羡有拥立吴王为帝的意图,还说殿下您因为不满太子之位旁落,曾秘密结会李君羡,预谋逼宫谋反,弒君篡位!还有谣传说您对李君羡之死耿耿于怀,还时常接济他的家人,并暗中对皇上怨言不断等等。殿下,您出征在即,现在却传出这般不堪的谣言,如何是好?”
待纥干承基气哼哼地说完以后,李恪不仅没有大惊失色,反而十分平静地说:“这些我已经知道了。”
纥干承基道:“殿下,依末将看,这定然是长孙无忌那个老狐狸的诡计!殿下如今重新得到皇上的器重,被封为征讨大将军,一旦出征,必将立下万世之功,到那时,李治的太子之位就保不住了,所以长孙老儿才使出这招借尸还魂的毒计,想掀起风浪以阻止殿下出征!”
李恪眉头深锁,目视前方,一言不发。
纥干承基越说越激动:“殿下,这些日子以来,您一直忍辱负重,如今长孙无忌得寸进尺,欺人太甚!难道我们就这样步步退让,任他宰割不成?如果现在不出手,若皇上再听信一时的谣言,有所动摇,殿下岂不是又要坐失良机了吗!?”
李恪仿佛陷入了沉思之中,仍然没有响应。
纥干承基急不可待地主动请缨道:“殿下,是时候给长孙无忌一点颜色看看了!殿下如有使令,末将定当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李恪终于发话:“纥干承基,你先退下,本王自有计较。”
纥干承基怔了一下,又急急央告道:“殿下,别再犹豫了,快出手吧!”
李恪厉声喝道:“退下!”
纥干承基失望不已,怏怏地告退离去。
李恪缓步走至庭院正中,仰天长叹,一只手紧紧握住佩剑的剑柄。忽然,他拔出了锋利的宝剑,用力掷向不远处的空地上,剑身稳稳扎入了泥土中。
原来,李恪之前的郁郁寡欢都是由此而来。望着此时李恪那悲凉的背影,我后悔自己刚才为什么不回避,而要傻傻地亲眼目睹李恪此时的失意与懊丧,让他在所爱的女子面前尴尬。更恨自己的无能,如此危机面前却完全帮不了他,想不出一条象样的计策。
与其为自己的多余感到无地自容,还不如无声地离去。
“墨儿,不要走。”
在我转身想要离去的一霎那,李恪忽然挽留道。
我再次回转过来,面对的仍旧是李恪的背影。
“恪哥。”
李恪也转身面对我,莞尔一笑,没想到此时此刻的他竟然还会微笑,只是这笑容十分惨淡凄凉。
“如果你是我,会接受纥干承基的提议吗?”李恪竟这样问道。
“这......”我有些意外,但还是如实道出自己粗浅的想法:“如果是我,我也许会对谣言充耳不闻,无动于衷,毫不在意失去出征的机会,因为我原本就甘心做一个凡人,选择平静安稳的活在世间;如果是我,我也可能会让纥干承基抑或亲自手提利剑斩下长孙无忌的首级,以解多年来的心头之恨,因为我不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而恪哥毕竟不是我,既不肯甘居人下,又能够忍辱负重,用何种方式应对,都一定会经过深思熟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