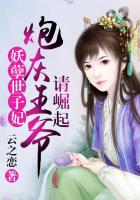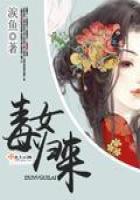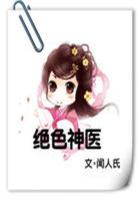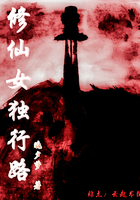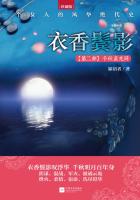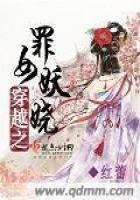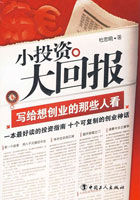楚怀忠就算看不起家里的穷亲戚,也不能将他们贬去当驿卒,这是要担上千古骂名的,搞不好就遗臭万年。
楚怀天也皱起眉头,他的设想里,是想给宗室找一些不累又能赚钱的生意。
要是上官晴明白两人的想法,一定会哈哈两声,然后说一句:“臣无能。”请他们另请高明。
既然说出来,上官晴脑中自动补充了宗室经营驿站的好处,想一想就知道垄断行业有多么的挣钱。
这时上官文和说道:“臣以为不妥,朝廷每年维持各地驿站的费用要六十万金,如果有宗室管理驿站,恐怕还要贴补更多的钱进去。”
王丘山也在旁边点头,作为文官,他是不想在宗室身上花钱的。
上官晴看看两边,首先安抚上官文和与王丘山道:“将驿站交给宗室,朝廷就不必贴补费用维持,而且只能前三年不收费用,三年后还要按照驿站等级不同收取例税,贴补朝廷的财务。”
“不可能。”楚怀忠不住的摇头,他可是知道宗室的嘴脸,知道那群人没钱就闹事,让他们干活就懒得不行。
楚怀天也觉得不靠谱。
上官晴解释说:“国内的驿站遍布七十二路,三百军州,而且每一处驿站都配属土地养活驿卒,只要将驿站向民间商人开放,每年光是餐饮住宿的收益就足够养活宗室,况且宗室也可以养活商队,他们是不用交国内的过境里金的,经商的获利更多。这样朝廷虽然会少一笔税金,宗人府却能省下一大笔钱来,只要将这笔钱划拨给户部,也就贴补回来了。”
上官晴的办法是以物易物,将一部分税金拿出来养活宗室,而不是从内藏库直接拨款给宗人府,内藏库的钱直接拨给户部,这样即养活了宗室,朝臣们也能够满意感恩,算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王丘山抓住其中关键问道:“如果天下商贾都与宗室联合,商队不交过税,地方上的衙门要怎么运营,这也是一笔钱。”
上官晴已经想到这个问题,说道:“收取过税里金并不合理,比如粮食,就是因为过境里金过多,才有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说法,因为过税太多,贩卖这些不挣钱。如果没有了过税,只靠民间力量,就能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去。”
王丘山插嘴强调道:“我是问,要怎么解决地方的财税。”
“可以收住税,按照经营的品种和营业面积的大小收取固定的税金,经营低价货的可以少收一些,比如粮食,高价货可以多收一些,比如布匹、金银。对了,我觉得对当铺应该收重税,要比高价货的店铺还要高一些。”
“如果地方官员与奸商勾结,将高价货按低价货算怎么办?”
“地方财税是要地方自用的,有官员愿意过苦日子,尚书又何必挂心呢?伸手向朝廷讨钱的地方官,每年给一次差评,他们会明白的。”
“如果分类高价货低价货?”
“朝廷拟定章程,一项项列出来公布天下,让天下百姓知晓,如果有官员暗中阻扰,朝廷也不必客气,既然他们不为朝廷着想,朝廷又何必优待他们。东郭先生的故事,想来大家都听说过。”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已经把解决方案讨论了出来。
楚怀天频频点头,觉得这个方法好,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地方对中央的吸血,可是想想又觉得不妥,一旦地方有了独立财源,很可能不听从中央的调遣,楚国一直以来的结构会被打破,很可能有人在地方举兵造反。
楚怀天轻咳一声说出了心中的顾忌。
上官晴说:“此法推行要与宗室经营驿站一起,只要宗室掌握天下驿站,地方的消息就能够直接传到朝廷来,任何地方有异常朝廷都能第一时间知道,宗室为了自身的利益安危,也不会看着地方势力做大的。”
“如果宗室有异心呢?”楚怀忠问题有些大逆不道,如果他不是宗人府大提举,上官晴都怀疑他在挑拨。
上官晴说:“地方豪族不会放任宗室渗透到地方的,可以规定宗室不得与当地豪族联姻,娶妻必须远娶,这样规定,至少百年内,地方豪族不会和宗室形成新的利益团体,对朝廷不利。”
上官晴此时,完全带入了凌灵的状态,现代文明累积了数千年的政治经验喷薄而出。
上官文和心中哀叹,如果是儿子该多好。
楚怀天心中却在想:“多亏不是男子,不然朕的天下危已。”
“受教了。”楚怀忠鞠躬行礼,竟然对上官晴施弟子礼,可见他心中对上官晴的佩服。
“过奖了。”上官晴还礼。
楚怀忠转身对楚怀天说:“臣附议。”
王丘山也上前说:“臣附议。”
上官文和最后走出来,又问道:“除了经营驿站商队,还有其他的收入吗?要知道宗室人口众人,而且还在增加。”
楚怀天脸色抑郁,怎么觉得宗室被当成了猪。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二百万人团结起来,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我想陛下一定有善用之法。”上官晴把决定权踢给楚怀天,她今天说的够多了。
上官文和没有继续追问,也对楚怀天说:“臣附议。”
关于宗室法案,就在冬暖阁内敲定了下来,楚怀天让王丘山动笔,将今日的君臣对话记录了下来,删掉其中一些不容易被人接受的内容,然后交给匠造书印书局印刷发行天下,楚怀天亲笔题写书名《新春问政录》。
上官晴回去后又用心编辑了一下,命人印刷了六个版本的《新春问政录》,其中最便宜的十个铜板一本,最贵的精装版三十银一本。版本间的区别除了纸张和印刷精美度,里面还分别附录了“大师”们的分析笔录,各种猜测浮想联翩,角度有正有歧都十分新颖,越贵的版本附录内容越多,而且每一本的附录内容都不一样。
书上那些“大师”用的都是笔名,其实都是上官晴写的,内容来自凌灵那个世界经济学大师们的文章,稍加改动就成了书中的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