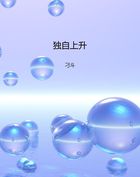父亲全然没有醒悟,只一个劲沉浸在他的思绪里,说,没关系没关系,关上门,大不了唱的时候,连窗户也关上。
第二天早上,母亲说,你父亲一早就起来了,烧开水,泡茶,还老是嗯嗯地清喉咙,就像担心那嗓子不在他喉咙里似的。
其实那天早上,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能当上老师,因为婉西压根儿就没出现。婉西回剧团去了,去拿衣服,请假,再看能腾出哪些时间来“上课”。那天早上,父亲没办法静静地喝茶,老是走来走去的,最终立在了窗前。窗外有一棵梧桐树,已枯了一整个冬天了,再怎么说,也该发芽了吧。
九
后来,母亲说,婉西来后,就因为父亲的过度反应,或者因为一番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母亲没让婉西先跟着父亲“念戏”。
也就是说,母亲没把婉西移交给父亲。
到这时候了,母亲才依稀觉得,婉西拜她为师,她就有了话语权而父亲没有。在我们家,母亲一直就生活在父亲的影子里而常常忘了自己,如今借助婉西的出现,母亲显出了形,凭着她一贯平静淡然的性格,她倒未必真要与父亲较劲;然而下意识里,她又何尝不想趁此机会做一回主,露一回脸?因此婉西来后,她几乎不看父亲,而是像所有掌权者那样,挺直了身板,让声音穿过硬邦邦的身体和喉咙钻出来,以强调自己的权威,掩饰自己的虚弱。然而母亲的底气实在不足,即便极力装扮,她的声音听起来仍然很飘,好比水面上的浮萍,看上去稳住了,实则无根无底。
母亲说,婉西,我们先来学身段吧,先学身段。
母亲指的是《秋江》,《秋江》中的身段表演。母亲知道,《秋江》中的身段表演相比其他许多剧目,戏份的比例要重很多,比如说在虚拟的江面上行船,上船下船时的颠簸与惊骇,道姑在船上极目远眺……可无论身段表演如何重要,只要动作一起,就离不开音响节奏,只要嘴巴一张,就离不开唱腔台词,换言之,没有独立存在的身段表演,没人能把动作和声音截然分开,相反动作越多,音响和节奏的作用就越大。
母亲明白这个道理,可她并没有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严肃性。此时的她因为正经八百收下了学生,就想独立完成整个《秋江》的教学工作。再说演了若干回《秋江》,她也多多少少攒下了自信,多多少少有了些成名之后的飘飘然。她与婉西一起把饭桌挪开,把茶几挪到了靠墙的位置,腾出了客厅里的大部分空间。
她站好了,气上提,摆好了出场的架势。
婉西站在她身后,也摆好了架势。
谁知母亲动作未起,嘴里先有了声音,锣鼓声:锵锵锵锵……
父亲就坐在那只靠墙的沙发上。
从婉西进门到随后的兴师动众搬桌弄椅,再到母亲说出先学身段,父亲一直就大睁了眼睛毫无反应。他不是不反应,他是差不多蒙了,一条顺理成章的路突然拐弯他不得不蒙。那几天里,婉西离开的那几天,父亲没少在心里谋划过憧憬过。又或者,他压根儿就没把婉西拜母亲为师听进耳朵,搁在心上。他才是老师,他是天经地义当之无愧的老师,他是老师的老师,他生来就是当老师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感觉:如今的他还能教婉西,还能教像婉西这样的年轻娃,他已不是什么老师,他已不是要手把手地教学生,而是要拽住一根救命稻草不松手。
母亲嘴巴里的锣鼓声像一根大棍,猛地将父亲敲醒了。他屏住气,闭上了眼睛。
没有人知道父亲在想什么。
父亲司了一辈子鼓。其实父亲面前的那只脸庞大的小鼓发出的声音并不响亮,远不如锣、钵或者大鼓小镲来得激越。然而那只小鼓的功用,就好比交响乐队前的那支无声的、细如竹签的指挥棒,“小”并不代表弱或者无,相反“小”在这一刻,代表着高度和强势,代表着权柄和主宰。要主宰别人,就须了解别人。因此父亲练就了一身功夫,除了能把打击乐中的所有响器玩熟玩透之外,还能在嘴上娴熟流畅地模仿出所有打击乐器截然不同的声音。
这也是他“念戏”多年念出来的功夫。他为演员念戏,他一张嘴就是整个打击乐队和管弦乐队,是所有音响效果的全部。演员要什么他的嘴里就能给出什么。一场戏念下来,至少在他和演员的感觉中,他们已将整出戏完整而透彻地演出了一遍。多年的习惯让父亲有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嗜好:自己用嘴念锣鼓却容不得别人的嘴里发出锣鼓声。原因很简单,别人嘴里的锣鼓声正如一只不会拉二胡的手在弦上磨蹭,发出“咯咕咯咕”之声,这声音不光刺耳,还伤神,还揪心,仿佛正有人拿刀杀他似的。
母亲大概也深知这点。母亲与父亲一生陪伴,唱戏说词,从没在父亲面前念起过锣鼓。当然了,母亲也无须口念锣鼓,她需要的声音,父亲满肚子都是,根本无须她亲自动口。因为听得多了,就难免产生错觉,以为手到擒来张口就是,谁知此时的她一开口,她自己的耳朵先抗议起来:那是她自己的声音吗?那么飘浮,怯懦,还带着异味,仿佛房梁上窜进来的坏食物的臭味……
但母亲已没办法放弃。她已经开始了,动步了,婉西就跟在她的身后。她就像一颗被推上了膛的子弹,扳机已经扣响,她想不想出发都必须走。比画的间隙,她拿眼睛去瞟父亲,父亲正闭目养神,看不出任何反应。她的心踏实了许多。至少,婉西辨不出异味,也看不出问题。再说了,丈夫毕竟是她的丈夫,早见过妻子短处的,短处见得多了,也就未必需要藏着掖着。
在母亲怪异声音的伴奏下,《秋江》中的道姑手拿一把拂尘,云朵一般飘出,去追赶已经乘船离去的书生。紧接着就是唱腔,唱腔母亲熟悉,而婉西不熟。不熟就得“念戏”,可母亲念不了,也不想念。母亲自己哼着,让婉西跟着她走,很快,她们来到江边,叫来了老艄公的船,这就要开始上船了,而上船的那一瞬,是身段表演的重头戏:道姑踏上虚拟的船头,身子往下一蹲,老艄公在另一端,往上一踮,两人一蹲一踮,此蹲彼踮……
婉西跟在母亲后面,茫然地跟着,茫然地一蹲一踮,全然踩不准节奏,也做不像动作,她突然站直了,红了脸,眼睛扑闪闪的,像两只正要扑火的飞蛾,她说,嗯……老师,这一蹲一踮的,啥时候蹲,啥时候踮?这都……是在干什么呀?
上船啦。母亲说。
上船,你不懂?母亲扭过头来,又说:道姑上了船,把船踩翘起来了,船一起一伏的……
哦。婉西说,又重新蹲了下去。
父亲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此时父亲的眼睛仿佛两口火山。父亲没想到他一辈子津津乐道的川剧,他一生一世魂牵梦萦的川剧,他心里梦里诅咒怨恨的川剧,经母亲这么一弄,竟像小孩子玩游戏一般滑稽可笑。不,连游戏都不如,顶多是一堆既搭不成房也做不成家具的碎木屑,是一堆垒不起雪人的残霜败雪。
父亲忍无可忍,已到达了极限。他就坐在那只沙发上,声音如同雷鸣:你要先给她讲戏,讲剧情,剧情!她连剧情都不知道,连剧本都没看,连唱腔都没念,你就要教她学身段,你这不是在对牛弹琴吗?
你这是在乱弹琴,乱弹!
末了父亲站起来,喘着粗气:演了一辈子的戏,连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起码的……你这样教,你就是教上三天三夜,越教她越笨,就像你一样……最后一个“笨”字父亲没说出口,父亲把它吞进了肚里,摔门而去。
十
“念戏”是从第二天开始的。由父亲上阵,就在我们家的那张饭桌上。
那天教身段,父亲咆哮着打断母亲,把婉西搁在了客厅中央,也把母亲原本不多的心气打压了下去。每到这时候,母亲别无选择,总会让步。往往是这样,父亲强,母亲弱。父亲脾气一经上来,母亲就会缩回去,像一只小猫那样无声无息。
这一次更不同。母亲觉得是她自己惹恼了父亲,是她的低能,她的没用。或许她可以说,她确实没教过学生,没有经验,可私下里面对自己时,她又何尝不知,她根本就不具备能力教授学生。
她能给婉西讲戏,讲剧情?那些剧情,那些最微妙最要紧的感觉,她心里都有,也能演出来,可她说不出来。若干年来,她就像一只存钱罐,只有极小的开口供人输入,可想要倒出来,除非把罐子摔碎,把她的肚子剖开。
这样一想,母亲的心里反而踏实了。晚上父亲回来,母亲端出热饭热菜,照例地坐在父亲一旁,看他吃。
然后,母亲幽幽地说,要不,明天你教她,你给她念?
父亲不说话,埋头对付着一只猪蹄。猪蹄是父亲爱吃的一种食物,因此母亲常常不吃,都让父亲吃了。吃罢猪蹄,父亲洗好了手,坐去沙发,端起了茶碗,揭开盖,这才说:哪有你那样教学生的?你要么不教,答应了人家,就得对人家负责。
父亲是在给母亲留面子。其实他心里想的是,你哪有本事教学生?或许,在父亲心里,他压根儿就不认为有任何演员可以教好学生。
“念戏”便从第二天开始。由父亲主持,母亲退去二线,做起了服务工作。偶尔,做罢家务之余,母亲还会记起她的老师身份,这时候母亲便走过来,静静地坐在桌旁,看父亲与婉西“念戏”,间或插上一两句。看着父亲有板有眼的样子,听着婉西十分明显的进步,母亲的心里泛满熟透了的橙子的味道,甜甜的,爽爽的,爽爽甜甜的深处,却未必不见酸涩的影子。此时她才留意起父亲“念戏”的方法。父亲“念戏”就像裁缝裁衣,先将布料铺在长桌上,再画线,再细致地描好每一个细部,看看一切都就绪了,不会再有差错了,这才屏足了气,一刀下去。
父亲从剧情开始,到每一段唱腔说白,再到每一段情节心理的处理,再让婉西站起来,在他的注视之下,从头到尾地串排……
结果可想而知。仅仅用了不到三个月工夫,婉西就在她所在的土桥乡川剧团,以一出《秋江》,获得满堂喝彩。
十一
那天婉西演罢归来,人还没到,呼呼的出气声先喷进门,跟着她一头扎进来,说,老师,老师,我演完了,演完了。
当时父亲就坐在那只沙发上,母亲照例在厨房忙乎。婉西的两声老师,一声是给父亲的,一声给母亲。
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说,演完了?
可父亲没动。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他想听的不是这个,他所关心的也不是这个。
后来父亲转过头,看着婉西,满眼睛都是问号。
婉西还在兴头上,像一片刚着了火的小树林,满头冒烟,满脸绯红。她仿佛发现父亲的反应有些不对,又还找不出问题所在,低了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那样,翻眼看着父亲。
父亲说,就演完了?
演完了。婉西回答。婉西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胸口的气又粗了:老师你是问演出的效果怎么样是吧?效果很好,观众使劲鼓掌,我谢了三次幕都不行。我还得了鲜花,老师你猜,人家演出完就得一束两束,你猜我得了多少?
老师你猜?
这一次婉西的声音特别大,是专对母亲喊的。母亲又缩回厨房去了,水管开着,母亲正淘菜下锅。
母亲没听清婉西的声音,就听见婉西在大声嚷嚷。父亲这时候换了表情,像个小孩子一般抬起眼,正猜谜语的眼神:
多少,你说!五束?父亲张开一只手掌。
哪里啊,十一束呢。婉西大声说。
给演员送花是近几年方才兴起的一种做法,源头来自旧戏班子,又在歌舞厅发扬光大,然后被一帮赶时髦的演出团体嫁接了去。旧的新的混杂,台上台下通用,因此也算得上一回时尚。
一束花,观众买过来五十一百,三十二十不等,送到演员手里,演出结束后,演员再去团长那里领取提成。
但父亲兴奋的不是婉西挣回了多少钱。父亲不关心婉西挣钱的事,他所关心的是婉西的演出,最终成功了。
成功是什么?是他的付出婉西的努力。是他那要命的川剧艺术还有人看,还可以感染人感动人,是如潮的掌声鲜花笑容泪水……
十一束鲜花,比别人多出了五倍十倍,这不是成功是什么?
父亲仍坐在沙发上。他端起茶碗,又放下。站起来,又坐下。然后说,好,好,好……
那天晚上,饭都上桌子了,父亲还站在客厅里,顺着父亲的眼睛,母亲发现他在看壁橱。他对母亲迎上来的眼睛说,哎,我记得,我们还有点酒吧?对了,还有,至少还有半瓶,那次张师兄来,没喝完的。
见母亲没有反应,父亲又说,你找出来,喝点,喝一点……
父亲从来不喝酒的。他不胜酒力,小嘬几口就足以让他脸红筋胀,因此酒对父亲,就好比炸药之于常人,是不敢轻易碰的。即便是那段阴雨绵绵的岁月,他从鼓棚子上被赶下来,他也从不以喝酒的方式表达情绪。
母亲当年演出《秋江》,也成功,也获得了满堂掌声,还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也没像今天这样,主动要求喝酒,更没像今天这样,连声地说好,在屋子里团团打转。
母亲人站在桌前,免不了陷入沉思。随后她放下手里的碗筷,去开壁橱。酒找出来了,父亲说,你也喝点?
又扭头对婉西:婉西,你也喝点,少喝点?
婉西赶紧摇头,说她从不会喝酒。母亲将一只鸡蛋大小的酒杯往父亲的面前一顿,说,我不喝,我也没那口福,喝不来。
坐下了,母亲低下头,道:我也没你那么好的兴致。
十二
后来,母亲说,婉西成了他们团里的名角儿,台柱子,也成了我们家的人似的,就像当初的你。
母亲说,当初,你知道,只要你在家,你怎么做你父亲都是高兴的。可别人不行,他的那几个徒弟,哪个行?见了他还不像老鼠见了猫。
母亲又说,连他自己的亲兄弟也不行,这你也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