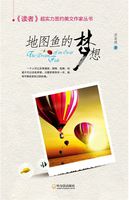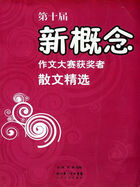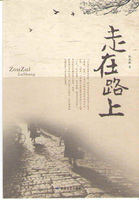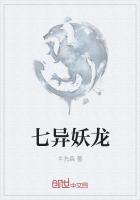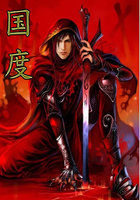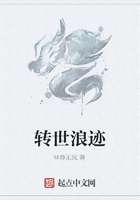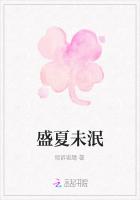一本书叫做闭嘴
陈丹青
喜欢陈丹青其人其文,大概因为他性格饱满,自由,独立,真实。如果真有所谓的文艺界,又或者文艺圈,也算是见惯了三十不立,四十不惑,格外坚定油滑的人物;也见多了曲折玲珑,精乖细巧的人物。世情如何,岂能不知?只不过大家不声不响,不管不顾,花花轿子一起抬。谁知竟然有陈丹青这样放纵恣肆的人物,偏偏就要捅破天机,三两下撕扯开那层窗户纸,一把掏出肝脑涂地一窝肚肠,血淋淋的,好不狰狞。陈丹青就有这样的生猛。
然而,他也有别样的妩媚和精致。陈丹青好玩,好看,我以为是他一身担负了许多大矛盾,纹理错综,且都协调自在,从容并处,所以才呈现质地的斑斓。他是今人,却有魏晋的风度,民国的气质。他画西画,文字却秉承国学的脉络。他是上海人,说话有靡靡南音,有一种矜持和柔软,引人怀念,然而他骂起人来,却完全是北京腔调,粗而不鄙,十足的江湖。他的文章亦是如此:当今之世,少有用字如此精当简峻者,少有行文如此光明磊落者。因个人际遇,他有眼界,有胸襟,因个人心性,他又有情怀,有真心。写到幽微之处,突然他会爆几句粗,恰如临锅的胡椒,破掉寡淡,破掉精细,格局为之一大,往往神采全出,令人会心一笑。陈丹青的字,是有神采的。
有时先生说:他们一旦看见一个不愤怒,不骂人的陈丹青,就觉得这不是陈丹青了!当然,他不是当真抱怨。我其实理解大众,因为我就喜欢看先生骂人。他骂人好看,也好听:骂得全在点子上,通透,痛快。迎战时,锋芒毕露,机智随性,回避时,腾挪如意,退也如进。骂人,颇能见性情。
喜欢陈丹青的人,往往因为他敢骂,敢说。不喜欢陈丹青的人,也许是因为他太敢说,太敢写。这一点,从“多余”到“退步”,从“继续退步”到“荒废”,从无改变。在新书《荒废集》的序言里,先生自己说,这本书应该叫“缄言集”,缄言,就是闭嘴。一个放言的人,居然取名闭嘴,这里头有一点黑色幽默,有一点苦涩。《荒废集》其实繁盛:讲阅读,讲艺术,讲市场,讲知青,内容时新,亦讲去年的盛事与灾难,有随笔,有访谈,有日常生活。他写鲁迅,也写范冰冰,在同一本书里。内容看似芜杂,但却并不纷乱。因为陈丹青的气息是连贯的。
我庆幸这个时代,有他这样的人与我们“进行时”,与我们共经这一遭人世。有时看去人的书,我常常在想:若是谁谁谁还活着,眼见得如今这个世界,他会怎么看?怎么说?怎么写?陈丹青的书,不必多介绍,就是他在活,在看,在想,在写。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的文化,是一个断裂的文化。陈丹青的写字,他的说话,他的浩叹和咆哮,我想,正也是一种努力,续接那道受伤的文脉的努力。
因为新书《荒废集》与陈丹青聊天那日,幸好他没有“缄言”。我们一路聊下去,从电影到纪录片,从****到民国,从台湾到日常,从学院到教育,从北京到上海……聊得殷殷实实,和风细雨。开始,微微有点不习惯这样的陈丹青,太平静,随即,更加喜欢这样一个陈丹青:双臂平放在膝盖上,目光并不高高在上,声音有一点儿疲倦,真实恳切,知无不言,滔滔而并非不绝。世人只见他峥嵘凶猛之处,却难得见他波澜壮阔下,静水深流之处。方才看黄集伟有一句话,讲得好,是讲一个写作者的气象。我以为,风云翻滚,是一种气象,云深不知处,也是一种气象。和陈丹青先生聊天,真能感觉到天高地阔,云卷云舒。
谈话部分
出名要趁早
绿 妖:请问您小时候就开始画画吗?我小时候写东西,父母总是说不好,很自卑。
陈丹青:父母这一关其实是第一关,每个人都一样。我童年的时候,把画给家里人看,他们说:“画得这么好,再画一张。”所以以后,不论再怎么受苦,再怎么委屈,都还有一分底气。这方面,我不会有阴暗心理。还有,张爱玲说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悟到这个,就是那句“出名要趁早”。(大家笑)这话真是对。我那时候,是完全悟不到这一层,就出名了,后来才知道,这一关其实已经过掉了。我后来看到太多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还没有成名的人,真的有才华,但是太苦了。
柏邦妮:先生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两大关。(笑)
绿 妖:这方面我是完全上当了,从小的观念就是大器晚成。看所有文学作品里,也都是说,一个人要经历多由的磨难,才够丰富,作品才好……
陈丹青:也不能说完全是欺骗,因为你相信了。还有,你没有听到别的说法,没有选择。
香烟
柏邦妮:先生你抽的是什么烟?
陈丹青:女人抽的烟,叫大卫·杜夫。
绿 妖:我在小说里非常喜欢写这个品牌。但我从来没见过。
陈丹青:你可以抽一根。
绿 妖:不,我不抽烟。(大家窃笑)
叙旧
柏邦妮:好快啊……我们上一回见面,已经六年了。我都记不得我那时候是什么样子了。
陈丹青:头发你变过吗?
柏邦妮:变啦!不过也差不多吧。
陈丹青:戴眼镜吗?
柏邦妮:一直戴啊!但那时候瘦好多。现在到北京胖了……
陈丹青:现在像个资深作家或者资深编剧了。(笑)
柏邦妮:哪儿像啊……(深感羞愧)
陈丹青:就在那一次,我们谈话,有个人给我递条子,说:陈老师,你这样说来说去,是要退步的。后来我就没扔这张条子,再后来就有了《退步集》。就是你在的那一次。
柏邦妮:真的啊?那次你给我的印象太好了。那时候二十岁,没有见过那么精彩的人。
陈丹青:你当时在南京大学还是……
柏邦妮:在南京艺术学院,后来就来北京了。
虚构与生活
柏邦妮:先生你还记得,当年我们是从谈电影开始的吗?
陈丹青:记得,我们讲了一个晚上戈达尔。
柏邦妮:最近看了什么好电影吗?
陈丹青:《梅兰芳》啊,《非诚勿扰》啊。《梅兰芳》头一段还是可以的,陈凯歌他想要的东西还是在里面。我也很喜欢他拍的那个被骂得一塌糊涂的--荆轲?
绿 妖:《无极》?
柏邦妮:《荆轲刺秦王》。
陈丹青:对。我觉得那是他最好的一部电影,可惜被冷落了。其实比《霸王别姬》要好。还有《非诚勿扰》也很好,远远超过冯小刚以往的电影。所以事情还是要做,做着做着就成熟了。
柏邦妮:对对对。我以前也不理解冯小刚为什么要搞《夜宴》、《集结号》,尤其是《天下无贼》,我觉得很一般嘛。但是这次再看《非诚勿扰》,觉得气魄大了格局大了以后,再做小东西,非常从容,有举重若轻的感觉。
陈丹青:还有看外国电影。我很迟到地看了一个电影,叫《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很好。还有一个好莱坞电影,讲两个女人都失恋了,互相交换,你到我那儿去,我到你那儿去……但是我忘了那个名字。
柏邦妮:我知道那个电影,女演员很出名。
陈丹青:有一个就是演《泰坦尼克号》那个。
柏邦妮:对,凯特·温斯莱特演的。
陈丹青:还有一个电影很好,是讲作家的。我想推荐给王安忆,但是到上海去的时候忘了。
柏邦妮:是《卡波特》吗?
陈丹青:不是,《卡波特》非常好。是一个讲书的电影,是有一个上班族,老有个声音在很准确地(描述),他刚穿上大衣(那个声音)就会说:“他现在穿上大衣出去上班了”,然后过马路……他觉得有个声音一直跟着他。
绿 妖:这两年的新片是吗?
陈丹青:也不新了,有至少四五年左右。
柏邦妮:完全没听过。
陈丹青:我老记不住电影名字。
绿 妖:好像是一个作家在写一个小说,她写的那个小说在真实中也在发生。那个人的生命就被改变了。
陈丹青:对对对。最后这个人急死了,这个声音老跟着他。他就老找一个老的文学家求救,是达斯汀·霍夫曼演的。过程我忘了,最后是这个女作家决定让他在小说里死掉,结果他在生活里也真的死掉了。但是因为好莱坞总要给个亮一点的结尾,他又没死,给车轧了,又救回来了。但是这个结尾之前,电影是好极了好极了。就是写虚构和生活的关系,写得好。
柏邦妮:你看过《时时刻刻》吗?
陈丹青:也好的,也好的。那个是其实有点蛮可怕的一个电影。最可怕的是那个女的找个旅馆要去自杀那一段。这个太好了。
讲述“讲述的不可能”
柏邦妮:说起《时时刻刻》,我就想到我最近想写的剧本。
绿 妖:是要写一个演员的那一个?
柏邦妮:不是,是写三个女人的。我前两天刚跟我导师谈过,他叫张献民。他是指导我毕业剧本的导师。我想写萧红,但是我不想就那么常规地写,写她一生波澜起伏生死离别,不想那么写。我很喜欢另外一个日本女作家,叫林芙美子,她写过一本书叫《放浪记》。成濑巳喜男喜欢她的小说,拿来拍了好几部电影,像《浮云》、《晚菊》,这都是她写的。她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她们是同时代的人。我觉得这种东西很有意思。她们俩的境遇也特别像。她们写的那种随笔,写生活在底层挣扎的写作的女人……我很想把她们并置来写。
陈丹青:Beautiful!
柏邦妮:我想能不能再添一重,就像《时时刻刻》那样三重,三个人。但是我没有想好怎么来构建这个关系……被我导师给否了。他说,你有多少时间去研究民国那个时候的人?去研究萧红?去研究林芙美子?他作为老师必须要说出你的草率。他是对的。
陈丹青:你现在还在读书啊?
柏邦妮:第三年啊,研究生。
陈丹青:在哪里?
柏邦妮:北京电影学院。
陈丹青:哦。你老师是?
柏邦妮:张献民。是一个人称中国地下电影教父的人。他是个很好玩的人。我记得有一次,看见他和他的研究生一起谈毕业剧本,就像夫妻俩在打离婚。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大家笑)。昨天我们谈到最后,又像是打离婚,大家不说话,僵持。哈哈!先生,你有没有想拍的电影?
陈丹青:电影这个事我不敢去做。因为我的性格是一个单干的人,而拍电影要弄一群人。但是,单单瞎想当然会有。先得有本子,《多余的素材》实际上几乎可以说是那些碎片了,可是怎么把碎片变成一个电影,这个很困难。我听说过一部电影,是纪录片,三个钟头。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到一对母女,这两个人之间沟通上有问题。女儿一直想知道纳粹时候到底(妈妈)你的经历是什么?因为爹已经没有了。到电影最后,那个娘坐下来说,好吧,我给你讲吧,这个电影就没了。我一听这个,我就觉得他们真懂。它不是在讲纳粹,而是在讲关于纳粹的叙述所遭遇的困难。
柏邦妮:有些伤疤还是隐藏在人心里的。我认识一对夫妻,即便已经中产富裕,但是一说起一些事情来依旧义愤填膺,热血沸腾。
陈丹青:但问题是,一个没有被说出的经验,它就不算了。就像你说的那对夫妻,我相信几千个人都在说,问题是仍然不算了。它一定要变成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可以。经验要成为作品才算数。
柏邦妮:今年有一个纪录片,我很想去看,但是没看成,叫《横滨玛丽》。它讲的东西很有意思,就是你知道日本战后有很多美国大兵,所以有很多妓女专门服侍这些大兵。有个叫玛丽的女人,她跟别人都不一样。她穿很高贵的衣服,白纱裙,打一个小白洋伞,化艺妓那样的浓妆。永远站在横滨街头,只接待军官。她的谈吐举止都跟别人很不一样,就是大家闺秀那个样子。她在横滨街头站了几十年,一直到她很老很老了,还在外边站街接客。后来就成为横滨的一个街头风景,人们都知道这个人物。直到有一天她消失了。
陈丹青:是纪录片?
柏邦妮:纪录片。
陈丹青:****!
柏邦妮:那个人(纪录片导演)就开始去探访,因为她已经消失了。玛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去找认识她的人。有的人就会说很多很多的事,讲那时候嫖妓的事。有一个小报记者为了采访,就被那个妈妈桑硬给上了。这种事情都有。大家拿出她的照片来看。最后大家找到这个女人,她在敬老院里面。脂粉已经全洗掉了,就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太婆。我听了就很想去看。
陈丹青:萨特有过一个剧本叫《可尊敬的妓女》,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还放过。现在不能想象。
柏邦妮:有什么你喜欢的纪录片吗?
陈丹青:我很惭愧,看的纪录片很少。但是看过的都很喜欢。纪录片是天然地会好,因为真实嘛,很简单。我看过我的老朋友王兵的那个《铁西区》,很好。还有,吴文光的电影我没看过。我在美国看过大量纪录片,但都是电视里看的。因为在中国,纪录片还没有变成一个市场。美国和欧洲是有市场的,专门成为一类产品。
柏邦妮:我最近听到一句话很有意思,戈达尔说的。他说:纪录片拍的是别人,剧情片写的是自己。
陈丹青:啊!他真懂。
柏邦妮: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非常有意思啊。可是有的时候纪录片拍的是别人,写的也是自己。
陈丹青:可是纪录片没有别人不行,剧情片有自己就够了。只有自己,就可以弄一大堆东西出来。他讲得非常对。纪录片是对象非常重要,你拍什么很重要,这个单靠你自己,无法完成。剧情片是其实要拍什么已经有了,都在他自己的心里面,只是怎么去拍的问题。
面孔
柏邦妮:先生,你觉得你的这本新书,最好的地方在哪里?
陈丹青:我觉得我每本书最好的不是文字,是图片。这里面有很多照片,像胡风早年的结婚照片和他的逮捕证,还有女劳模给毛主席点烟的照片,都特别好。
绿 妖:你喜欢谈民国人的长相,比如鲁迅。前几天我和朋友们在一起说这个,有个人说,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像难民。
陈丹青:(笑)谁说的这个话?很有意思。
绿 妖:我是听李拜天说的,是我的一个同事。
陈丹青:他出过国吗?感觉这个经验是出国带来的。
绿 妖:他出过国。
陈丹青:我当时出去最刺激的经验是: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街头都像难民?用不着三个,一个就很像。我从橱窗里看到我自己,也像个难民,(笑)后来我就不留长头发了。
绿 妖:但是你在中国看看,也会那么觉得,年轻人可能还没那么明显,但是人一到中年,脸上就被侵蚀得特别厉害,就是一副被生活殴打过的样子,那脸很难看。
陈丹青;你这个朋友很敏锐。木心1994年第一次回中国,他是1982年走的。他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散文叫《乌镇》,是他的故乡,(这篇文章)发表在台湾。还有一篇他比较谨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叫《上海在哪里》。因为他回到上海以后发现,上海没有了。其中有一句他说得很好玩:马路上没有兵没有马,兵荒马乱,家里面没有鸡没有狗,鸡飞狗跳。
绿 妖:我以前在国贸附近上班,你要是白天在国贸那里走,就是乱世,整个是乱世,尤其是地铁口那儿。
陈丹青:问题是你到香港湾仔,比这个人还要多,你到东京,到华尔街……
绿 妖:但不是这样的感觉?
陈丹青:绝对不是这样。人比我们的城市还要多,但都是疏散的感觉,疏散和流通的,默然中有一种秩序,即便人潮匆匆,并不觉得慌乱。
柏邦妮将《往事并不如烟》的照片给陈丹青看。
柏邦妮:我看这几张照片(余叔岩)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脸,很有意思。
绿 妖:我看过一张周作人要去受审时候的照片,真的是……怎么能那么有气质呢!
柏邦妮:我今天还看到孟小冬的照片,比章子怡漂亮多了。
陈丹青:你没有看到她晚年,太好看了,我没有想到她这么好看。(一起看照片)我看这张,已经觉得她很好看,但我想象不出,她拿掉帽子以后,整张脸日常是什么样子的。她跟杜月笙有两张照片是非常好看的,她穿着旗袍,站在杜月笙后面,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柏邦妮:眉目很清楚,神态也清楚,一点不混浊。
陈丹青:对,很清朗。
同源文化
柏邦妮:很喜欢新书里先生写台湾的那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