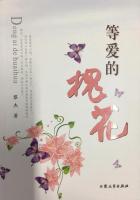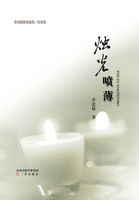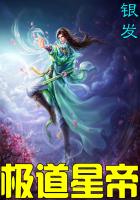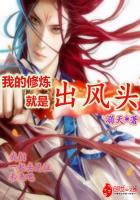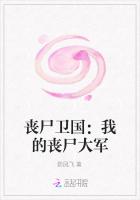文体不是孤立的语言现象,在其话语体式的背后,有一个话语主体的心理——精神结构所指向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家创造的话语符号结构,与其精神、心理结构具有同构对应性。文体作为文学话语的结构模型,既受到文化的制约,也同样表征着文化。特定文化中主体的行为方式与精神结构,包括体验世界的心理图式,是文学文体话语体式演化的内在规律。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化往往以胡、汉文化,也即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为表征。文化的整合形成北朝士人的特殊文化心态,如文化隔漠心态,畏祸心态与羁臣心态等。这是造成北朝诗赋凝重古奥的文体特点的内在原因。一文化隔漠心态在诗赋文体上的投射北朝文化整合过程,实质是汉族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整合过程,一个由碰撞走向融合的过程。碰撞和斗争表现在社会心理方面,就是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持排斥态度,对汉族士人采取杀戮政策;这导致了胡人统治集团对汉族文化的隔漠心态。中原汉族文化的传承在战乱时期的北方主要依赖于留存北方的士族大姓和其他文士。胡人的文化隔漠心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投射于文学创作,就是对汉族文人和诗赋创作的蔑视和禁止。这种情形以十六国时期与孝文帝实行汉化之前的北魏时期最为突出。如十六国时期羯族石勒的后赵,以********为号召,对汉族不论士庶一概屠杀。十六国时期近一个世纪时间,有名姓可考的赋家才15人,赋作才12篇。流传至今的只有1篇。除去几乎为汉族统治的“五凉”政权下的张斌、段业、李、刘、梁中庸、秃发归、张穆等七人,作者寥寥,作品也无一篇留传,辞赋创作几乎完全停滞。(1)如果不是“五凉”文人的努力,恐怕辞赋创作在北朝早就灭绝了。北魏建国,为了便于统治,借鉴汉族制度朝仪。
太武帝拓拔任用汉族士人,但又很反感汉族文化。《魏书·贺狄干传》的记载,及《崔逞传》的记载就是显例。北魏前期胡人统治集团文化隔漠心态的另一个典型事件是崔浩国史案。《魏书·崔浩传》及《北史》本传说崔浩因修国史“备而不典”,“北人(鲜卑)咸悉怨毒,相与构浩于帝”。于是夷浩九族。“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实际上崔浩之死是胡汉********激化的结果,国史案只是借口。魏收修史,为何于《崔浩传》中不肯明确道出原因,而只是提出修国史一事?周一良先生认为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北魏旧史可能不愿暴露鲜卑统治者与汉族高门间之冲突,于是魏收只沿袭旧文,而在《卢玄传》的行文中微见其意。第二是魏收修史时正当“鲜卑车马客”高欢统治的时期,他不敢详细叙述崔浩事件的经过和真正原因,怕因文遭祸。(2)周先生所言应有所据。由上可见,时至北齐,虽经魏孝文帝实行汉化后较长的时期,以出身六镇的军人掌握政权时,不仅仇视汉族士人,而且仇视汉化的胡人士族,文化隔漠心态仍然存在。史载尔朱荣攻占洛阳后,费穆劝告他说:“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魏书》卷四十四本传)。这种出身和文化上的自卑心理驱使尔朱荣屠杀胡汉门阀士族。《魏书》卷七十四载尔朱荣入洛,将朝士们骗至河阴,“列骑围绕,责天下丧乱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缘此等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纵兵乱害王公卿士,皆敛手就戮,死者千三百余人”。由是北朝士族人物几乎尽歼。当然,统治者具有文化隔漠心态,并不是说他们对汉族文化完全排斥,他们对于汉族的制度礼仪、经学、儒家思想等有利统治的一面还是接受的。而对于汉族的审美情趣、生活习惯、语言文学则持漠视态度。这必然会造成对诗赋创作的排斥。诗和赋对于汉族文人而言,是中原汉族文化的标志,是他们高门身份的标志。而对少数民族中怀有文化隔漠心态的人来说,则是其文化心理上的对立的表征。所以他们对之加以蔑视和禁止。曹道衡先生分析认为:北魏初年的文化本来比较南朝落后,而统治阶级对待士人的政策,更使北方文学的发展受到不利的影响。由于拓拔氏上层分子不甚理解汉族文化,又对汉化怀有一定的敌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当时的士人较少在这个领域里作努力。……统治者对诗赋既不欣赏,对辞藻华美的骈文也不感兴趣。(3)统治者的文化隔漠心态,是造成北朝诗赋创作总体上不如散文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产生像南朝那样的创作风气,更不用说有意识地探讨诗、赋的体式与技巧了。由于文化隔漠心态的间歇性出现,诗赋创作的真空状态在北朝后期也还存在。北魏诸帝中,除孝文、孝静外,多不尚文雅。北齐开国皇帝高欢“指事论心,不尚绮靡”(《北齐书·高帝纪》);孝昭帝“所览文籍,源其指归而不好辞采”(《北齐书·昭帝纪》)。周的开国皇帝宇文泰更是反对华丽的诗赋,“性好朴素,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周书》本纪)。
北朝统治者的这种隔漠心态是阻碍诗赋这两种美文在北朝充分发育的重要原因。南朝文坛上诗赋两种文体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在北朝并没有大规模出现。在北朝文坛上,散文的成就总体高于诗赋,也就不足为怪了。二畏祸心态与诗赋文体的复古倾向北朝士人的政治焦虑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是险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一种紧张情绪。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限度,必须要释放出来,才能保证士人心理的平衡。其实,从中国士人阶层产生起,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角色(民、官、文化承传者),政治的焦虑就是士人阶层的基本焦虑之一了。因为士人阶层除了知识以外一无所有,因此,期望从根本上改变外部政治环境,实现自己入仕的理想或改变仕途受挫的境遇,以消解政治焦虑是不可能的。从先秦到南北朝,士人阶层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消解政治焦虑的方式,那就是诗化的士人自我超越。中国古代士人的自我超越具有内倾的特点,它是士人心灵借助文学趋向宁静平和的过程。孔子说:“诗可以怨”;司马迁也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少卿书》)。文学,尤其是诗歌,是士人完成自我超越,消除政治焦虑的最好手段。这一点,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也有很深的体会。钟嵘的《诗品·序》说得好: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之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可见在南北朝士人心目中,不仅人生的喜怒哀乐之情可以借诗歌来渲泄,而且现实世界的其他种种挫折也可以借助诗化境界的营造而得以化解。北朝士人政治焦虑的消解,主要是在诗与赋的创作中营造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一种被美化和装点过的历史的空间。这个消解方式对诗赋关系形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士人诗赋创作中的咏史寄慨模式。这又形成诗赋在语体上的复古倾向。咏史寄慨是中国古代士人消解基本焦虑的惯常方式,北朝士人也不例外。咏史寄慨造成诗与赋在语体风格、句式、声律等方面共同的复古倾向。从诗歌创作方面说,北魏前期的诗歌复古的倾向最为明显。北魏中后期及北朝后期,虽然南朝文学对北朝文学的影响日益深入,但是在北朝文坛上,复古的创作倾向仍然存在,比较典型的作家如高允、韩显宗、常景、郑道昭等人。他们中间,有的人亲历崔浩国史案,以及汉族士人(包括汉化胡人)遭迫害的惨状;有的人则仕途受挫,才高见弃或沉沦下僚,灰心丧气。对他们来说,内心的恐惧、苦闷在现实中是无法消除的。这些无法消除的焦虑,迫使士人转而追求内心世界的营造,将焦虑的心态在文学创作中诗化或淡化。高允早年曾和崔浩一起修史,北魏初年所作《答宗钦诗》十三首,表达了对身在北凉的宗钦的思念。公元439年,北魏攻破北凉,宗钦随之来到平城,作者十分兴奋,在诗中写道:在昔平吴,二陆称宝。今也克凉,吾生独矫。道映儒林,又为群表。我思与之,均于缟。这些诗采用四言体写成,古朴真切,体现了北魏初期诗歌的普遍状况。《征士颂》作于太和初年,上距崔浩国史案发虽已二十多年,但士人的恐惧心理仍然存在。在《征士颂》序中,作者战战兢兢而又无不沉痛地写道:昔岁同征,零落将尽。感逝怀人,做《征士颂》……日月推移,吉凶代谢。同征之人,凋歼殆尽。
在者数子,然复分张。往昔之忻,变为悲戚。张仲业东临营州,迟其还返,一叙于怀。齐衿于垂没之年,写情于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复至陨没。在朝者皆后进之士,居里者非畴昔之人。进涉无寄心之所,出入无解颜之地。顾省形骸,所以永叹而不已。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长言寄意。不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于心,岂可默乎?从这段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北魏统治者的文化恐怖政策下,士人阶层“凋歼殆尽”的残状,以及笼罩于幸存士人心灵深处的痛楚和恐惧。崔浩国史案后,高允“不为文二十年矣”!可见其惧怕之深。“然事切于心”,“事”盖指崔浩等北方士族被诛等一系列事件。这些事积聚心中,不吐不畅。所以做颂“长言寄意”。作者要“寄”的“意”,就是对被杀害的崔浩、游雅等士族文人的悼念,和自己被恐惧情绪长久地折磨,而又无处发泄的苦闷和焦虑。在颂的末尾,作者说:“披巾散想,解带舒怀,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静言思之,中心如摧。挥毫颂德,潸尔增哀。”也说明了作者作“颂”的用意。作者用颂体来“寄意”,也是有其惧怕文祸的心理背景的。颂体一般用于歌功颂德,用颂体之名,行寄意之实,也不至于有撄逆鳞之忧。在序文末尾作者说:“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长言以寄意。”可以看出作者在特殊的心理背景的支配下选择文体以渲泄内心焦虑的苦心孤诣。《征士颂》表面上是歌颂北魏前期统治者“登延俊造”“梦想贤哲”的功德,实际上是对崔浩、卢玄等四十多个士族“冠冕之胄”的惨遭荼毒表示哀悼痛切之情,也是对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悲愤恐惧的渲泄。一定的社会心理通过对创作主体的作用,可以吁求相应的文体。童庆炳等《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一书对于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索,书中说:“对创作主体来说,外部的社会心理作为他的内化对象,重复作用于他,当这种重复达到一定数量时,外部的社会心理内化到他的头脑中,成为一种概括化、言语化的、简缩化的‘情结’。”“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心理作为一种题材,就会吁求艺术形式,吁求真正的理想的形式,以促使题材(社会心理材料)向真正的艺术作品转化。”(4)高允的政治焦虑心态在北朝具有代表性,因此他们的诗赋创作采取咏史、怀古、忆旧以寄托己义的间接深隐的语体就不足为怪了。高允的五言诗《罗敷行》《王子乔》也是仿古之作。有的学者指出《罗敷行》是模仿《陌上桑》和曹植的《美女篇》。(5)《王子乔》则是借歌咏仙人寄托自己对现实的厌倦之意。形式上也刻意模仿汉乐府民歌。诗歌语体的复古倾向还表现在韩显宗的作品中。韩显宗,北魏昌黎棘城人。性刚直,有才学,能言敢谏。随孝文帝南征,屡建奇功。后因恃才傲物,被免职。诗人心中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因赋《赠李彪》诗一首,以贾谊、董仲舒才高被弃自比,以平心头之怨。诗云:贾生谪长沙,董儒诣临江。愧无若人迹,忽寻两贤踪。追昔梁阁游,策驽厕群龙。如何情原夺,飘然独远从。痛哭去旧国,衔泪届新邦。哀哉无援民,嗷然失侣鸿。彼苍不闻我,千里告志同。太和二十一年,即公元497年,诗人随孝文帝南征,旋归被免,作此诗。作时约当南朝齐永元年间,上距“永明”末年约四五年左右。这时在南朝诗坛上,正是声律说盛行的时候;北朝诗坛上则是北朝诗人努力模仿南朝诗风的时期。《魏书·成霄传》载成霄“好为文咏,但词采不伦,率多鄙俗……知音之士,共所耻笑”。可见当时北朝文人,知音者已不在少数。而韩显宗的这首诗,从声律上看,仍然很古朴。除避免了沈约所说的“上尾病”外,诗句的平仄并不讲究,甚至连最起码的声律因素:句中的“二、四、六分明”也没有考虑。从诗的构成上看,全诗七联十四句,这种形式在汉魏时还能见到,但在当时的南朝文坛上已经很少见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朝文学总体上比较落后所致,但主要还是与北朝士人的焦虑心态有关,设想他们激愤之情充斥于心,在正常情况下又不能得到宣泄,只能以诗赋来咏史寄慨,这样的创作,必然会“情”胜于“文”、“质”胜于“文”。在情感的抒发和文体形式的经营上,首先考虑的是前者。北朝的辞赋,大多数直承两汉,并不取法魏晋及南北朝,这还与北朝士人渴望南北统一的心理有关。汉代武功强大,服四夷,一天下的宏伟时代精神,在北朝士人处于文化和人生的双重重压时,不能不说是一剂精神的安慰剂。因此他们的诗赋在文风上直追两汉,又多咏汉代故事,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