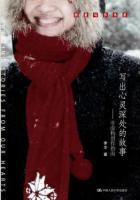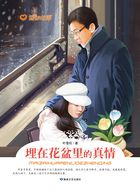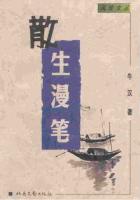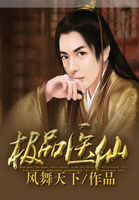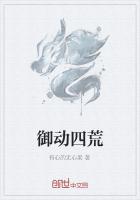輸寫其流落患難無聊之情,而怡然有恬愉閒雅之度。如《書懷》《紀夢》《寄友》等篇,莫不理趣幽遠,其味悠然以長,幾迫古作,非胸中有書者不能爲,亦非淺之爲章句者所能到也。{《秋聲集》卷五}
這裏的修養包括德行與書本兩方面,正是基於這樣的修養,所以其雖遭患難而性情中和,性情閒雅,故其趣幽遠,其味悠長。
我們在對有節與有餘的分析之後可以發現,宋代詩學中的有節與有餘觀念事實形成了一個紡棰形結構,即總起來看爲兩頭大,中間小的結構:蓄積的有餘(即范溫所說的“韻生於有餘”)與效果之有餘(即范溫所說的“有餘之謂韻”)構成兩頭大,而要求表達有節(簡易、含蓄)則構成中間的小。
第二節 中和與平和
蓄積而後平淡,平淡而餘味無窮還涉及了文與質的關係。宋代文質觀念有兩種思路:一是內容與形式,而文質中和即要求內容與形式的參半,這與前代沒有太大的差別;二是華麗與質樸,則無論內容與形式皆可能有華麗與質樸的不同。宋代詩學標舉內容的繁富與形式的質樸,這是具有宋代特色的文質中和,此亦可以相通於平淡而餘味無窮的表達原則。
我們知道漢魏六朝以來的尚藻麗文風一度使表現層面遮蔽了本質的真實,先組麗而後平淡的理論緣于宋代要求剝去華彩,以圖靠近本質真實的努力。但是文學發展並不僅對藝術技巧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言,人類的思維與感情也是在由簡樸向復雜發展,這就決定了宋人不可能再回到《詩經》那樣的環境中去,而只能將《詩經》作爲一種詩學理想的標誌加以標舉。顯然無論是單純的尚質,還是單純的尚文,都會使詩歌陷入危險境地,所以宋人要求文質中和也就有了時代的意義。
宋代的文質中和並非是傳統修辭學意義上的文質參半,而是要求形式的質樸與內容的豐富。“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都是追求“先組麗而後平淡”,這時的組麗與平淡的關係雖是一前一後,但事實上可以理解爲內容的組麗與形式的平淡。所以我們可以說宋代的文質中和觀成了內容的豐富與形式的質樸,這與前代的文質參半有著很大的不同。
一、文與質
我們知道文質中和觀念最早見於《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晏《論語集解》引苞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孔子雖然這裏談的是君子爲人之道,但此語實對後世爲文有深遠的意義。{因爲最初的“文”觀念,君子之風與六經之文一樣都是屬於“文”的,所以論人亦可移至論文。}《禮記·表記》:“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是從“情”“禮”關係講的,雖講的政治,但精神完全可以相通。《論語·八佾》又表示“繪事後素”,可見在質與文雖說應並重,但還是有前後之分的。
文質彬彬作爲一種表達理想,一直被標榜,鍾嶸《詩品》:“吟詠情性,何貴於用事”,“公幹詩氣過其文”。殷璠《河岳英靈集序》:“文質半取,風騷兩挾”,此“半取”就是指的華質中和,也就是文質中和的意思。但自漢魏六朝以至於唐代,都是以藻麗爲主流,即使出現如陶淵明那樣的平淡詩人,也並未受到重視,即使出現要求文質中和的理論,他們要求的卻在於以華藻寫悲情。
宋代具有尚質的觀念。曾鞏《祭歐陽少師文》謂“絕去刀尺,渾然天質”, {《元豊類藁》卷之三十八}對於歐陽修摒棄華豔,歸於天質的文風表示稱賞。黃文雷《看雲小集*和陶》:“工華不工實,此語我所疑”,陸遊(1125-1210)《宋都曹屢寄詩且督和作此示之》:“淫哇解移人,往往喪妙質”, {《陸放翁全集》《劍南詩稿》卷七十九}皆表示重質而輕華。但宋人並不是不講華彩,華彩是“文”本身固有的含義,完全排開文而尚質,是文學所不能允許的。楊萬里《洮湖和梅詩序》:
梅之名肇於炎帝之經,著於說命之書,召南之詩,然以滋不以象,以實不以華也。豈古之人皆質而不尚其華歟?然華如桃李,顔如蕣華,不尚華哉?而獨遺梅之華,何也?{《誠齋集》卷七十九}
即表示華彩不可棄。只是這種文還得以質爲先決條件。張九成(1092-1159)《橫浦心傳》卷中釋:‘繪事後素’時說道:“大抵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必先有其質,方可從事於外,豈有先繪衆采,而後施素者乎?”{《橫浦文集》附《橫浦心傳》卷中。}所以最好的提法還是文質中和,也就文質彬彬。
由此出發,宋人多有要求文質中和者。鄭獬(1022-1072)《劉舍人書敞》:“然翶之文尚質而少工,湜之文務實而不肆。張籍歌行乃勝於詩,至於他文不少見,計亦在歌詩下,使之質而工,奇而肆,則退之作也。”{《鄖溪集》卷一四}此雖論文,實可移評於詩。李綱(1083-1140)《書四家詩選後》:“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梁溪集》卷一六二}其理論標準顯然就是文質中和。范溫《潛溪詩眼》“詩宗建安”:“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對建安詩的理解就體現了文質中和的觀念,“言直致而少對偶”謂語言接近內容真實,屬尚質;“指事情而綺麗”都指表現接近內容真實,但又不乏華彩,這就是文質並重的觀念體現。王履道《鄄城杜澤之詩集序》:“精深婉約,華而不綺,清而不臒,刊陳而趨新,出險而掇奇,人所甚嗇,而公獨裕。”{王正德《餘師錄》卷三引}劉克莊《敖茂才論詩》:“至質翻如俚,尤臒始似仙”,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七}正是“至”“尤”,才使風格流於一偏。
但宋代的“質”不再是質樸的內容,而是由華麗而歸於平淡的質。陳知柔《休齋詩話》:
人爲之詩要有野意。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惟淵明耳。如太白之豪放,樂天之淺陋,至於郊寒島瘦,去之益遠。
這裏認爲意味自長的前提即是“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始腴”指內容的豐富,“終枯”指形式的平易。這裏的文指內容的豐腴,而質指形式的簡易,二者不再是平面的“彬彬”,而是由文而返歸於質,所以表面看來是質,但卻有著內涵的文,所謂“平淡而山高水深”。因爲這裏的質是對超越了文質以後而得到的質,即“千煆萬煉以歸於平易”, {道璨《柳堂外集》卷三《營玉澗詩集序》}所以質內在地包含了文。這就是宋代特色的文質中和觀念。
文質在外現層面上體現爲質樸與華彩的關係,但由於外現的質樸直接來源於內容的質樸真實,所以文質關係又常用來指內容與形式的關係。那麽由文質關係可以引出語與意、語與情、語與理等與文質關係相類似的關係問題。
在語意關係上,主張“理得而辭順”,與文質關係相似,都在於強調質對文的主導地位。黃庭堅《答王觀復書》:“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要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表示理對辭的主宰作用,並注意“意”的有餘。陳亮《書作論法·意與理勝》: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文彩詞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大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類拔萃。{《龍川集》卷一十六}
此雖論文,其理實可通於詩。他認爲“寕不足於辭,而有餘扵意”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〇《張文學詩卷》},其意即在於強調質對文的統領地位。姚勉《送黃強立序》謂:
文之所以妙者,意也。意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有盡而意無窮也,夫意無窮而後文有味,意非文之所以妙乎?雖然,意必至於理,理至焉,意次焉。{《雪坡集》卷三八}
這裏的“意無窮而後文有味”與范溫“有餘之謂韻”說的是一個道理,要求詩歌首先應該做到文盡而意豐,也與《滄浪詩話·詩辨》所謂的“言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互證。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下:“言淡而旨遠,決非汨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言淡則指言簡,旨遠則指味長,用文質範疇來表述則可謂爲文約而質豐,宋代詩學的文質中和觀特色即在於此,即外在的質包含了內在的文,換言之,則爲內在的文以質的形式外現。這樣的文質中和當然不同於宋代以前的文質彬彬。
但是前代的文質彬彬觀念在宋代仍然存在。宋代對重語辭而輕意理的創作態度表示批評就體現了重質的觀念。張鎡《仕學規範》卷三十九引歐陽修語謂:“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論文》:“崔德符《魚詩》云:‘小魚喜親人,可鈎亦可扛。大魚自有神,出沒不可量。’如此等作甚好,《文鑒》卻不收,不知如何?正道理不取,只要巧。”
但宋代詩學並不輕視語辭。劉克莊《張文學詩卷》:
意本也,辭末也,然聖門之論曰‘辭逹而已矣’,又曰‘質勝文則野’,辭亦豈可少哉?{《後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一〇}
表示辭亦不可輕。但是重文或是重質都會帶來偏激,如王正德《餘師錄》卷四“李翺”謂:
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並,乃能獨立于一時而不泯滅于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尚質而去文與尚文而去質皆陷於一偏,最好的表述還是中和。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元白張籍以意爲主,而失于少文;賀以詞爲主,而失於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