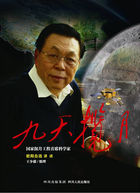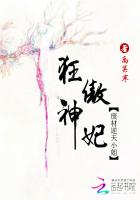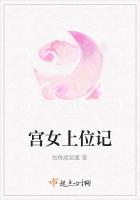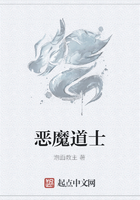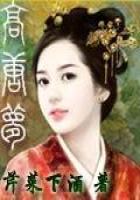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吟詠性情爲詩之本旨,宋人認爲詩歌爲性情的自然流露,性情不僅可以穿透時空,如陳藻所謂“詩,情性也,古今一也”,而且也可以穿透作者與讀者的隔閡,“以今之情性求古之情性,則奚有諸家之異同哉?” {《樂軒集》卷六《詩》}但這裏的性情必須是合乎要求的性情,也就是說性情應該中和平和,樓鑰所謂 “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攻媿集》卷六七《答楊敬仲論詩解》}所以詩中所流露出的性情也應是平和的。對於這種平和的性情,讀詩者當然也應以平和的心態去理解它,而且應該從這種平和性情流露的詩歌中得到啓示,受到薰陶與教育。正如韓淲(1159-1224)《澗泉日記》卷上評呂本中所謂“評詩論文,必歸淳雅”,詩歌的品鑒其最終的目的也在於得性情之正。
中和性情的表現往往是平淡的。表達平淡與置心平易從創作到接受都以平易爲要求,張載的“置心平易始知詩”成爲宋人談詩論詩的普遍心理要求。與宋代的平淡詩觀相聯繫,平淡並不是枯槁,平淡與餘味無窮是不可分離的。與餘味相應,宋代詩學要求以涵詠諷誦、熟讀玩味來加以體會。我們可以看到宋代心性中和詩學在接受層面的回應。在此宋代中和詩觀終於達到理論的圓滿,即從天、人、詩關係的探討到對詩歌創作本身的探討,再從對詩的品味中體驗人格的魅力以及與天道的合一。
第一節 無邪之思
我們在前面已經多次提到宋代對人與詩的關係的重視,他們認爲詩歌應成爲人的真實寫照,應該反映出詩人自身的人格修養以及他們對世界的體悟。這樣宋代詩歌就成爲理想人格的流露,而我們所謂的理想人格就是中和性情。宋人認爲這種中和性情自然流露於詩中,詩成爲這種中和性情的載體,具有了承載與運載的功能。宋人標舉流露出中和性情的詩歌。陳藻《綿亭楊氏子名字序》:“詩三百,思無邪,無邪者誠,誠者中,中者仁,此詩之至也。”{《樂軒集》卷五}認爲性情的中和是詩歌最爲重要的條件。而柴望(1212-1280)《道州台衣集原序》所謂的“學詩四十年,吟詠數千首,求其優柔和平,哀樂中節,可以詔將來,有關乎世教者,蓋百不一二也。”{《秋堂集》附錄}可見性情中和一度成爲詩人們終生追求的目標。
宋代人以《詩經》爲詩歌的典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詩經》所流露出的性情被認爲是“思無邪”的。我們知道《論語·爲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成爲宋代詩學思無邪論的依據。同時《論語》“子曰:《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認爲《關雎》流露的性情中和。《關睢》位於《詩經》之首,也是國風之首篇,可謂爲詩經的代表篇目,《關雎》的性情中和也應可以看作是《詩經》性情中和的代表。
宋人廣泛認爲《詩經》是思無邪的,如楊簡《慈湖詩傳》卷一十五《漸漸之石》:“是詩正矣,無邪思也,無邪,道也,孔子取焉。”宋人屢屢表示對《詩》的無邪之思的向往。宋代並以此爲期人之勉,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十《題勿齋曾魯詩藁》:“勿夫子語顔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而後可。曾君魯擇言未爲不精,尚勉之哉!”
一、宋代詩學對《詩》思無邪的闡釋
我們知道漢儒對思無邪的理解表現在《詩大序》中:“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以禮義爲詩中所發抒之情的限定。雖然《詩大序》說的是變風,但由於《論語》認爲《詩經》總體上是思無邪的,所以有理由認爲發乎情止乎禮義應是合乎“無邪”的要求的。魏晉南北朝思無邪說衰微,《文心雕龍·明詩》:“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主要指的是詩之本身的無邪可修持人之性情,對於無邪並沒有明確的說明。宋代詩學重視詩人之性情的修養,對“思無邪”進行了種種闡釋。
《詩經》中內容多樣,流露性情並不整齊一致。詩三百篇中畢竟還有許多或怨憤或嬉戲之詩,正如李衡《樂菴語錄》卷二所謂:“且如《桑中》、《牆有茨》、《東門之枌》之類,皆具道閨房****之事”; 段昌武《毛詩集解》卷首《學詩總說*作詩之理》引永嘉戴氏曰:“今《詩》中亦有自敍其嬉戲之樂,嘲謔之辭”,這些似乎算不得 “無邪”,對思無邪進行闡釋,宋代詩學必須對此作出合理的解釋。
(一)漢儒所亂
極端的看法就是漢儒所亂。方岳(1199-1262){另有方岳(約1252年前後在世),字元善,有《深雪偶談》存世,當注意區別。}《回趙子淵》謂:
嘗鼎一臠,則《牆茨》諸詠,似若以人倫之逆自相報復者,此殆不可以訓。孔子刪詩,何取乎刪也?傷風敗俗之辭,不可以明示天下來世者,則刪之耳。《牆茨》諸詩,所謂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蓋父不敢以訓諸其子,師不敢以淑诸其徒者也。某意其決在刪例。何以言之?《記》《禮》《左氏》諸書所引逸詩,其辭皆雅正,而夫子猶刪之。則淪三綱、斁九法如《牆茨》諸詩,刪之決也。夫子之言詩曰:思無邪。若諸詩者,其然歟?某決以爲黷亂如《牆茨》之比,淫奔如《桑中》之類,皆夫子所刪之詩也。删之矣则曷爲存秦火之燼,漢儒亂之也。漢儒奚其亂之火於秦者,不能盡記而孔子所刪之詩流傳習熟於人之口耳者猶在也,亡者不可復,則取其在者以足之耳。此漢儒之罪也。{《秋崖集》卷二十六}
但是象王柏那樣直接改動《詩經》的人畢竟不多,這種看法只代表了少數要求純正的“思無邪”的極端觀念。
(一)止乎禮義
變通的一種看法就是無邪即爲合乎禮義,如唐仲友《詩解鈔*四始六義》:
夫詩者,有感而作,心之發也。先王之民雖甚卑賤而僻陋者,其言猶若是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子刪詩之法也。發乎情故有思,止乎禮義故無邪。詩非必聖人之所作,而聖人斷之者也。
明確表示無邪就是止乎禮義。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詩序》:
詩三百篇,不爲不多矣,而孔子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蓋取其直已而發,粹然一出於正,風雅雖變,而思之無邪則一而已矣。
這裏的“直己而發”、“一出於正”指的就是性情之正,義理之正。陳埴《木鍾集》卷二《孟子》“詩可以怨,當怨而怨,不害於義理之正。”認爲詩經雖然有怨,但是其怨是義理之中,也就是“當怨而怨”,所以也可以算是思無邪。這裏的思無邪指的是義理之正,而邪就指的是違背義理的性情了。段昌武《毛詩集解》《學詩總說*作詩之理》引黃氏曰:
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大序》亦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曰思曰情,則有喜有怒,有哀有樂,而思曰無邪,情曰止乎禮義,則《記》所謂中節而和者也。今觀諸詩,其盛者言后稷先公之風化,文武成康之盛德,溫溫乎其和可知,而其變風,變雅之作,雖愁困哀思之中而亦有惻然愛君之意,則所謂喜怒哀樂之中節者,於此可證。
這裏指出思無邪就止乎禮義,也就是性情中和,並不是詩中發抒性情不能有喜怒哀樂,只是喜怒哀樂應該合乎禮義的要求。變風變雅之作,雖有怨愁哀思,但其中有愛君之意,其中雖有喜怒哀樂,但這種喜怒哀樂是合乎禮義的,也就是發而皆中節,這裏的節也就是義理、禮義,所以也就是思無邪的。
(三)作詩者意在勸戒
但是以上只是停留在對作者的性情流露上,雖可解釋變風變雅的愁困哀思,但仍不能解釋《桑中》等詩的道****、敘嬉戲之詞。稍爲通達的看法是將《詩經》的性情放在教化的環境中來攷察就顯得可以理解了,也就是將詩經的取捨原則與說詩者的選擇聯繫起來。楊簡《慈湖詩傳》卷四《桑中》:“詩無邪,《桑中》非淫者之辭,乃刺者之辭。”認爲《桑中》雖然寫的是淫者之辭,但是作者目的實在於勸戒,所以是合乎“思無邪”的原則的。朱熹將這種情況解釋爲:“彼以無邪之思,鋪陳****之事,而閔惜征創之意自見於言外”。{《朱文公全集》卷七〇《讀呂氏詩紀桑中高》}這裏仍然就作者流露的性情而言的。
(四)讀詩者之思無邪
這裏認爲《詩經》的原作者所流露的性情雖然看起來是有邪,但其目的卻在於勸戒,所以還是無邪的,這種思路仍然難以解釋鄭衛之音中的男女淫奔之詩,於是性情中和更多地向接受一方側重。朱熹說:
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之事,而閔惜征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征創之資耶?{《朱文公全集》卷七〇《讀呂氏詩紀桑中高》}
這裏認爲“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即謂即使作者之思爲有邪,但只要讀者之思無邪,也可合於思無邪之原則,也是與聖人之旨相合的。從作者思無邪,到讀者思無邪(作者即使思有邪,而讀者亦可存無邪之思以讀之),我們可以看到思無邪向讀者一方的側重。
在此我們將宋代中和詩觀對讀者的性情要求引出就顯得順理成章了。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十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謂
此一言,《魯頌·駉篇》之詞也,主于思馬而言。夫子讀詩,至是有感而取之,以斷三百篇之義。非以三百篇之詩,皆止乎禮義而粹然一正也,如變風鄭衛之詩,不止乎禮義,而逸於邪思者亦多矣。聖人之意,直以詩有美惡之不同。其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惡志,所以指歸,不過欲人使人得情性之正而已。故惟此一言,簡要明白,可以通貫全體而盡蓋三百篇之義,因特表而出之以示人,可謂切矣。則讀詩者,右不深體以爲切身之務而徒諷誦之云哉?然詳玩是言,雖約而爲義甚博,蓋誠之通而大本之所以達也。豈但讀詩之法爲然,凡讀書窮理,治心修身,無適而不可,學者誠能深味其旨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爲千條萬緒,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陳淳將朱熹的讀者之思無邪觀念發展到治心修身,更涉及到了品鑒的意義所在,雖然他說的儒家的修身之用,但對於我們今天的文學品鑒所謂的陶冶作用也是可以有所借鑒的。
我們說過,詩歌作爲中和性情的載體,起到承載與運載的作用。當被讀者讀到時,意味著這種承載和運載到了接受者的一方,接受者一方被認爲是這種中和性情的接受者,也是創作者中和性情的印證者,這樣的積極的接受方式當然要對接受者本身進行要求。思無邪這一原則也被用於接受者了,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也是宋前所未見到的。陽枋《與蘇坤珍書》謂
‘無邪’,不只是作詩者‘思無邪’,而誦詩者亦當‘思無邪’方得。不然詩只是古人言志底,何益哉?所謂不能無疑且闕之,看來看去,疑者終亦不疑矣,只須取其爲我用者,深玩潛體,其餘差舛不必深較徒費工夫虛度時日,大閫之招已辭之矣。”{《字溪集》卷三}
可謂一語道破天機。{自漢代以來詩歌的接受者往往又具有闡發的責任。本章的討論將誦詩者、解詩者、說詩者一並認爲屬於
品鑒類,這是要先進行說明的。}所謂的以無邪之思讀之,也就是要求讀者的性情合乎要求。只要讀者之思無邪,即使詩作本身思有邪,亦無妨礙。正如李衡《樂菴語錄》卷二引王居正曰“觀人之言,系乎心術之邪正。”而“道本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所以“非特明作詩者之思慮不及於邪,亦欲使讀者其心術不可不出於正也”。對讀者的無邪之思的要求就成爲宋代中和詩觀品鑒論的重要內容。
但其間還有一個轉變過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五“桑中”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指的是作者思無邪,讀者亦須思無邪。陽枋《與蘇坤珍書》:“‘無邪’,不只是作詩者‘思無邪’,而誦詩者亦當‘思無邪’方得。” {《字溪集》卷三}要求讀者思之無邪與作者思之無邪的一致。而朱熹的觀點則在呂氏與陽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指出即使作者思有邪,只要讀者思無邪也可合乎聖人之意。其意在於以讀者之思無邪來達到對作者思有邪的超越。在朱熹之前,宋代說詩者皆認爲《詩經》之思是無邪,即使那些怨憤嬉戲之作,表面看來思有邪,但其中作者真正的目的仍在於勸戒,也就是所謂的“喜怒哀樂中猶有愛君之意”,呂祖謙的觀點事實上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觀點,即所謂的“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而朱熹觀點則將思無邪的側重點移到了讀者一方來。這從品鑒論來看,無疑是具有重大意義的。讀者之思無邪超越了作者之思無邪而在詩歌接受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事實他們還把思無邪的接受方要求延展到了其他領域。有謂六經皆思無邪者。陳傅良《止齋文集》卷四
五附錄《文章策》:“昔者甞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
秋》《禮》《樂》也,皆其無邪思也,”可見宋代思無邪觀念的廣泛滲透。}陳埴《六經總論》卷二《孟子》“學詩之人每一章一篇,並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木鍾集》卷二《孟子》}充分認識到讀者性情之正在詩歌接受中的積極作用。
二、讀詩可得性情之正
既然三百篇之義在讀者而不在作者,當以無邪之思觀詩,而觀詩又可促進思之無邪。讀詩成爲修心養性的一種方式,劉翼(1198-?)《戲和劉雪巢題壁韻》:“要識性情根極處,請觀三百五篇詩。”{《心遊摘稿》南宋群賢小集本}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有謂:“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上引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十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進一步表示:“豈但讀詩之法爲然,凡讀書窮理,治心修身,無適而不可,學者誠能深味其旨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爲千條萬緒,莫非天理之流行矣。”皆謂讀《詩》可以修心養性,而得性情之正。與此相反,對於某些詩,人讀之而不得性情之正者,則進行批評。楊時《龜山先生語録》卷二謂:“若涉於訕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指出讀之而怒,不得性情中和,所以此詩不可取。楊冠卿(1138-?)《靜寄樂府序》提到“或者乃謂綺靡之詞,發人幽感,君子病之,不傳焉可也。”{《客亭類藁》卷七}即表示有人認爲讀之而得傷感的詩歌沒有流傳價值。
我們在第二章第三節討論詩以修德時已經提到讀詩而得性情之和,那麽在宋代人觀念中爲什麽讀詩可以修心呢?那是因爲詩有如下幾種作用。
首先是勸戒作用。勸者,進也,也就是鼓勵促進的意思。陳淳說“聖人之意,直以詩有美惡之不同,其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惡志,所以指歸,不過欲人使人得情性之正而已。”即可以對善心進行鼓勵,而對惡志對懲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