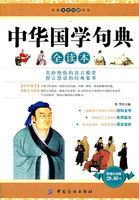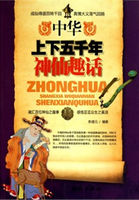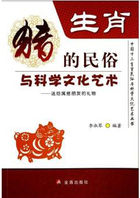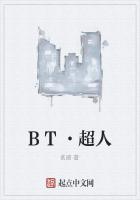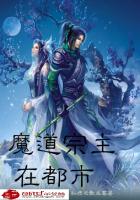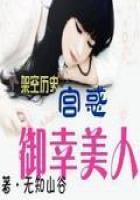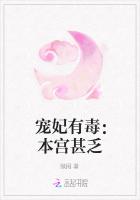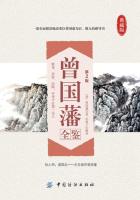动物相食搏斗纹主要表现大型猫科动物吞噬牛、鹿等偶蹄类草食动物的场景。如石寨山3号墓出土的一虎噬牛铜扣饰,一虎跃踞牛背,口噬其肩,两前爪紧抱牛腹,左后爪抓住牛腿,右后爪蹬地;牛身躯略向后倾,张口号叫,其下有二蛇,一蛇尾绕牛腿,另一蛇缠住虎腿,高8.3厘米、宽15.5厘米;同墓还出土狼豹争鹿铜扣饰,鹿被二兽践于足下,作仰卧挣扎状,鹿腹已被狼爪抓破,肠露腹外,狼、豹又展开一场争夺小鹿的恶斗:豹口咬住狼颈,前爪紧抓狼腰不放,狼又咬住豹的后腿,用左前爪抓住豹的腹部,右后爪拨开豹头,左后爪及右前爪紧按小鹿不放,其下有一蛇,蛇口咬住豹尾,高7.2厘米、宽12.5厘米;其他如石寨山3号墓出土的二虎噬猪,71号墓出土的二豹噬猪,13号墓出土的二虎噬牛、一虎背牛,6号墓出土二狼噬鹿,12号墓出土的三虎背牛等同类题材扣饰,造型生动,表现出栩栩如生的场景(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82-94,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在这些扣饰的构图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动物相食搏斗的主要场景之下,往往用蛇的形象来连接,它除了发挥连接扣饰整体,使构图更加紧凑、饱满的作用外,可能还具有某种宗教内涵,是滇文化扣饰颇具特色的一个构思。此外尚有水鸟捕鱼等题材。
狩猎纹猎人或骑马,或徒步,狩猎的对象既有凶猛的虎、豹等肉食动物,也有温顺的鹿等草食动物,既有多人戮力捕杀凶猛动物,也有单人独自狩猎,有的还表现猎犬帮助猎人狩猎的场景。如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骑马猎鹿鎏金铜扣饰,一骑士御马逐一鹿:骑士头缠包巾,着对襟上衣及短裤,跣足,腰间束带,佩短剑,左手控缰,右手上扬作刺鹿状;一鹿仰首扬尾狂奔于马前,其后胯已被马前足踩踏,显然难逃成为猎物的命运,其下有一蛇,蛇口咬住马尾,高10厘米、宽17厘米;著名的八人猎虎铜扣饰,出土于石寨山17号墓,表现六人持矛刺虎,一人被虎撞倒在地,仍用剑刺入虎头,另一人亦倒地,颈部已被老虎咬断,似已死亡;两猎犬扑向虎背,其中一犬咬住虎之颈部,另一犬紧咬虎之后背,八人服饰、发型相同,头顶皆挽高髻,耳佩环,着对襟短袖上衣,跣足,高11.5厘米、宽13厘米;石寨山3号墓出土的一人三犬猎鹿铜扣饰,一猎手左手抓住鹿的后腿,右手上举做刺杀状,一猎犬扑向鹿背,噬其腰部,另一猎犬咬住鹿耳,还有一猎犬伏于鹿腹下,紧咬其腰部,其下有一蛇,口咬鹿之前足,尾绕其后腿,高8.5厘米、宽15.2厘米(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82-94,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祭祀纹其中的动物形象,以牛为多,如江川李家山M24出土的1件,牛角上倒吊着一人,铜柱右侧有一人紧拉牛缰,牛头前有一人被践倒,牛旁立一人,一手按牛背,一手拉栓牛头的绳索,牛后有一人双手紧拉牛尾,场景最下方有二蛇盘绕,左侧蛇头上蹲一蛙,蛇张口吞噬蛙足(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此应为表现剽牛祭祀的场景,在滇文化贮贝器及其他器物上也多有表现。单一动物形象扣饰的种类有牛头、枭、鱼、鲵、水鸟等,以牛头居多。
(二)兵器
滇文化青铜器中,以兵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其中最具特色的、与动物意匠有关的有两类。一是所谓“仿生式兵器”,模仿动物身体的某一部分制作,如鸟头形铜啄,整体似一长嘴的鸟头,其上有两个对称的圆圈,很像鸟的两个眼睛,刃部既长且尖,刃上端有横出的圆銎,便于穿木柄,柄与刃部呈丁字交叉状,使用时如长嘴啄木;又如1件蛙形矛,刃部后端及銎部铸一浮雕的青蛙,两前肢弯曲成双环耳,两后肢下蹲作起跳状,蛙背及四肢上有双旋纹、圆涡纹、回纹及竹节纹等,既刻画出青蛙的生动形象,又巧妙地使其变成铜矛的装饰。其他尚有鸭嘴形铜斧、蛇头形铜叉、蛙形铜矛、鸟头形铜钺等(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页17,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二是大量雕铸立体动物造型的兵器,种类有矛、戈、啄、斧、钺、戚等,构思奇特,造型生动。戈、啄类兵器,动物形象一般焊铸于横銎上,布局不拘一格,既有单体的,又有两两相对的,还有多个动物形象并排的,甚至有表现某种简单情节的;矛、斧、钺、戚等兵器,一般在銎侧焊铸各种动物形象。此类兵器数量颇多,不过很可能不是实用器,而是某种礼器。
(三)杖头饰
此类物品出土时,其下端銎内有的还残存一段木柄,銎上并有对穿的小圆孔两个,当是纳柲于銎中,复用一小圆钉自穿孔内横铆之,使柲不易脱落。晋宁石寨山M19、M20各出土一组,每组皆为七件。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完整的木杖,关于其用途,历来众说纷纭,有仪仗头(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94,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旗杆头,权杖头、手杖头(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页222-224,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等意见。杖头饰的形象,除各种动物以外,尚有人物等。动物形象以牛、鹿、兔、孔雀、鹦鹉、鹰、鸡等为常见。以上三类是表现动物形象最为集中的器型,除此之外,各种立体动物形象广泛应用于青铜器物上,如锄、铲等农具,铜鼓、葫芦笙等乐器,尊、壶等容器以及贮贝器、针筒、线盒、带钩、枕、案等生活用器,等等。另外,滇国工匠还使用线刻、金银错等工艺,在青铜器表面刻画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
可以说,动物形象在滇文化青铜装饰艺术中无处不在,构成了滇青铜装饰艺术的最显著特征。
二滇文化动物意匠与欧亚草原动物意匠的比较及差异
滇文化中的动物纹牌饰,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流行于广袤的欧亚草原的动物纹。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学者白鸟芳郎就注意到,滇文化中的动物搏斗纹和兵器上的动物装饰等,与斯基泰艺术中的动物搏斗图案十分相似,说明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并认为将斯基泰文化传入云南的承担者是汉代的“昆明”,唐代的“昆弥”,近代云南纳西族和彝族的先民(白鸟芳郎:《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中国西南地区所见的斯基泰文化影响》,《民族研究译丛》第1辑,1982年。)。白鸟芳郎先生以后,这个问题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以张增祺先生为代表,同意白鸟芳郎的基本意见,但作了若干修正;另一种意见以美国学者埃玛?邦克(Emma C. Bunker)为代表,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认为滇文化的动物纹植根于本土民族文化。
张增祺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后撰写了系列文章阐述他的观点(张增祺:《关于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上一组人物形象的族属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4期;《关于彝族的渊源及其形成问题》,《民族学与近代化》1986年2期;《云南青铜时代“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考古》1987年9期。),肯定在战国至西汉初,滇国青铜文化中确有部分斯基泰文化遗物(包括当地的仿制品)的存在,并进而论证这些文化信息是由古代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塞人”(亦即斯基泰人),通过青藏高原经澜沧江河谷传入云南的,从而在同意白鸟芳郎滇国青铜文化中确有一部分遗物是斯基泰艺术影响的结果意见的前提下,就传入的中介者及途径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后来,张先生又曾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张增祺:《再论云南青铜时代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及其传播者》,《云南青铜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页274-287,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美国学者埃玛?邦克(Emma C. Bunker)不同意上述白鸟芳郎和张增祺两先生的意见,认为其是偏离事实的假设,遮掩了真实艺术历史的画面(Emma C.Bunker:《滇国艺术中的“动物格斗”和骑马猎手》,赵永勤译,《云南文物》总26期。),其主要理由包括:
1.欧洲东部草原部族艺术中的动物格斗图案,被描写的是一种因袭传统的符号,这只是图腾崇拜的反映。而滇国动物的表现则是非常逼真的写实作品,还没有出现任何可视为符号体系的动物形象。
2.滇国艺术风格中所表现的马背上的猎人,和欧亚草原东部地区骑马猎手的形象不同。滇国骑马猎手用长矛捕猎动物,而内蒙古北方的骑士则是用弓箭射杀猎物。滇国这种在马背上用长矛狩猎的方式,不论在东亚草原和中原地区从未见过。
3.欧亚东部草原上的骑士们,像斯基泰人那样身佩短剑,是用绳子拴在衣带上;而滇国猎人是饰带上挂着剑,饰带又挂在右肩上。这是流行于地中海以及古代近东地区的佩剑方式。
4.在滇国随葬品中,确有一些来自亚洲西北部的遗物。虽然有的学者提出中亚及西北亚的商业人群有的曾向南移居至中国西南部,但这两个地区间的差异很大,如欧亚东部草原的游牧民族穿长袍、毡靴,而滇国居民多单衣、赤脚等,使这种理论缺乏根据。
邦克女士以后,继有一些学者支持她的观点。如田晓雯从滇文化的青铜扣饰与欧亚草原的青铜扣饰在构造与用途上的差异着眼,认为虽然滇文化的青铜扣饰的流行年代晚于欧亚草原,但滇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大体处于同一时代,所以认为滇文化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或将它们一概而论,其根据是不足的,滇文化青铜扣饰的创造者是云南古代少数民族先民(田晓雯:《从青铜扣饰看古滇国的装饰艺术》,《云南青铜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萧明华亦就滇人青铜扣饰与北方和中亚、西亚或斯基泰艺术的动物牌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从制作年代、文化背景、工艺风格、形式和用途等方面考察,它们各有自己的源头和分布范围,各有特定的创造和使用民族,各有特定的用途、独特的风格和各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因此尚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继承、交流和发展的关系(萧明华:《青铜时代滇人的青铜扣饰》,《考古学报》1999年4期。)。邱兹惠也认为,滇文化青铜扣饰上动物格斗的形象与游牧民族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相同点仅止于观念上对动物形象的认知,为青铜时代各从事畜养业的民族所共有,包括斯基泰、匈奴及各氐羌系民族,从风格和图像内容上来说,滇青铜器上各种动物造型当是当地的写生实录,但不乏想象力及创意性,而动物形象表现的极度写实的风格,也当为滇文化特有(邱兹惠:《滇青铜文化多元艺术风格的涵义》,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编《东亚古物》(A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有关滇文化动物意匠与欧亚草原的区别,我们尚可以做一些补充。
就动物形象的种类而言,我们认为,滇文化各类器物上所描绘的动物形象,基本反映的是云南战国秦汉时期的动物区系(Fauna),换言之,动物形象的母题多系滇人日常所见之种类。滇文化器物上反映的动物种类十分丰富,除牛、马、猪、羊、狗等家畜外,尚有虎、豹等大型猫科动物,鸳鸯、孔雀、鹦鹉、鹰、猫头鹰等鸟类,鹿、兔等草食性动物,蛇、鳄鱼等爬行动物,此外还有狼、狐狸、熊、穿山甲、水獭、鸡、青蛙等。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种类为云南独特地理、气候条件所孕育,如猴、鳄鱼,又如孔雀、鹦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谓滇池周边“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其系滇地特产无疑,此类动物形象不见于欧亚草原的艺术品。
有的动物种类,尽管从物种分布的情况看,云南和欧亚草原都是存在的,但仔细分辨,实际还是有一些差异。如在滇文化和欧亚草原的动物形象艺术中,都包括有大量鹿的形象,但从其形态的具体情况分析,可能应属于鹿类动物的不同亚种(鹿类动物是指反刍亚目鹿上科动物,包括麝科和鹿科动物,一般也将鼷鹿上科的鼷鹿列为鹿类。见王利华:《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3期。)。我国鹿的种类很多,仅鹿科动物据统计即有9属16种之多(盛和林:《中国鹿科动物》,《生物学通报》1992年5期。),在古代,生活栖息在我国境内的鹿类动物应更为多样,与人类关系密切(王利华:《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3期。)。滇文化中的鹿形象,如云南省博物馆藏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立鹿针筒(玉溪地区行政公署:《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图版一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两件骑士猎鹿扣饰、铜鹿(玉溪地区行政公署:《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图版一〇八、一〇九、一一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鹿的体形较为粗壮,四肢略短,臀部钝圆且较低,鹿角角冠分三枝,特征上很接近现已濒临灭绝、野生种群仅分布于云南耿马和西盟县边境的“豚鹿”。当然,动物种属的辨别,要考虑艺术表现手法的因素,但滇文化的动物形象,一般高度写实,应当可以反映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看,滇文化的鹿形象,有立有卧,有的被猎人追逐,有的被猛兽撕咬,有的作为兵器等器物的附属装饰,有的单体表现,形态多样,且写实程度较高。而北方草原地区的鹿形象,一般单体表现,形态多为伫立状和伏卧状,在阿尔泰地区的鹿形象中还包括奔驰状的。几种形态中,卧鹿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与斯基泰艺术的关系十分密切,以至被称为“斯基泰鹿”(参见李晓红:《试论北方草原古代艺术中的鹿形象》,《考古与文物》2002年5期。)。在表现手法上,欧亚草原的鹿形象十分夸张地表现鹿角,分枝状的角连至尾部,如克斯托斯卡亚(Kostromskaya)出土的公元前七世纪透雕金卧鹿,鹿身伏卧,长角与尾部相连,角枝呈图案化的“S”形(Tamara Talbot Rice,Ancient Artof Central Asia,p.31,fig.19,London,Thamesand Hudson,1965.);河北省宣化小白阳墓地出土的透雕鹿,昂首伏卧,长角与尾相连(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等:《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7年5期。);又如呼鲁斯太匈奴墓出土的鹿形牌饰,四肢直立,昂头前视,两耳上竖,头上有枝状角联结尾部(塔拉、梁京明:《呼鲁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其他尚有内蒙古准格尔旗速机沟(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文物》1965年2期。)、内蒙古伊克昭盟西沟畔(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等地出土的鹿形象,都与滇文化的鹿形象区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