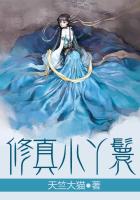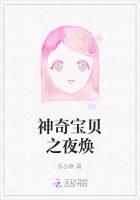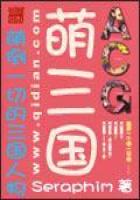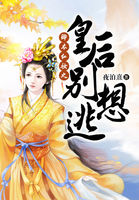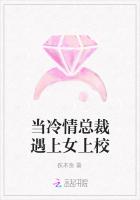对现代汉语合成词的几点思考
合成词是词汇学和语法学都要研究的对象,历来为词汇学家和语法学家所关注。笔者在现代汉语合成词的教学与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些认识,现在写出来就正于诸位同仁。
一、关于合成词确立的理论依据及实际操作问题
对最小的能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词,一般就其结构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单纯词指由一个词素构成的词,合成词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素构成的词。对此人们的看法完全一致。由人们对合成词的理解,我们可以知道合成词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素的组合。换言之,一个词是否为合成词其判别标准就是合成词的本质特征,也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素的有机组合。一个词如果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有机组合而成,那么就是一个合成词;反之,如果是由一个词素单独构成,那么就是一个单纯词。这里涉及了合成词确立的理论依据以及实际操作问题。
我们认为合成词确立的理论依据就是合成词的本质属性,即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素的有机组合,具体来说就是至少存在着两个词素,它们分别以自己的词素义直接地体现了合成词的词义(词汇义或语法义)或间接地体现了合成词的词义。
对合成词确立的理论依据的把握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对“词素”的理解;第二,对词素义的确立及词素义与合成词词义之关系的理解。
1.对“词素”的理解
“词素”(morpheme),有人称之为语素。两种说法稍有差别。用“词素”这个名称的,都认为词素是词内部的单位,是从词里分析出来的;用“语素”这个名称的,不承认词素是从词内部分析出来的,他们认为“语素”是先于词的划分,是比词更为根本的东西,有的不限于构词,也可以加在短语(词组)的前边(如“第”)或后边(如“的”)。词素作为一级语言单位,人们对它的说法不完全相同。如:
高名凯、石安石合著《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认为:“词素就是语言中最小的包含有意义的单位。”
张寿康的《汉语学习丛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认为:“词素就是构成词的具有意义的构词单位。”
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说:“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语素,语素可以定义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
黄伯荣、廖序东的《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说:“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
对词素的说法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对词素本质的理解却已达成共识:第一,它有意义;第二,它是最小的语言(语法)单位。
作为词素必须表示一定的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这“意义”是只指词汇意义(或日概念义、理性义),还是既指词汇意义,也包括语法意义,很多著作语焉不详。不过,从大家对合成词结构的分析以及词根、词缀、实词素、虚词素之类说法中可知词素必须有意义的“意义”既包括词汇意义,也包括语法意义,否则“桌子”“盖儿”之类用附加法构成的词就不是合成词了。
举例来说,“语言”一词,“语”和“言”都是词素,因为它们都有意义。刘熙《释名》说:“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桌子”一词,“桌”和“子”都是词素。因为它们都有意义,只是“桌”具有词汇意义(表示一种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可在上面放东西或做事情的家具),体现了“桌子”一词的基本意义,“子”具有语法意义(作为名词的标志,具有类化作用),体现了“桌子”一词的附加意义。
总之,作为词素必须具有意义,不管这种意义是较具体的词汇意义(或日概念意义、理性意义),还是较抽象的语法意义,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叫词素,比如“玻”“枇”等。
2.对词素意义的确立以及词素义与合成词词义之关系的理解
词素有词汇意义或者语法意义,这是词素之所以是词素的前提。现在的问题是一个词素的意义究竟怎样才能确定?我们认为词素虽然具有一定的表意作用,但常常不能表示一个明确的概念。比如“发”作为一个词素,在“发展、发言、发愁、发放、发源”等词中,表意不完全相同。在“发展”里含有“扩大”的意思,“发言”里含有“表达”的意思,“发愁”里含有“流露”的意思,“发放”里含有“交付”的意思,“发源”里含有“产生”的意思。但如果把“发”这个词素单独抽出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就不很明确了。而且同一个语音形式或书写形式,可能此时是词素,彼时却不是词素,如“布”在“棉布”“布匹”等词中是词素,而在“布尔什维克”“布尔乔亚”“布拉吉”等译音词中只是一个音节符号,根本不具备词素的资格。再如“马”在“马车”“马蹄”“马路”等词中有意义,是词素,但在“马虎”(mǎ hu)中则无意义,不是词素,只是一个音节符号。还有像“子”等符号情形也很复杂,在“鱼子”中读zǐ,是实词素,有词汇意义,而在“桌子”“拍子”“挑子”“盖子”等词中是虚词素,只有语法意义(作名词的标志,有类化作用),读轻声(zì)。
既然同一个符号在甲词中是A意,在乙词中则可能是B意,而且同一个符号还有可能在甲词中是词素,在乙词中却不是词素,只是个音节符号,所以我们认为词素意义的确立应依据特定的词。换句话说一个符号是不是词素,或者是什么意义的词素应由具体的词来决定,离开具体的词,一个符号是不是词素,或者是什么意义的词素是难以确定的。
就合成词来说,构成合成词的词素义应由合成词这个客观的语言环境来决定,反过来合成词的词义也需要其构成成分一一词素的意义来体现,二者相辅相成,辩证地构成一个统一体。
就现代汉语来说词素义体现合成词的词义有如下几种表现:
(1)词素义直接体现合成词的词义(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
a.几个词素直接体现合成词的词汇意义,如:
皮鞋、公审、阅读、停止、改正、缩小、兵变、性急、鼓掌、营业……
b.几个词素分别直接体现合成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如:
老师、第一、念头,硬性、可能性……
其中加点的词素体现该词的语法意义,其他词素体现该词的词汇意义。
(2)词素义间接体现合成词的词义
a.几个词素义揉合起来通过引申、比喻间接体现合成词的词义,如:
脚夫、茶房、拉手、手足、领袖、心腹、爪牙、皮毛……
b.几个词素义通过某个典故、传说间接体现合成词的词义,如:
说项:“讲情”之意,唐朝杨敬之看重项斯,写了“到处逢人说项斯”的诗句,“说项”即由这一典故而来。
染指:“分取非分利益”之意,春秋时,郑灵公请大臣们吃甲鱼,故意不给子公吃,子公很生气,就伸指向盛甲鱼的鼎里蘸上点汤,尝尝滋味就走了,“染指”即由这一故事而来。
根据以上所述合成词确定的理论依据:至少得有两个词素,它们以自身的词素义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合成词的词义(词汇义或语法义),下面我们讨论两个问题:
(1)合成词中的“偏义”词问题
国家、窗户、人物、质量、忘记、干净、睡觉……
这些词通常被认为是由两个词素构成的联合式合成词,而且人们认为其中一个词素的意义完全消失了,如“国家”一词只有“国”的意义,“家”的意义完全消失;“忘记”只有“忘”的意思,“记”的意思完全消失。奇怪的是,很多著作一边说“家”“记”等意思完全消失,一边还说“家”“记”,等是词根(词素),这从理论上讲似乎有点自相矛盾。
这些偏义词既然只有一个符号有意义(即只有一个词素),另一个符号在该词中完全丧失表义能力,既无词汇意义,也无语法意义(即不具备作为词素的资格),那么就不能视为合成词。我们认为这种偏义词应是单纯词。比如“窗户”中的“户”在“户口”“账户”“户主”等词中有意义,因而是个词素,但在“窗户”一词中已丧失表义作用,而沦为音节符号,就不是词素了。根据我们所理解的合成词确立的理论依据,这种偏义词中既然只有一个词素,那么只能认为是单纯词,而不能看成合成词。当然,这种偏义词中丧失表义作用的符号虽然不能作为词素体现词的意义(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但有其存在价值。它作为一个音节符号,起到了“衬字”的作用,保证了该词的双音节形式,从而与现代汉语词汇以双音词为主流的现象合拍。
与“偏义词”一个音节表义,另一个音节表音情形类似,现代汉语复音单纯词中也有一个音节表义,另一个音节表音的情形。其表现主要有两种:
其一,前一个音节表义,后一个音节表音。如:
水螅、妖娆、蹉跎、坎坷、螺蛳、钥匙、黄鹂、蟾蜍……
这些词的前一个符号代表词素,因为它们有意义,其意义与该词词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后一个符号只表音不表义,只是纯粹的音节符号,它们的作用只在于使该词双音化。
其二,前一个音节表音,后一个音节表义。如:
螃蟹、嫦娥、肮脏、侥幸、逍遥、玫瑰、菖蒲、胭脂、砝码、瞌睡……
这些词前一个音节只表音,只是个纯粹的音节符号;后一个音节是词素,它体现了该词的基本意义。此外,复音节单纯词中还有这种情形:某个符号原有意义,代表某个词素,但在语言的发展变化中逐渐丧失了表义功能,从词素转化为音节符号。如:“蚂蚁”“蝴蝶”本为偏正式合成词,“蚂”原本写作“马”,是言其大,“马蚁”即大蚂蚁。后来由于“马”,添了个“虫”字旁(可能是受后边词素“蚁”字偏旁的影响,类推出这么个“虫”旁),“蚂蚁”又变成蚁类的通称,于是“马”原义消失,演变成的“蚂”也就成了纯音节符号了。“蚂蚁”也因而成了单纯词。“蝴蝶”的演变也是如此,“蝴”原本写作“胡”,“蝴蝶”是因其头上的一对触须而得名的,后来“胡”被写成了纯粹的音节符号,“蝴蝶”也就成了单纯词。
我们认为所谓“偏义词”,因为其中一个符号已经从词素转化为纯粹的表音符号了,所以应该看成单纯词。可将它们与上述“蚂蚁”“蝴蝶”“螺蛳”“螃蟹”等一个音节表音,另一个音节表义的复音单纯词视为同类。
(2)音译词问题
通常认为音译词属于单纯词。严格来说这种说法有失严密。音译词多数属于单纯词,但不是所有的音译词都是单纯词。
音译词问题比较复杂,撇开半音译半意译和音译附注类别这些不纯的音译词(半音译词),那种音译的同时又兼顾意义的音译词看成单纯词是不妥当的。比如邢福义先生主编的中学教师培训教材《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将“乌托邦”看成单纯词,这是值得商榷的。“乌托邦”源自英语Utopia,Utopia原义为乌有之乡,是英国ThomasMore爵士在1516年用拉丁文所写书名的简称,后成为空想主义的同义语。“乌托邦”是音译兼顾了意译,显然“乌”“托”“邦”不是纯粹的音译符号,它们也有意义,其意义与“乌托邦”这个词的词义有直接的联系,它们都是词素,因此“乌托邦”作为一个汉语词(来源于外民族,但已汉化,成为汉语的词),应该是个合成词而不是单纯词。
我们认为凡是音义兼顾的音译词都应视为合成词,因为这种已经成为汉语词汇家族成员的音译词每个音节都有意义,因而都是词素。比如:
引擎(engine)、幽默(humour)、维他命(vitamin)、嬉皮士(hippies)、爱滋病(AIDS)、声纳(sonar)、俱乐部(源自日语“俱乐部”kurabu,音译英语club)、绷带(bandage)。
另外,音译词中的人名,当姓、名(有时还有父名、教名)连用时可看成是几个词素组成的合成词。
二、关于合成词结构类型的确立依据及实际操作问题
就复合型合成词来说,其结构类型的确立依据应该是其内部构成成分之间的意义组合关系,而不是外部的语法形式(附加型合成词与复合型合成词确立依据不完全相同,本文暂不作讨论)。否则下面两组结构类型本不相同的合成词就变成相同的了:
第一组:火红、葱绿、笔直、冰凉、雪白
第二组:心酸、眼热、胆怯、性急、心细
第一组与第二组从外部语法形式来说都是名词性词素与形容词性词素的组合,但从内部词素之间的意义关系来说,第一组合成词词素之间是修饰被修饰、限制被限制的关系,而第二组合成词词素之间是陈述与被陈述的关系,因此第一组属偏正式合成词,而第二组属陈述式合成词。
事实上人们一般将复合型合成词分成“联合式”“偏正式”“支配式”“补充式”等等正是从合成词构成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着眼的。
合成词结构类型的确立取决于词素之间的意义组合关系而不取决于孤立的词素功能,其原因就在于词素之间的意义组合关系决定了词的内部结构。现在的问题是词素之间的意义关系决定于什么?
我们认为词素之间的意义关系取决于该词的构词理据,取决于人们创造该词时对所反映的对象或对象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人们创造该词的目的。请比较几个合成词词素之间可能有的意义组合关系:
拖鞋(1)拖着鞋子(2)用于拖脚的鞋子
吊环(1)吊着环(2)吊着的环
围裙(1)围着裙子(2)围在身前的裙子(似的东西)
睡衣(1)睡着衣服(睡在衣服上)(2)用于睡觉时穿的衣服
这四个合成词,它们构成成分之间可能有的意义组合关系都不止一种,如果按甲种意义组合关系理解,则为A类结构类型的合成词;如果按照乙种意义组合关系理解,则为B种结构类型的合成词。例如“吊环”,如果意义组合理解为(1):“吊着环”,则为支配式合成词;如果意义组合关系理解为(2):“吊着的环”,则为偏正式合成词。
从理论上来说某个合成词词素之间可能有的意义关系有时或许不止一种,但事实上只能有一种。这种意义组合关系就取决于我们上面所说的该词的构成理据,人们创造该词时对所反映对象或对象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人们创造该词的目的。比如上举“吊环”可能有的意义关系有两种,但是根据其构词理据等我们可以判定第二种理解正确,因为人们认识到这种体操器械是在架子上挂两根绳子,每根绳子下面各吊一个环,人们握住的是这两个“环”,“环”是这种体操器械的特征。人们通过“吊环”这个词反映的正是这种器械的本质是“环”,一种“吊”着的“环”。因此“吊环”一词的意义组合关系是修饰被修饰、限制被限制的关系,即“吊环”应为偏正式合成词,而不是按(1)理解的支配式合成词。再如“挂镰”一词,从理论上来说有两种意义组合关系,一为“挂着的镰刀”,一为“挂着镰刀”。但根据人们创造此词的目的,可知第一种理解错误,第二种理解正确,因为人们创造“挂镰”一词是为了通过这种动作(“挂”)与事物(“镰”)之间的关系来表示对“一年中最后一茬庄稼的收割工作结束”(《现代汉语词典》)的理性认识,而不是用来表示什么样的镰刀。因此“挂镰”只能理解为支配式,而不能理解为偏正式。根据同样的道理,“拖鞋”“睡衣”“围裙”应为偏正式合成词,而不是支配式合成词。
既然合成词不同的意义组合关系决定了不同的结构类型,不同的结构类型显示了不同的意义关系,意义关系与结构类型相辅相成,因此就词典的释义来说,一部好的词典在解释词义时要能暗示出该词的结构类型来。《现代汉语词典》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如该词典对“吊带”“挂钩”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