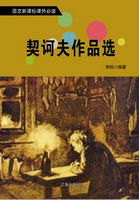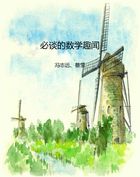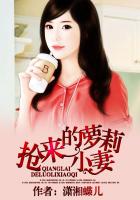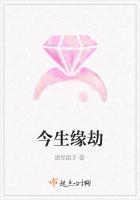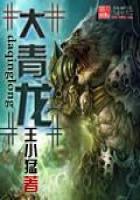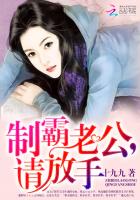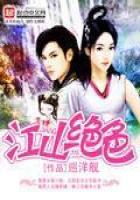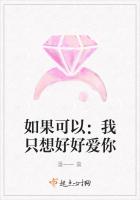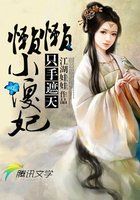我们认为“异称”处于辞格与辞规的中间状态,是辞格与辞规的中介现象。作为从不同的视点、不同的角度给同一个人以不同称谓的修辞方式,“异称”有时可谓魅力无穷,如上引谭永祥先生所举的“兰姑娘”与“慈禧”的例子。有时又可能极其平实,毫无魅力可言,如“********、市人大主任刘伟今天中午在稻香楼宾馆会见了澳大利亚伟力公司副董事长、伟力公司亚洲地区首席执行官李晓燕博士”,此句用“异称”点明了“刘伟”与“李晓燕”的多重身份,追求的是表达的明晰简洁,并无特殊的魅力。有时魅力的有无可能相当模糊,如李准的小说《李双双》的开头:
村里街坊邻居,老一辈人提起她,都管她叫“喜旺家”,或者“喜旺媳妇”,年轻人只管叫“喜旺嫂子”。至于喜旺本人,前些年在人前提起她,就只说“俺那个屋里人”,近几年双双有了个小孩子,他改叫作“俺小菊他妈”。另外,他还有个不大好听的叫法,那就是“俺做饭的”。
这六个称谓指的都是李双双这个人。这六个称谓反映了李双双与周围人的不同关系。这里异称的使用就很难说有多大的艺术魅力。
一般说来在文艺性语体中异称的使用可能会更多地追求其艺术魅力,而在应用性语体、科技性语体中运用异称更多的应是从不同角度揭示同一对象的不同内涵,追求的是平实而不是艺术魅力。
异称的实质,从逻辑学角度来说就是同一关系概念的运用。对同一对象运用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来指称他,如果只着眼于这种指称性,“侧重在理解”,那么此时消极修辞的效果显著,辞规的特征明显;如果在指称的基础上追求形象生动,追求委婉曲折,追求一种动人的意味,“侧重在情感”,侧重在“体验性”,那么此时积极修辞的效果显著,辞格的特征明显。异称的这种辞格辞规的模糊性,或日亦此亦彼性造成了归属的二重性,可归入辞格,也可归入辞规。
异称归入辞格有道理,归入辞规也有道理,因为异称是辞格与辞规的中介现象。当我们对异称有了这样的辩证认识之后,它的归属则是次要的了,是归入此类,还是归入彼类,或是归人第三类都无关紧要。
下面我们试用范畴化理论来探讨辞格与辞规的中介现象问题。
大千世界纷纭复杂,人类面对这纷纭复杂的现实世界,在认识、改造自己生存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范畴化的能力,并以此对经验进行处理、构造、存储,与他人进行交际和交流。从认知的角度来说范畴化是人类高级认知活动最基本的方式之一,“它指的是人类在歧异的现实中看到相似性,并据以将可分辨的不同事物处理为相同的,由此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进而形成概念的过程和能力”。范畴化在人类认知过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因而范畴化问题一直是认知研究的中心。认知科学研究范畴化所形成的两种范畴化理论对我们研究修辞方式应有很多的启示。
两种范畴化理论一为经典范畴化理论,一为原型范畴化理论。经典范畴化理论肇始于亚理斯多德对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的区分。它的一个基本假定是:范畴是根据一组充分必要特征/条件来下定义的,或者说范畴是由充分特征和必要特征的合取定义的。这种理论还有以下这些假定:(1)特征是两分的,某一范畴具有或不具有某一特征泾渭分明;(2)范畴之间有明确的边界;(3)同一范畴内的所有成员地位相等。这种根据共有特征而概括出来的范畴就是特征范畴(feature—basedcategory)。原型范畴化理论是在经典范畴化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范畴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范畴不一定能用一组充分特征/条件来下定义。实体的范畴化是建立在好的、清楚的样本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将其他实例根据它们与这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在某些/一组属性上的相似性而归入该范畴。这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就是典型(即原型),它们是非典型事例范畴化的参照点。这种根据与典型事例类比而得出的范畴就是原型范畴(prototype—basedcategory)。这种理论还有以下假定:(1)实体是根据它们的属性来加以范畴化的,但这些属性并不是经典的范畴化理论中的那种二分的理论构件,而经常是个连续的标度;(2)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不固定的;(3)同一范畴内的成员地位并不相等,有较好的成员和较差的成员之分,较好的成员是该范畴的典型成员,较差的成员是该范畴的非典型成员,最好的与最差的成员之间可有等级之别;(4)范畴中原型性更高的成员具有更多的与同类其他成员共有的属性,并具有更少的与相邻类别的成员共有的属性,换言之,就属性而言,原型成员最大限度地区别于其他范畴的成员,而非原型成员则相反,它们与同类其他成员共有的属性较少,而与相邻范畴共有一些属性。
我们认为已有的修辞方式:辞格的分类、归类工作基本上是以经典范畴化理论为逻辑背景的。例如,采用一两个或若干个认为是充分必要的特征来给不同的辞格下定义;往往认为某一辞格具有或不具有某一特征泾渭分明;常常希望这类或这个辞格跟那类或那个辞格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并且默认同一辞格中的样本地位相等,没有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之别。这种追求整齐划一的科学理想极有价值,指导实际工作也很有成效,但面对纷纭复杂的修辞现象,在辞格的实际分类与归类中经常会遭遇很多难题而无令人信服的答案,甚至有些难题见仁见智,争论难休,成为永远的难题。何以如此呢?我们觉得根本的原因在于辞格不完全是特征范畴。因此,完全用经典范畴理论来规范、导引辞格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不可避免地会面对一些难题无能为力,勉强为之,常常难以圆满。
我们认为辞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原型范畴,它并不是通过某一共有特征而形成的聚合系统,而是通过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类聚系统。辞格内部的每个成员都和其他一个或数个成员共有一项或几项特征,但很难找到一项特征是所有的成员都共有的。辞格的定义难下、类别难分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辞格可谓修辞学研究最主要的内容,但给辞格下定义的著作并不多(被誉为我国现代修辞学奠基之作的《修辞学发凡》就没给辞格下定义),而且这不多的定义也多有不同,不能使人满意,无论是包容性、排他性或明确性上。辞格的定义不一若从传统的经典范畴理论看,它只说明人们对辞格的本质属性认识不一,只能归结为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不一的问题,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或许不只是人们对客体本质属性的认识不一的问题,应还有个客体本身也许不是特征范畴的问题。辞格的定义不尽如人意,也并不是学者们无能,它其实昭示着辞格并不是个真正的特征范畴,而是个原型范畴。
辞格的分类一直是个难题。唐钺的《修辞格》、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等等较早的著作的分类常被认为不尽如人意,原因就是“有的分类,前后角度不一致,分类的结果出现了一些矛盾;有的分类,以偏概全,不那么完整、系统”。也就是说这些名著的分类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标准或角度不一,分类结果交叉;二是不能针对所有的辞格来分类,这其实还是分类标准的问题。这些学者们因为找不到某一个能适用所有辞格的标准(也就是所有辞格共有的特征)来给辞格分类,结果自会产生以上所说的不尽如人意。后来有很多学者一直努力寻找单一标准给辞格分类,如影响较大的吴士文的“特定结构”标准、刘焕辉的“特殊组合”标准、李济中的“表达效果”标准等,然而至今仍没有哪一位学者能做到凭一个标准给所有的辞格分出尽如人意的类别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辞格本不是个特征范畴,凭某一个共有特征来给辞格分类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
说辞格不是个特征范畴,并不是说辞格之间是毫无联系的一盘散沙,而是说辞格作为一个类,不是因为每一个辞格都具有辞格的共同特征,而是因为每个辞格都和其他一个或几个辞格有一些“家族相似性”。辞格正是以环环相扣的方式通过“家族相似性”而联系起来形成类聚系统的。
基于辞格是个原型范畴的认识,我们认为辞格存在着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之别。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有些辞格与其他辞格有较多的相似性,成为辞格的典型成员(典型的次范畴辞格),而有些辞格与其他辞格相似性较少,成为辞格的非典型成员(非典型的次范畴辞格),如“移就”是辞格这个范畴中的典型成员,而“异称”则是非典型成员。从微观上说,在某一辞格的内部也并非绝对同质,存在着典型的成员(较好的样本)和非典型的成员(较差的样本)的差别。例如在比喻辞格内部,异类事物构成的比喻是典型样本,而同类事物构成的比喻则是非典型样本。
辞格是个原型范畴,因而辞格与辞格的界限是交融的,辞格与非辞格的界限也并不泾渭分明。辞格与辞趣,辞格与辞规都存在着中介现象,它们的典型成员因对立而区别,但它们的非典型成员却因相似而有了瓜葛。就辞格与辞规来说,作为修辞方式,它们都具有模式性或规律性。作为修辞方式的两极对立,它们又必然具有区别性。辞格与辞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艺术魅力的有无上形成对立,然而它们各自非典型成员(样本)的存在又决定了二者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交叉,或者说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模糊区域,造成中介现象。
辞格有典型样本与非典型样本的区别,辞规也有典型样本与非典型样本的不同,以辞规“面中显点”为例,其典型样本应为“面”和“点”共现,“面”是显性的。但言语现象中也存在着“面”为隐含的形式,这种“面”为隐性的表达方式就是“面中显点”的非典型样本。请比较:
(1)而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科技人员十分活跃,不但在许多重要的国际学术场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的身影,而且他们也利用一切机会,向世界表达中国科学家的学术观点,参与国际科研活动,阐释中国对世界科技的贡献。(金振蓉、王光荣《我国基础研究正在经历三个变化》,《光明日报》2001.12.28)
(2)他从1920年以来的五年多时间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章希梅《击碎旧世界的惊雷——纪念张太雷烈士牺牲六十周年》,《人民日报》1987.12.10)
(1)为面中显点的典型样本,“改革开放后”为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点。(2)为面中显点的非典型样本,其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和发展”为点,面则是隐含的。张太雷烈士在1920年11月到1925年4月“5年多的时间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发展都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隐含的面),但他从1920年11月组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5年4月这一段时间主要是搞团的工作,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发展做出的贡献更大,因此有必要突出这一点,而且突出这一点表意更加准确、恰当。
辞规面中显点的核心成员是点与面直接相连,直接并列,而实际言语表达中也有点与面间接相连,非直接并列的形式。这种形式也应属面中显点的非典型样本,如下例:
加入WTO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的约束力越来越明显,我国企业家、技术人员亟须更新知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新体系势在必行。外国教育资源的进入,客观上可以满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需要。特别是国外大企业参与培训市场,将会促进中国教育与培训市场的发展与成熟,有利于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郭扶庚《WTO与教育改革》,《光明日报》2001年12月27日)
辞规与辞格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原型范畴,它也不是通过某一共有特征而形成的聚合系统,而是通过“家族相似性”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类聚系统。从宏观上来说,辞规这个类聚系统中存在着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的区别,即辞规的次范畴有的是典型的辞规,有的不是典型的辞规,因此在宏观上存在着辞规与辞格的中介现象,如“称谓合体”之类。从微观上来说,辞规的次范畴——某一具体的辞规其内部往往并非绝对同质,常常存在着较好的样本(典型样本)与较差的样本(非典型的样本)的差别,因此辞规与辞规之间往往也存在着中介现象。例如“明域确延”这个辞规与“面中显点”、“概述细说”等辞规有时就有瓜葛产生:
(1)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选集》第五卷)
(2)书记要听“五种话”——好话,坏话,正面的话,反面的话,反对自己的话,决不能搞个人说了算。(《求是》1990年第2期)
这两例周世烈先生认为属明域确延,但这两例绝不是明域确延的典型样本(明域确延的典型样本,如,“诉讼参与人是指:证明人、鉴定人、翻译人员”),例(1)与面中显点类似,例(2)与概述细说有牵连。这种情况的产生固然与辞规次范畴的界定有关,但也反映了辞规在很大程度上属原型范畴的事实。
我们认为辞格与辞规在很大程度上属原型范畴,承认辞格与辞规存在中介现象,并不是要取消辞格与辞规的界限,也不是主张不必探求辞格与辞规的特征与分类标准,而是意在强调辞格与辞规对立之中有统一,同时也意在强调在修辞方式的研究中既要有非此即彼的思想,也要有亦此亦彼的思想,也就是对待修辞方式需要有个辩证的认识。我们认为对待修辞方式,对其典型成员宜采用“非此即彼”观,对其非典型成员(或日边缘成员)宜采用“亦此亦彼”观;研究辞格、辞规应该重视对典型成员的研究,也应该重视对非典型成员的研究,二者相结合,解释相关修辞现象会更加科学、合理、圆满。
(原载钱进主编《新世纪的中国修辞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部分内容以《辞格分类的原型范畴化思考》为题刊发于《修辞学习》2004年第5期)
有意与无意:某些语言现象辞格与非辞格的分水岭—一兼及某些辞格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