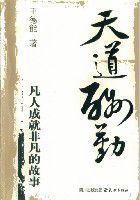因此,在关于黄世仁是债权人:杨白劳是债务人的陈述中,遗漏了黄世仁是压迫者,杨白劳是受压迫者这样一层关系。人们同情杨白劳,同情喜儿,憎恨黄世仁,是不满人权被侵犯。说杨白劳与黄世仁是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只是说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他们还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关系。否定这种关系,不利于我们伸张人权。
所谓压迫,就是侵犯人权的中国式表述。所谓压迫者,就是指利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侵犯人权的施害人。
4
今年4月29日,芭蕾舞剧《白毛女》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上演,二年级小学生宁宁由妈妈带着观看了演出。妈妈的出发点,是想进一步提高宁宁的艺术修养。妈妈对小宁宁很舍得投资,练书法、学钢琴、练舞蹈,打羽毛球、打跆拳道,文武双全了。演出还没结束,宁宁问妈妈:“喜儿为啥不嫁给黄世仁呢?做少奶奶可以吃得饱,穿得暖,不就不用跑到山里这么苦啦?”
据报道说,对女儿的问题,妈妈一时答不上话来。也难怪,时代不同了,有许多在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都成为回答不上来的,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9岁的宁宁所提出的问题来说,在过去,是不构成为问题的。1945年,歌剧《白毛女》首演。初版剧情有一段就如宁宁所希望的那样,喜儿希望嫁给黄世仁,做少奶奶过衣食无忧的日子。可是残酷的现实,让喜儿的幻想破灭了,就在将被卖掉之际,受尽凌辱的喜儿在张二婶帮助下逃到深山里去了。
歌剧上演后,许多民众向创作人员提意见,认为喜儿受黄世仁污辱怀孕后就忘却杀父仇恨,幻想可以彻底委身给黄世仁,不符合喜儿性格的发展逻辑,要求修改。创作人员吸取民众意见,于1946年对剧本进行重大修改,删掉了这个幻想情节,着重突出了反抗主题,从此好评不断。
老百姓为什么受不了喜儿要嫁给黄世仁的幻想呢?老百姓们并不笨,他们知道喜儿的幻想不会有结果。如果黄世仁有要娶喜儿过门的想法,就用不着逼债,直接把那石粮食作为聘礼给杨白劳就行。虽然,逼婚和逼签卖身契,都是坏蛋行为,还是有程度的差别。以目前这样的情景,喜儿到了黄家,充其量也就是当个性奴隶。所以,喜儿要逃走的,并不是一段不如意的婚姻,而是要反抗自己的奴隶命运。
《白毛女》是一出经典剧目。在艺术形式上,它是民族经典。在剧本内容上,它是人性的经典。它的表现手法,是用三个典型人物表征永恒人性的三种反抗方式。首先第一种,是杨白劳式的反抗,以死抗争。这固然是最悲哀的反抗方式,但依然是一种反抗。许云峰在中美合作所里视死如归,就属于这类反抗。第二种是逃跑的反抗。喜儿所表征的就是这种不甘心听天由命地屈从于自己的奴隶命运的反抗方式,敢于逃跑,敢于争取自由。第三种反抗方式更为积极,就是主动斗争的反抗方式。王大春象征了这种积极的反抗。
不同的反抗方式有不同的存在价值,这取决于反抗者的反抗条件。比如赵一曼,当初选择的是主动斗争的反抗,后来被俘,条件改变了,她选择逃跑的反抗,虽然被抓回最后死去,但就是不要做奴隶。像狼牙山五壮士,也是选择以死抗争的反抗方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抗方式,但精神相通,就是不要做奴隶,不屈服于奴役。要自由,要追求光明。
《白毛女》一剧的精神价值也就在这里,这是我们民族最伟大的精神品质之一。敢于摆脱,敢于反抗。中国人一直是最珍视自己的自由与人权的民族,而且,也是最敢于捍卫自己的人权的民族,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可骄傲的民族性格。就是在现在把财富的意义强调到至高无上的今天,人们对那些不甘心被骗去当小姐而逃跑,甚至因此摔断了腿的少女,仍然报予极大的同情,就说明这种可贵的品质仍然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人们赞美的,不是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其实,也许她们本来就不是处女了。人们赞美的,是她们不甘受压迫,不甘受奴役,要主动逃避自己做奴隶的命运的反抗精神。这就是中国人对人权的态度。人权是珍贵的。我们珍视人权,反抗压迫。
有人把内斗作为中国人的主要的民族性格,并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丑陋特征之一。为了支持这些丑化中国人的论调,他们还拿出了所谓的历史证据。中国历史上,一直战祸不断,内战不止。所以,中国人就是爱搞内战,中国人就是丑陋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内战,都是为争取人权,捍卫人权而引起的。这与世界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的内战是一样的。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引起项羽反抗秦王朝的压迫的内战,角斗士斯巴达克思在古罗马的起义,以及美国南北战争,都是著名的奴隶争取人权引起的战争。
因此,用杨白劳来象征老赖,用黄世仁象征可怜巴巴的债主,这样胡乱的戏说是对《白毛女》一剧原创人员的极大的不尊重。本身就是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黄宏的戏说,把原剧最精髓的反抗精神给戏说掉了。
《白毛女》这出戏,说的不仅仅是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债务纠纷的故事。这更是一出关于侵犯人权和捍卫人权的故事。或者用中国式表述,就是压迫和反抗压迫的故事。
5
所谓戏说,就是不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所谈论的对象。
在戏说者的艺术中,戏谑、嘲弄是其基本的表现手段。因此,戏说者在进行艺术表现时,是不会去尊重人们认为应该尊重的表现对象,否则,他们就无法自由地戏说表现对象。而为了获得出人意表的戏说效果,戏说者乐于拿人们所珍贵的东西来开涮。这就像刻意打烂一个漂亮的陶瓷比刻意打烂一块瓦片更引入触目,有更大的乐趣。
多年前的春节联欢晚会有个十分精彩的相声节目,说了一副关于官本位思想的对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相声博得哄堂大笑,大受观众欢迎,这副对联从此风行全国。
文艺作品是精神产品,艺术消费是精神消费。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文化艺术都具有影响人的思想情感的宣传作用,这是否认不了的。尽管这种宣传,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刻意的,但总是存在着的。在传统中,为什么相声、小品均被人们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艺术样式呢?这是由其内容,而不是形式决定的。相声、小品等艺术样式,戏说成分重。戏说倚重于巧智,使人惊奇一下,而不是真智慧。戏说的高见通常只是偏见,而不增加人类的知识,偏见也无助于加深人们对生活及世界的了解。除非带着足够的批判力度,使作品的意义在批判中体现出来,而不是体现在戏说中。戏说只是批判的工具,而不能作为真理。只有这样,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批判精神,相声、小品这样的艺术样式,才可能真正具备登上大雅之堂的条件。
“不服不行”的对联指出了官场上的一些恶霸现象,在人们心中产生了共鸣。但是,整个相声里,批判力度不足,还是戏说的成分多些。这样,戏说就成为偏见,偏见是有害的,把偏见作为真理来宣传,灾难就发生了。
我们都知道,只是在推行“一把手负责制”后,中国的官员们才真正地大权独揽。实际上,在那副对联冒出来之前,虽然官场风气已经出现毛病了,但有不少领导,还是为人正直,敢于坚持原则。可是,经此没有批判的一番戏说调侃后,不少人就统一了思想,以为当领导的就应该这样当。下属的行与不行,全由“负责”的上司的个人喜好来确定。
当戏说上升成为指导性的思想原则,并为学界所推崇,吹捧为“新思维”时,所造成的破坏,恐怕是不可修复的了。这就像一栋大厦,墙身穿了窟窿,补补也就可以。但若基础被挖掉,大厦就只有倒塌。
2002年月12月5日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说,中国教育部新版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逼当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
《大纲》的观点颇有些巧智,虽然冠冕堂皇,却在戏说历史,极不严肃。持这个观点的那些人,虽然口头上称自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俱进。还从语言学、逻辑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搞得神乎其神,但其实连唯物主义的影子也见不到,见到的只有幌子,只有历史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的基本点就是要尊重客观事实。因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人们只有尊重客观事实,才有可能理性地获得对事实的正确认识。关于民族英雄,老百姓的理解很简单,也很直接。他们可能不懂得什么叫民族主义,也没有钻研过这方面的学术论著,也不懂什么语言学的。他们只是把英雄前面的“民族”这个词理解成定语,简单地把岳飞看作是自己的英雄。即所谓民族英雄,就是来自自己民族的英雄,就跟法国人把圣女贞德看作是自己的英雄一样。
其实,用不着复杂的语言学、逻辑学和历史学来搞综合论证,把简单事情复杂化。戚继光、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不能称为民族英雄,这结论显然荒谬,是有历史矛盾的。戚继光是反对外来侵略的吗?如果数百年以后,中国和日本成为一个国家,那时候,戚继光还算不算民族英雄?说岳飞不能称为反对外来侵略,但若数十年后,中国又被分裂了呢?按《大纲》的标准,岳飞的对手,岂不是又变为入侵者了?不要以为这可能性不存在,“****分子”李****一直在鼓吹将中国分裂成七大块,这种论调有国际市场。岳飞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象征,戏说岳飞,否定岳飞,否定的并不是岳飞个人,而是沉淀在岳飞这个英雄名字下的民族精神。
《杨白劳与黄世仁》这个小品的戏说艺术是成功的,也有所批判。但批判的方向不正确,是错误的。在黄宏的戏说下,杨白劳和黄世仁的关系成为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黄宏在此基础上批判了老赖的不道德行为。只从哲学意义上说,黄宏的戏说是唯心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因为,他的戏说没有尊重事实。在《白毛女》一剧中,杨白劳的生活质量在最低限度线上,他不是不愿还债,而是无力还债,因此,一旦突破这条界线,他就只有死路一条。而黄世仁也只有把杨白劳逼往死路,才能强抢喜儿。所以,杨白劳和老赖不愿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来赖债有本质区别,两者根本不可比。
在小品的戏说下,黄世仁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不见了,黄世仁作为一个侵犯人权者,压迫弱势者的形象,被美化了。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人们不再认为侵犯弱势者的人权是错误的,人们也不再认为有尊重人权的必要,这就是戏说所为会为祸的原因。
6
1826年,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写下他的抒情名篇《先知》,其中这样写道:
我怀着焦渴的心灵
在幽暗的荒原上徘徊辗转,
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一位六翼的天使忽然显现,
他又弯下身子,探进我的嘴
连根拔去我罪恶的舌头,
使我再也无法去空谈和狡狯,
接着他以血淋淋的右手
伸进我的痦哑的口腔,
给我装上智慧之蛇的舌头。
然后,他用剑剖开我的胸膛,
把一颗颤抖的心给我挖走,
一块火焰熊熊的赤炭
他给塞进我裂开的心坎。
像一具死尸,我躺在荒原上,
这时候,我听见上帝的呼唤:
“起来吧,先知!听呵,看呵,
让我的意志附在你的身上,
去吧,去走遍五洲和四海,
用我的真理把人心烧亮。”
别林斯基称普希金“是第一个偷到维纳斯腰带的俄国诗人”,像短诗《给克恩》,长诗《茨岗》等,都是极美丽动人的爱情诗篇。读着他的诗,内心会有暖暖的爱意流动,心潮起伏,禁不住要“以颤栗的手掩覆着眼睛”发出长叹:人生怎能没有爱?爱对普希金是重要的,他最后也就是为着爱,为着自己的女人和他人决斗而死。
但普希金心里,不仅装着对女人的爱,他还装着对社会的大爱。在《先知》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内心情感折磨着的人,也就是诗人自己,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有一天在荒原上与天使相遇,天使在他的眼簾上点了一下,给了他先知的眼睛,让他可以从社会的现象看到社会的本质,看到社会发展的未来。然后,天使又在他的耳朵上点了一下,让他能够听到天上的音响,让他内心充满诗的灵感。天使还把右手伸进他嘴里,拔去他罪恶的舌头,使他不能空谈和狡狯。这是一个深刻的象征,普希金把诗人的空谈和狡狯看作罪恶。究其原因是诗人仗着与常人不同的能力,具有了与常人不同的权利,也就有了与常人不同的责任。像“空谈和狡狯”,这些常人的娱乐和巧智,于诗人就是一种罪恶。最后,天使把他的心挖走,换上赤诚的火热。于是,这个在人间的荒原上徘徊着的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方向——用真理“把人心烧亮”。
文艺有他的服务对象,创作文艺作品,肯定要考虑受众的需要。那种认为艺术创作只为满足自己需要,只为表现自己欲望的态度,是骗人的,是对艺术创作的戏说。艺术活动是艺术创作者与活动受众的交流,是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如果艺术只为自己而创作,那就用不着费劲出版,自个儿在家里欣赏就行。把作品出版,就是为了和读者交流,表达自己的意见,听取读者的批评。就像歌剧《白毛女》的最终定稿,就是原创人员和观众相互交流的结果。
但艺术创作考虑受众,并不意味着艺术家应该迎合某些受众的低级趣味,艺术家也并不应该因考虑受众的需要而成为在利益市场上被牵着牛鼻子的逐利之徒。艺术是个性化的创造,但无论是怎样的个性化,艺术活动的宣传功能,使艺术家始终承担着引导受众升华自己情感的责任。诗人应该成为社会的先知,这不是抬举,而是诗人不可逃避的天赋的责任。
当然,可能会有人有些看法,东也责任,西也责任,总是说责任,这样活着,累不累?累,肯定是累的。
但是,仅仅因为累就要逃避自己天赋的责任?这是不是太懦弱,这会不会太没用了?这样的人,又有什么资格称为诗人,并享受诗人的权利?普希金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陀斯妥耶夫斯基甚至被押上了刑场。他们累不累?但他们始终没有改变对自己祖国的爱,没有改变对人民的爱。难道我们的诗人的这点社会意识,要落后人家200年吗?
但愿我们的艺术创作者和学术研究者,还是多一些认真,少一点戏说。诗人是先知,承担着社会的责任;诗人是真理的传播者而不是真理的戏说者。但愿我们的诗人,我们的学者,都能怀着一颗追求真理之心,而不是追求利益之心。但愿我们的诗人,我们的学者,多一点认真,少一点戏说。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有希望些的。
祝福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吧。
200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