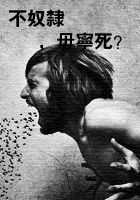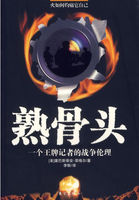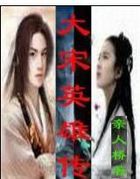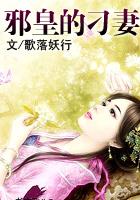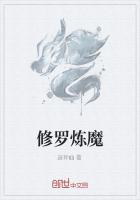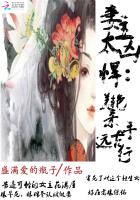1
一个社会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就如同一个社会人的优点和缺点,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能分开。没有十全十美的入,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文化。
在欧洲旧大陆看来,美国文化是粗俗的、野蛮的,完全没有欧洲文化的优美感和高贵感。但在美国人自己看来,他们的文化却是更有活力,也更具创造性。谁更正确呢?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都是正确的。他们只是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去认识同一枚硬币罢了。一个看到了正面,一个看到了反面。这无所谓对或者错,人的优点和缺点,本来就是统一的整体。没有缺点,就没有优点;有了优点,就一定要有缺点。人的本质,就是这样。
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他那本著名的《分成两半的子爵》里,很有意思地表现了这种辩证法思维。小说主人公梅达尔多子爵,因伤被分成两半以后。有一半是专干坏事的,另一半则是专做好事。专干坏事的那半个子爵,邪恶得令人恐惧。而专做好事的那半个子爵,又道德到像个偏执狂一样,令人几乎接受不了。直到两半重新合二为一,梅达尔多子爵才回复了正常状态,于是,有好也有坏,也有了爱情。
卡尔维诺区分善与恶的标准,是不构成为关于善恶的科学标准的。他描述的邪恶的子爵,品质并不全归于邪恶,正如他描述的好的子爵,其品质也不全归于好品质一样。当然,卡尔维诺是无需要对善恶的概念作科学区分。他只是在写小说,行文能出效果就行了。只要读者认为,极端的邪恶与极端的道德,都同样不近人情。只要读者产生这样的感慨,他的文学任务就完成了。
2
对卡尔维诺塑造的梅达尔多子爵这个形象,英国作家佛斯特有个专门的术语,称为“扁平”人物,这种“扁平”人物,是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的。所以,佛斯特又称这种“扁平”人物为漫画人物。
佛斯特认为,用这种漫画式手法塑造艺术人物有一个好处,就是易于辨认。
“如果一个作家想要将他的力量集中使用一击中的,扁平人物即可派上用场。”同时,漫画式的扁平人物性格固定,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读者读过之后就把人物牢牢记忆在脑海里了。就如《大卫·科波菲尔》里面的米考伯太太一样,永远是那一句说话:“我永远不会舍弃米考伯先生。”尽管我们可能不记得《分成两半的子爵》里面的具体情节怎么样了,不记得那个邪恶的子爵是否又做过些好事,或那个善良的子爵是否又干过些坏事,但对那个被分成两半的、黑白分明的梅达尔多子爵的形象,我们是永不会忘记的。
柏杨先生是个杂文家,但也写小说。不知他是否读过佛斯特那本篇幅不大的经典小说评论。如果他不曾读过的话,那是大可不必再读了。倒不是因为柏杨先生现在已经是成名人物,更重要的是,柏杨先生对使用漫画手法来塑造扁平人物的艺术,深得要领,比佛斯特本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记得二十年前初读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那感觉是极度震撼、极度的惊怵。中国文化原来是这样丑陋,中国人原来是这样丑陋,做中国人实在太没劲,做中国人太可恨,真想把自己的皮肤给漂白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好崇拜柏杨先生,觉得他敢于说真话,有眼光,直要拿《丑陋的中国人》来作照妖镜,照出自己丑陋的面目。
但卡尔维诺区分善的梅达尔多子爵和恶的梅达尔多子爵的标准,不构成关于善恶的科学标准。柏杨先生对中国人的评论,也不构成评价中国文化的科学标准。
《丑陋的中国人》只是一本文学作品,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希望一本文学书具有科学的客观性,以图强国富民,是不切实际的期盼。柏杨先生不过是用漫画式的创作手法创造了一个扁平的中国人形象。他完成了他的文学家的任务,艺术手法是高明的,但不构成对中国人的正确认知。
3
高中生上语文课,学习怎样写文章的技巧,语文老师一定会耳提面命地教训说,写文章首先要有个主题。主题是文章的“灵魂”,是文章的“统帅”。没有主题,写什么鸟文章?而且,主题还一定要新颖,一定要说出别人没说过的话来。拾人牙慧,是写作的禁忌。
所以,每一个老老实实地学习写作的高中生,都会老老实实地在写文章前,整理自己的思想,提炼自己的主张,千方百计把自己要发表的意见,形成新颖有力的主题。不然,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不让老师打屁股才怪。
那么,什么是柏杨先生文章的主题呢?
柏杨先生表白说,他演讲的主题“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他要批判中国人,要鞭笞中国文化。因为,对中国的贫穷落后,如果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责怪的话,首先就是责怪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点文化传统。
“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柏杨先生把中国的一切问题,把中国人的一切问题,全归咎于中国文化。这应该是明智的选择。广义地说,文化是社会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文化随人类自身的成长而产生,反过来,又对人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国人的行为特征,自然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所以,从中国人的一些不良习惯入手,批判和鞭笞中国文化,是不会犯常识性错误的。
但如果柏杨先生的文章就只是这一个主题的话,就了无新意了。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开始,批了将近一百年。还能批出些什么新意来?如果再往上数,数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是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当然,秦始皇用的是暴力批判,够坚决的了。而从武批到文批,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应该是没有停止过的。
文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说的和表达的不一样。往好里说,是有艺术性;往坏里说,就是口是心非。如果单凭柏杨先生一句我要批判中国文化,就让他的图书广为流传,从而获得相应的商业利益的话,恐怕是不大可能的。批判中国文化可以成为旗号,但不能成为卖点。对此,市场触角灵敏的出版商,应该最有心得体会。
柏杨先生的卖点在哪里?
4
读《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不可能不为剧中两个青年人炽热的爱情所感动。当罗密欧初见朱丽叶第一眼,他由衷地从心里发出了赞美:
“啊!火炬远不及她的明亮;
她皎然悬在暮天的颊上,
像黑奴耳边璀璨的珠环;
她是天上明珠降落人间!”
有哪一个青年人不这样期盼自己的梦中情人?而当罗密欧挖开坟墓,最后一眼望着朱丽叶美丽而安静的面容时,深情地哀叹道:“眼睛,瞧你的最后一眼吧!手臂,作你最后一次的拥抱吧!”对这最后的时刻,谁又不为之落泪呢?
莎士比亚把他的这出戏剧命名为《Remeo and Juliet》,直白地告诉了观众这是一出爱情剧。但实际上,爱情只是这出戏的旗号,戏的真正主题,是它反封建的倾向。莎士比亚在剧中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归咎于陈旧的封建意识,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向中世纪衰朽而野蛮的伦理观念,指向现实的封建势力。这一主题,与他宣称的并不一样,不是直白地坦露出来,而是艺术地表现出来的。
这就是艺术家的文章与学生的文章的区别了。艺术家的文章不仅有主题,而且还有艺术地表现他的主题的技巧。达到“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俱无”的境界,几乎每部小说都是一个爱情故事,但《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只有一部。只有主题而没有表现主题的艺术,文章就如同是白开水一样了。
柏杨先生说他自己“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从他这番表白中我们可以看到,柏杨先生是既有生活积累,又有创作积累的。即使不及莎士比亚伟大,也是有相当高明的表现主题的艺术技巧的。他知道自己要表达的是什么,也知道怎样艺术地去表达自己要说的话。
比如他说: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
“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
“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
“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入,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
台湾那一块弹丸之地,自然形成不了泱泱大国的心胸。谁会期望台湾人表现出泱泱大国的心胸?不当小偷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可见,柏杨先生说他谈的不是个人,不是政治,是一种艺术的表白。不能信以为真。他这本书,固然不是谈他个人,也不是谈台湾政治。他谈的是大陆的政治,骂的是大陆广大为自己获得解放而欢天喜地的劳动人民群众嘛。一个终生在地里劳作的农民,能有些什么高贵气质,那不是显摆吗?
“十年浩劫使许多入都成了禽兽。”这句话,就更是经典。大陆媒体最爱引用了。瞧着大陆媒体那副德行,有时也真是让人觉得不争气。给人卖了还殷勤地帮人家数钱呢。柏杨先生这一经典结论,不是明摆着骂我们大陆同胞,全都是禽兽养的嘛。
真是高明的艺术,达到诗的高度了。
5
柏杨先生的论证逻辑,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坚定有力的。一点也看不出,文章出自一位年纪已经达到六十五岁的老人家之手。思维还是那样清晰,火力还是那样猛烈,没有一点衰弱的感觉。这也许得益于柏杨先生对美国的了解,文章是充满自信的,因为,他知道,他用的逻辑,正是美国人攻击中国时,最爱使用的逻辑。
美国人认为,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实行与美国一样的政治制度。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中国要想过这样的日子,就要实行与美国一样的制度。但若中国人多个心眼问,沙特也很富裕,为什么不介绍我们去学沙特的制度呢?美国人一定会循循善诱地说,你中国有沙特那样多的石油吗?它会提醒中国人,沙特的财富主要来自它的石油,但你中国的人均油量有多少呢?所以,如果中国希望能与美国一样的繁荣,还是要学美国的制度。但美国人是不会提它自己的财富来源的。比如,独特有利的地理环境,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横财,大量有才华的外国移民,更不用说黑奴和华工在美国完成它的原始积累时,所付出的作为成本的代价了。美国就是这样利用它的强大建立起它的逻辑联系。美国的繁荣,来自它私有的“民主”政治制度。这判断是否真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是它对外宣传的信念。
当然,柏杨先生不是超级大国,没有那种强行建立一种逻辑联系的蛮横的力量。他只能用艺术的手法来建立这种强盗逻辑。他没有直接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他也不需要这样做,政治制度不过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攻击大陆社会文化,自然也就达到攻击大陆政治制度的目的了。
但中华文化毕竟是灿烂的文明,要直接攻击,一笔抹杀,很不容易。于是,柏杨先生就来一个迂回包抄,深入敌后,旁敲侧击。人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人是好的,社会文化就是好的。人是坏的,社会文化就是坏的。如果能证明中国人是丑陋的人,那么,中国文化也就是丑陋的文化,这样中国的政治制度自然也是丑陋的政治制度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师手笔,一竹竿下来,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全给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去,美国七支航母舰队和它的原子弹,加起来也没有这样强大的威力吧。
但要说人,也是优点和缺点共存。******有******的优点缺点,华盛顿有华盛顿的优点缺点。拿******和华盛顿比较。你不能得出******是恶魔,华盛顿是天使的结论;也不可能得出******是天使,华盛顿是恶魔的结论。拿一个条件相近的普通人与另一个普通人作比较,情况也是一样的,不容易得出明确结论。要不然,姑娘家挑男朋友,为什么左挑右选总是下不了决心呢?因为结论不好下,决定作不了嘛。
柏杨先生毕竟是一个艺术家,知道怎样利用艺术的逻辑去避开这种学术难题。他不采用这种难弄的横向比较的方式来判断中国人的优劣,而是用自己同自己比的方法。或者说,是用恶的梅达尔多子爵和善的梅达尔多子爵作黑白分明的比较,用被分成一半的梅达尔多子爵与正常人作不对等的比较。
柏杨先生先首先装模作样地肯定中国人都是很聪明的,素质优良的人。他说:“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他举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例子。这两位受人尊敬的、生活在美国的科学家,是有足够的说服力证明中国人品质优良。但他们生活在美国,这一点对柏杨先生很重要。这说明他们的优良品质,是在美国文化的熏陶下才焕发出来的。然后,他就一口气下来猛烈数落中国人的各种丑陋表现。什么嗓门大、内斗、懒惰等等,几乎不需要用一口清水来润润他叫累了的喉咙。而这些中国人,都是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