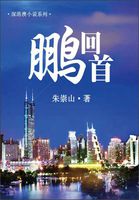李忠、谢文华得到父亲病重的消息,立即决定从达累斯萨拉姆返回成都。
2000年4月1日下午,我和李忠在府南河边喝茶。我们在春风和谐的阳光下,留意着成都市近些年在整治城市河流上的成就,绿化得如同公园一样的河堤,拔地而起的幢幢民居。
我们谈得最多的当然是在东非洲的共同感受。李忠和他的朋友们在东非洲已经干了十来年,同时也是销声匿迹,不为人知的十来年。他们最熟悉东非洲,当然他们也熟悉成都。他们在帮助或者承包建设东非洲的新景观的时候,他们的家乡也在旧貌变新颜。他们挂念家乡,但是他们无暇顾及家乡。只有是家中有了象父母亲生病住院这样的大事情,才能够被迫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浓浓的亲情在隐隐地磨折他们,欲罢不能。
他谈起了杜衡产,一定要带我去杜衡产家。他马上就用移动电话拨通了杜老板的家里电话。
刚刚走进杜衡产家里,李忠就抢上一步紧紧握住老领导的手。
杜衡产关切地问:“你父亲的病怎么样了?”
“有点恼火,很危险。”
“你还要赶回********?”
“没办法,忠孝不能两全!”
李忠的脑海里一定是回想起了童杰父亲去世的情形。
那是1996年,也是草长莺飞的4月。距离李忠父亲病危刚好是4年整。
那天,李忠上午在和四个工地上的项目经理们例行通话。李忠的内心非常矛盾,如何给童杰讲他父亲的事情呢?他踌躇良久,再三斟酌,终于在步话机里喊到:
“小童,小童,下山一趟,家里有事,家里有事!”
童杰的夫人苏艺,当时也在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工地。四年后的2000年5月20日,一个清爽的上午,她在成都马鞍北路华西集团宿舍里,对我谈起那一幕,仍旧是长吁短叹,感慨万千。
当时苏艺听见李忠这样子喊童杰,凭女性的直觉和对童杰父母的了解,她的心脏狂跳起来。
“我当时就觉得没对!”
那段时间,苏艺晚上做梦,老是梦见自己的牙齿掉。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如果做梦梦见掉牙齿,家里就要走(死)老人。且,非常奇怪的是,那段时间童杰也老是梦见掉牙齿。
“童杰,是不是你们爸有问题约?”
“不是很清楚。”
实际上,童杰的父亲刚刚得脑血栓,引起偏瘫,他就不得不奉派参加援外任务,去了肯尼亚。
但是,童杰的父亲是个非常坚强和通情达理的老人,他支持童杰去肯尼亚,他为儿子能够成为我们国家援助非洲大工程的建设骨干,感到十分欣慰,哪有拖后腿的道理?事实上,老人也的的确确是在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刚刚好一点,老人就拄着拐杖,在家属院里走动走动。
童杰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童杰的妹妹害怕影响哥哥的工作,但是又不能不把父亲的病情悄悄告诉嫂嫂苏艺。
苏艺收到童杰妹妹的信,就已经知道公公的情况不是太好。
她看着劳累清瘦的丈夫,实在是只有在内心里隐隐作痛,她知道他作为童家的老大,这个儿子确实是没有尽到孝道。
“你去看看,路上小心开车。”
对讲机效果不是太好,童杰实际上也是七上八下,很不踏实。他简单明快安排好工地上的事情,匆匆忙忙就开车上路了。
到了阿鲁沙,李忠给童杰讲明了成都来电话的全部内容。
“小童,你父亲病情恼火,有点危险。”
“啊?”童杰料到了是父亲的病情。
“你把工作安排好,和苏艺赶紧回去看看。机票我已经订好了。”李忠一贯把事情做的细致到位。
童杰马不停蹄,立即驱车赶回恩戈罗恩戈罗。当晚他安排好工地上的事务,第二天就和苏艺登上了回国的班机。飞机经阿鲁沙、内罗毕和亚的斯亚贝巴,回到北京。
在首都国际机场,童杰和苏艺是又累又饿,疲惫不堪。
“童杰,你去给妈挂个电话嘛,说我们到北京了,下午到成都。”
苏艺当时明显是脑筋里少根弦,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随口说的提议会带来什麽后果。
“要得。”
童杰实际上也想打电话问,归心似箭,披星戴月,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心中的挂念已经是堵到了喉咙管,不吐不快。
童杰拨通了千里之外成都家中的电话。
他的母亲接的电话,老人家对儿子媳妇赶拢北京了,也不能满意了,她哽咽着说:“童杰,你爸爸已经去了!”
“啊!”童杰一下子就感到晕眩。
当时,童杰就在机场大厅里放声恸哭。
苏艺明白他们千赶万赶,还是没有赶上和父亲见最后一面。她看见丈夫悲伤万分地哭号,也忍不住放声大哭。两口子抱头相拥,在来来往往的中外旅客面前无所顾忌地发泄悲伤。可以说,这是出国援外人员里少有的回国场景。
1996年4月29日傍晚,童杰和苏艺回到了成都市区,在马鞍东路的家中,父亲已经是大家属院里那个哀伤的灵堂中的一张黑白像片了。童杰的母亲看见儿子媳妇万里迢迢的回到身边,更加悲伤,她抱住儿子放声大哭:“你们回来了!你们爸爸面都没有见上!”
一时间,童家的大大小小、男女老少,触景伤情,立刻哭成一片。这样的场面,让所有在场帮忙的同事、朋友们,感到了揪心的心酸和万分伤感。
童杰的父亲去世时,年龄不算太高,刚刚68岁。
2000年5月,我和苏艺摆起这段往事时,她给我补充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细节。
“我们现在都回来了。有时候,想起来,还是觉得他老人家走得太早了!前一段时间,我和童杰去看我的好朋友。她的父亲也是偏瘫,很少出门。今年五一节那天,老人家说想出去看看。童杰二话没有说,马上就开车陪老人出去转了半天,耍了一趟。老人高兴得不得了。”
童杰看见乐呵呵的老人,情不自禁地感叹:“哎呀,要是我们爸在就好了!”
2000年5月29日,李忠和谢文华离开成都,经深圳转道香港,乘坐阿联酋航空公司飞机,返回达累斯萨拉姆。
这天早上5点,庞大笨重老旧的摩托罗拉中文传呼机定的5点零八分的闹钟还没有响,我就醒了。睁开眼睛,头脑非常清晰:我今天要去送李忠谢文华到双流机场。
天边微微泛着曦微的晨光。
窗外是宁静的成都西郊的田野和农舍。
楼下院子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车。为了怕被堵在院子里出不了门,我把特意借来的切偌基越野车停在更宽敞的路边。
平时很少在凌晨开车穿过成都。我从大街小巷一路风驰电掣,把大白天诚惶诚恐的红绿灯视若无睹,心中很是愉快。时时刻刻在各种各样的规则管理下,偶然能够违犯一下,不用说,有一种形容不了的快感。
十多分钟,我就跑完了平时白天要将近五十分钟才能够完成的路程,可以想象,成都市这座号称西部如何如何的都市,交通已经拥塞到了何种程度。司机们都在抱怨:成都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堵城了!我不明白,有关的官员去过巴黎,看过纽约,逛过东京,他们研究明白没有:人家那么多的车,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在高速流转,少有堵车?
五点四十分,我在马鞍北路给李忠拨电话。
“你来了?”李沛接的电话,语气里有点吃惊。
按照计划,我应该是在六点二十分到。我有一种潜意识,如此沉重的告别,可能还是多一点时间,好些。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在医院。
李忠把箱子一个一个的搬出来。
实际上,就在李忠谢文华决定回********,把飞机票都预定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天人感应,昨天也就是2000年5月28日晚上,李忠父亲出现紧急情况。当时李忠一家人已经疲惫不堪的回到马鞍北路宿舍。电话一次又一次地从肿瘤医院打来,让人心惊肉跳的。李忠马上又开车返回医院。原来是被一口痰堵住了。情况紧急,李忠当时就想退飞机票了。全体家属,医护人员,看护人员,进进出出,手忙脚乱,半夜三更,老人家总算是缓过气来。
李忠和谢文华,还有李沛,三个人提着大包小裹出来。
我注意到,有一个很大的电饭锅,可以煮十来个人的米饭。很奇怪!
谢文华说:“********基本上日用小商品都是中国货。达累斯萨拉姆买不到大一点的电饭锅。”
还有一个纸箱,很沉重。李忠告诉我:“这里面都是书,哈佛经营管理教程之类,现在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从院子里开出来,我把切偌基开到路边让它。
“刚才那辆出租车,是我原来一个同事开的,”李忠说,“原来都是公司的领导,没有法,只好出来开出租车,还算中等以上的活法,每个月多多少少还有点收入,养家活口嘛。”
我明白。今年春节,我回到贵州省的老家,去看我的一个老同学。我们原来一起工作的那家军工厂不明不白的破产了,他靠一辆二手长安车,来来回回地在遵义县城和火车站拉客人,每次都要超载几个人,才能够勉强挣点稀饭钱。
切偌基轻快地穿过刚刚苏醒、立即就车水马龙的芙蓉城,我们沿着红星路向南疾行。
李忠在车上交待李沛,一定要去看望一位患病的老朋友:“据说也是得了癌症,晚期喽,可能拖不了多久,去看看,代表我和你妈妈。”
“嗯。”
四川省肿瘤医院,也叫四川省第二人民医院,就座落在人民南路二环路立交桥和新修的机场高速公路起点立交桥之间。这座听起来不那么轻松的医院,我是从来没有进去过,如果不是因为李忠父亲生病住在里面。
我把切偌基开到医院大门前,李忠和谢文华,李沛都下了车。
李忠让我在门口等。
我明白,李忠不愿意有其他人看见或者说参与他们与老人家的别离场面。
我已经去病房里看望过老人家。
我买了些康乃馨,恭恭敬敬地走进四楼43号病房。
老人家是清醒的,他温和地卷曲在病榻上,双手合十,轻轻地向我道谢,并伸出了他的大手,我赶紧握住他温暖的手,看着这位从抗日战争就投身革命的坚强老人,我只是在内心祈祷,但愿病魔能够快快离他而去。我只是在内心里想,没有说出来。我是一个拙于在口头表达内心的人。但是,我很不愿意看见病人,尤其是熟悉的人,或者是同学,或者是亲朋好友。人一生病,就显得无助。我的心肠软。
早班飞机从南边的天空划过,轰鸣声让我回到眼前的现实。
一会儿,李忠谢文华和李沛神情滞重地缓缓步出大门。
我细细地注意到了他们的眼圈是红的。
上车以后,没有一个人说话。
我明白,这是一次生命难以承受的告别。
我赶紧发动切偌基,轰鸣着向双流国际机场开去
李沛后来告诉我当时在病房里的场面。
李忠匆匆忙忙疾步走进病房,人还未拢父亲病榻前,他,一个在东非洲呼风唤雨、叱诧风云的人物,放声大哭,向父亲告别辞行。
他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咚”地一声给父亲磕头!
谢文华捂着嘴,不忍心看这一幕,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李沛也远远地看着父亲和爷爷,看着奶奶,看着母亲,内心非常难受,甚至是感受到残酷的煎熬。
她觉得每一秒都象有平时一个小时那么漫长。
“当时,我大气都不敢出一口!我只是觉得告别对爷爷,对父母,都是太残忍了。我们家运气,今年最坏!”
今天到双流国际机场送行的,还有谢文华的八妹。
李忠和谢文华把行李交办托运。离停止办理手续只有十五分钟了。
谢文华告诉我:“你来********,帮我们多带点郫县豆瓣,花椒,海椒。”
“好,没有问题,我一定多带点。”
李忠和谢文华走进安检口,回头给我和李沛招手:“再见,坦桑见!”
“坦桑见!”
晚上九点过,李沛给我发传呼,她已经从医院回到马鞍北路的家中。
她在电话里幽怨地讲,今天一整天,医院爷爷病房里笼罩着戚戚怅怅的情绪。很压抑。
李忠的母亲几乎是哭了一天。李忠的父亲处于昏昏糊糊的状态,也不知道是真的迷迷糊糊,还是不想多说一句!
李沛下班后去了医院。看着心爱的爷爷在病床上的样子,她想着早晨在病房里父亲和爷爷告别的一幕,心中很不是滋味。
这时,电话响了。奶黄色的若齐亚手机演奏的是《康定情歌》,尖利,电子合成,不伦不类。
李忠从香港来了电话问候父亲。他和母亲说了好些话。尽管李忠和谢文华的飞机要在晚上十点过才从大屿山国际机场起飞,但是,李忠已经在考虑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处理好项目上的事情,再尽快争取返回成都,回到父亲的病床前尽孝。
他一定是充满了后悔。
李沛说:“哎!这也可以叫作忠孝不能两全吧?”
小小年纪,李沛的话已经透出一丝沧桑味道。
谁说李忠的心境,仅仅是他内心的独享?
1999年11月,李忠的父母亲远涉重洋,到了东非洲********。可以这么说,在东非洲,从经援到承包,还没有哪个的父母亲出过国!
李忠和谢文华陪同父母亲去了阿鲁沙,去了赛伦盖蒂大草原,去看了赛琳娜项目。现在进去的道路,虽然还是泥土路,已经比较平整,相当好走。李忠开车,越野车跑得又快又平稳。李忠的心情可以说是很复杂:自己那么多年在外面,没有尽义务照顾好父母亲,吃了再多的苦和累,现在两位老人能够亲自来看看,也是一种安慰和沟通。
他们一行人在马尼亚拉湖旅馆看了看,就只有走。因为,很简单,没有床位了!在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旅馆,两位老人住了一晚。在赛伦盖蒂动物园旅馆,老人和李忠谢文华,又住了一晚。赛伦盖蒂草原帐篷旅馆。,路途遥遥,就没有去。他们一路上都处于兴奋之中。
“这辈子,还能够出来看动物,看风景,看非洲,值得!”
两位老人的运气可以说是非常好。李忠和谢文华在赛琳娜项目施工期间,进进出出野生动物园保护区很多次,也没有他们这样,一次
把主要的希奇动物看完。长颈鹿,角马,狮子,豹子,牛羚,大象,狒狒,河马,还有平时不露峥嵘的犀牛,统统尽收眼底。
老人很满意。
回到成都,他们给家里其他人摆,兴奋,很满足。
“嗨,李忠也算个孝子罗!”
2000年6月11日,星期日下午,滴滴答答,小雨下个不停。我已经在家里的电脑上写了连续两天,没有下楼。我接到李忠家人从四川省肿瘤医院发来的传呼。
电话里,他们告诉我一个不祥的消息,尽管是早有预计的消息:李忠父亲病情急转直下,开始出现败血症,可能,医生说,可能过不了今天晚上了。
我忙惊问:“李忠知道不知道?”
“知道。中午还从达累斯萨拉姆打来电话。家人已经告诉李忠实情。”
“李忠还要赶回来?”
“可能不行。他们工地上有麻烦,工地上刚刚死了一个当地黑人。走不了。”
这期间,6月13日,李忠还为我发来了一个封电子邮件,标题是“嗨!”
“回到达累斯萨拉姆,忙得晕头转向。今天平静一点,我就你的来访,初步拟定了一个日程,看看如何。……”
……
2000年6月15日早上8点22分,我开车去电视台上班的路途中,被一大片乱钻乱挤的车辆堵在羊市街西延线上,大约是三友百货商店和中级人民法院之间,传呼机响了。
李沛发的:“我爷爷今天去世了……”
上午,我和老朋友、泸定县旅游局前任局长邓明前一起,到四川省肿瘤医院,表示我们的哀思,也表示我们对李忠父亲的敬意。李沛也认识邓明前,她对邓明前的到来,稍稍有些惊讶。
病房外,李沛的奶奶已经悲伤地哭喊着老伴,显然,早已经预计的生命消失,一旦来临,还是难以承受和相信!
我的思绪当然也在关注:李忠是不是已经得知这个恶耗?
李沛在病房电梯边的磁卡公用电话上,用IP电话拨向遥远的********。当时是达累斯萨拉姆时间凌晨三点多,办公室怎么可能有人呢?连续拨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李忠和谢文华是否已经梦见?
李忠父亲的遗体,被医院和殡仪馆的人抬走了。在成都市的儿女和亲友们,搀扶着悲痛欲绝的老人,上车回到东郊的石油总机厂。
下午,李沛在电话里告诉我,她与父亲李忠通了电话。
在万里之外的东非洲,李忠闻讯,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6月16日,李忠的母亲召集在成都市的亲友们开会,决定不让李忠回来。
李忠刚好就打了电话回来。听了母亲的决定,李忠不表态,也不知道是否有合适的航班,能不能及时赶回来。李忠在电话里交待李沛:“你替爸爸妈妈,多给爷爷磕几个头!”
我在办公室里,用IP卡给********挂电话,李忠的手机不通,办公室也没有找到他,谢文华也不在。我想表示我的慰问和哀悼心情。电话不通,没有办法,晚上给他们发个电子邮件去。
主题: 节哀
李忠、谢文华:你们好!
你们的父亲去世,使你们不能尽孝于此刻。非常理解你们的哀痛。
我已经在今天上午去总机厂凭吊了老人家。
希望你们节哀、保重。
刘洪耀
2000年6月16日星期五22时32分于成都
2000年6月15日,从中国成都市返回********达累斯萨拉姆刚刚半个月的李忠,又一次面临老问题:是走,还是不走?
我心中有预感,凭着李忠的性格和脾气,他极有可能抓紧时间赶回来。只要时间允许,只要航班合适,他哪怕只回来几天,也会天远地远的赶回来送别父亲。
6月17日上午,乌云笼罩着成都。我大清早就驱车到了成都市西郊的茶店子。在一条小巷里,我拜会了曾经在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旅馆工地工作过的赵云舜老师。在童杰那里,他一个人既是翻译,也是保卫和出纳。退休以前,他是电子工业部第十研究所的翻译,和我读大学以前所在的贵州083基地,是一个系统。我当时在的那家军工厂,红红火火,主要的军品设计,都是十所设计的。说来有缘。他居住的地方和我蜗居的西门,相距不远。再次证明,在我的命运中,有很多定数,难以改变。
在赵云舜家中,从李沛那里得知,李忠已经决定在今天上午从达累斯萨拉姆启程,将于明天晚上八点半左右到达成都市双流机场,并且已经确定在6月20日左右启程返回********!距离我送他和谢文华到双流机场,刚好半个月时间!
2000年6月18日晚上,这些天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海外游子,来来回回奔波了好几趟的李忠终于来到了父亲的灵堂前。他在父亲居住的四川省石油总机厂宿舍楼下的灵堂下跪,朝父亲的遗像行大礼。
李忠的伙伴们,在赛伦盖蒂动物园旅馆工程上,一起奋斗的战友朱凤鳞、童杰、尹书涛和苏德模来到了李忠身边。他们安慰李忠,他们非常理解李忠此时此刻的悲伤。
2000年6月19日,革命老人李发清的告别仪式,在成都市北郊的殡仪馆隆重举行。
这天,大清早,我从成都市西郊驱车匆匆忙忙赶到时,送葬的车队即将发车。我在送别李忠不到一个月,再次和他见面,我趋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保重,节哀!”
“谢谢!”他的嗓音是嘶哑的。
大大小小的车辆,一共有十八辆。最前面是一辆崭新的上海桑塔纳轿车。后面依次是亲朋好友的车辆,还有李发清老人所在单位的大客车,上面坐满了向李发清老人道别的领导和职工代表。李忠端着老人家的遗像,表情沉重,上了第一辆车,李忠的兄弟、妹妹和李沛一起,也上了前面的车辆。早晨7点30分,车队缓缓驶出李发清老人工作了几十年的工厂,离开八里庄,过青龙场立交桥,沿着川陕公路开向成都市北郊殡仪馆。沿途,车队抛洒着土黄色的钱纸,一路顺畅。
在北郊殡仪馆第十告别室,革命老人李发清安卧在鲜花和花圈丛中。一百余人的告别队伍,在第十告别室外庄严肃穆地向老人三鞠躬,致以最后的敬意。李忠率家人缓缓进入告别室,端详着老人的遗容,眼泪止不住涌出来。家人中的女性悲伤地哭喊,气氛立即就哀伤起来。
我在李发清老人住进四川省医院和四川省肿瘤医院期间,见过老人家。每次都是匆匆忙忙,基本上没有交谈。只是在四川省肿瘤医院病房里,老人家双手合十,并与我握手,轻轻地谢谢,至今记忆犹新。
最后的时刻,在火化炉前来到。我已经不忍看见和听见老人家的亲人撕心裂肺、声斯力竭的哭喊。那是亲人们向他真真正正最后的道别。一个来到世界上71年的生命,就这样化为灰烬,也许是人生最大的痛,也许就是生命的最后归宿。
2000年6月22日下午,我陪李忠来到成都市工程机械厂。这几天,李忠依然是忙得脚不沾地。上午,他刚刚和全体亲友在新都县为父亲选定了最后的归宿地:宝光塔陵。下午,他在刘守明那里和陈家禄等人,商讨了尽快去乌干达展开项目的事情。快五点,我和李忠在成都市某机械厂碰面。我刚刚结束了在川大的研究生期末考试。李忠为这个工厂到********参加一个展销会忙碌。大型机械设备已经通过远洋货轮运到了达累斯萨拉姆,还有很多说明书、礼品,需要带过去。李忠见状又赶紧安排陈家禄他们26日走的时候,帮忙带点。
我和李忠驱车去他的妻妹家道别。很巧,谢文华妹妹的先生,是西南航空公司的757驾驶员,和我是贵阳老乡,只是他在贵阳风景秀丽的花溪长大,我在贵阳南明河边的甲秀楼畔渡过童年。在机场路边的妻妹家中,我和李忠才正式谈到了我第二次游历东非洲的日程和内容。随后,我们又去了四川省石油总机厂宿舍。李忠的母亲和众亲友都在,他们仔仔细细地谈论了宝光塔陵的事项,基本上确认了这个安排,比较满意。同时,李忠还关切母亲一个人的生活安排。亲友们已经计划了在成都市最闷热的夏季,让老人家去青城山避暑。
李忠母亲看着孝顺的儿女们,表示了满意:“李忠,你回去要安心工作,注意身体!”
刚刚五十的李忠,已经有点糖尿病初期症状,医生告诫,不能喝啤酒,不能吃肥肉,不能……亲友们赶紧推荐防治糖尿病的药。现在国家改革医疗制度,病人的恐惧是费用,健康人的恐惧是怕生病、住院。药是太贵了,普普通通的看个感冒都要一百多。有一天,我儿子的膝盖破点皮,那个医院的医生不问青红皂白,化验,查血,打针,抹药,折腾那里几个小时,将近一百元,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最后,几块钱弄点普通药水,就搞定。
2000年6 月22日晚十点,我和李忠在马鞍北路宿舍路边道别。
次日早晨,他飞向香港,转机阿联酋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越印度洋,飞回达累斯萨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