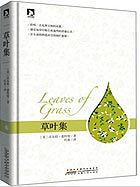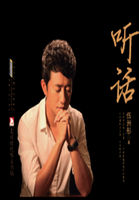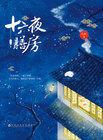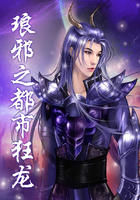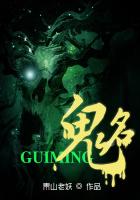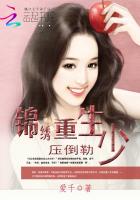很明显,指点干预很可能破坏叙述的“逼真性”的,夸张的指点目的之一就是不让读者保持“现实幻象”。因此,到了16世纪后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指点性干预就日见其少(也有例外,如公认为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的名著《名利场》,但萨克雷的其他小说并没有这么多的指点)。20世纪的小说中,指点几乎完全隐藏了起来,只有个别时候,指点干预的突然出现给叙述一种突兀的起点或转折。例如E·M·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兹海角》这样开头:
我们不妨用海伦写给她姐姐的信开场。
寄自霍华兹海角
星期二
亲爱的梅格……
这里为什么有一个指点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在一部现代小说中用这么个指点开场是很刺眼的事呢?这是因为这个直接抄录开场方法很特殊,完全省略了任何背景介绍,或气氛的营造,使这条指点干预成为一件自然而并不做作的事。
《红楼梦》中的指点干预看来比任何中国古典小说来得少,但第六章这一个指点显然有必要:
且说荣府中合算起来,从上到下,也有三百余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没个头绪可作纲领。正思从哪一件事、哪一个人写起方妙?却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这一家说起,倒还是个头绪。
这段指点很长,因为叙述者作了一个很出格的安排,从不相干的小人物刘姥姥来访开始整个叙述,这样的安排需要一定的辩护。那个时代,并不赞许小说的叙述方式创新,《红楼梦》也不是实验主义的小说。放进一些指点干预能缓解叙述方式非程式造成的不安。
总结一句:指点性干预就像戏剧中的舞台说明。指点只与叙述方法有关,就像舞台说明只与演出方式有关。因此,如果叙述者想在书中插入他对小说技巧的看法,他就可以利用指点干预的机会。《孽海花》第二十一回:
话说上回回末,正叙雯青闯出外房,忽然狂叫一声,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想读书的读到这里,必道是篇终特起奇峰,要惹起读者急观下文的观念,这原是文人的狡狯,小说家常例,无足为怪。但在下这部《孽海花》,却不同别的小说,空中楼阁,可以随意起灭,逞笔翻腾,一句假不来,一语谎不得,只能将文机御事实,不能把事实起文情,所以当雯青的忽然栽倒,其中自有一段天理人情,不得不栽倒的缘故,玄妙机关,做书的此时也不便道破,只好就事直叙下去,看是如何。闲言少表:且说雯青一跤倒栽下去……
《孽海花》的分章节法与传统章回小说比,没有任何不同之处,雯青这一跤的确是“小说家常例”,“文人(程式化)的狡狯”。然而曾朴又是中国最早的西方文学研究者之一,他想努力求新,脱尽陈套。他想这么做,却没有找到一套方法。《孽海花》作为中国最后一部传统小说,充分表现了内容与形式的不相容,新与旧的不调和。这段指点性干预,本想说出此书在叙述上求新的意图,但其场合,其方式,甚至其措词,却完全是旧小说的程式。这段指点想说明的是新形式,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新形式的阙如。
和西方现代小说相似,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指点式干预也越来越少,只有像《阿Q正传》这样充满讽刺语调的作品,用过分的干预来调弄叙述。但是,追求传统小说风格或民间文学风格的作品,依然有大量的指点干预——实际上指点干预成了这一类小说的风格标记。古华的小说《芙蓉镇》有一例:
芙蓉姐子米豆腐摊子前的几个主顾常客就暂且介绍到这里。这些年来,人们的生活也像一个市场,在下面的整个故事里,这几个主顾无所谓主角配角,生旦净丑,花头黑头,都会相继出场,轮番和读者见面的。
这段指点干预与传统小说的指点干预已经很不相同,整部小说中的指点干预段落也不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程式化指点,作者本意怕也是求新。但是,此类指点干预之存在本身,就指向了传统叙述风格,恐怕是每个读者都能感觉到的吧。
最后我们谈一下一种非常特殊的指点干预手法——伴随文本手段干预。有时这种干预非常奇特,有时让人不知如何分析才好。晚清王濬卿的小说《冷眼观》第五回有这样一段,实际上是给叙事文本加注释:
黄胖子见姓吴的眯着一双近视眼,尽管凑在他老婆身上慢慢赏识,不觉发急问道:“先生,唔贱内的相貌,可能配得上拿这五千银子?”(此句是南京人方言)
在上一章中,我们说到过,叙述者把底本人物言语变成叙述中的引语时,不得不舍弃语音语调特征,可以保留某些风格性文字记号,例如这一段中的“唔”。但是,如此关于方言语音的形式指点,显然是超出文本之外的关注。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此小说的现代编者阿英不得不用一个很尴尬的括号。
有的超文字指点干预设计巧妙,意味深长。法国当代作家赛贵尔的小说《投降》中有一段:叙述中的一个人物在读一本小说,有个旁观者看到他正读到第144页,而这时,《投降》这本小书也正进行到144页。这是一种用类文本的印式手段(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来象征叙述现实与客观现实之对应。
小说不同于科学性的叙述(包括历史叙述等),它完全不必加脚注,编辑加的技术性脚注,也是类文本,不属于叙述文本的一部分。但有时,脚注被利用来作为一种叙述干预手段。法国18世纪著名小说《危险的关系》是一本书信体小说,但却有许多脚注,大都是说某封信可以与某封信印证,某个事件在某个地方有记录等。这些脚注实际上是叙述文本的一部分,但它仍具有超文本的假象,假象被利用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干预手段,以增加文本的逼真感。
法国当代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的小说《瓦特》有个调动文本指点的例子。小说中有一句:“凯特二十一岁了,很漂亮的姑娘,只是有血友病。”该页有个脚注:“血友病如前列腺肿大一样,是个男性的疾病,但在这本小说中无此限制。”恰特曼引了这个例子并认为这条自我坦白自称本作品为虚构,是谎言,反而使叙述具有独立的价值,不依赖于叙述外的其他价值体系。
(第三节) 评论干预
叙述中的评论,布斯称为“作者干预”(authorial intrusion)。既然叙述是由叙述者所控制的,叙述文本中的每个字都是叙述者说出来的。作者无法直接进入叙述,作者即使要发表评论,也必须以叙述者评论的方式出现。因此,布斯这个术语是不合适的,笔者建议改为“叙述者干预”(建议英译narratorial intrusion)。这种评论干预可以很长。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九卷第一部《燃烧的荆棘》用了整整十多页篇幅评论“革命理想”问题。这些评论完全不受叙述时间空间的限制,甚至可以预示未来:
一七八九年的酒,如今在家庭酒库中只剩几瓶泄了气的,可是我们的曾孙玄孙还会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喝得酩酊大醉的。
作如此长的评论时,叙述流暂时中断了。但大部分的评论却是在叙述并不中断的情况下进行的。常常,这种评论短到只有一句,半句,甚至一个词,尤其常是形容词、副词或插语。这样的评论在几乎任何叙述中都随处可见,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上册中的一段:
李自成镇定而威严地向全场慢慢看了一遍。奇怪,仅仅这么一看,嚷叫和谩骂的声音落下去了……
巴尔扎克的《夏倍上校》:
夏倍因为不得不在卧房里接待客人,脸上很难堪。的确,但尔维在屋内只看到一张椅子。
伍尔夫的《到灯塔去》:
明达·道伊本能感受很细腻,她直率地,荒唐地(absurdly)说她不相信有人会喜欢读莎士比亚。
这最后一个评论是反讽式的,隐含作者明显地同情明达之直率。
有时候,评论性干预被仔细掩盖起来,几乎没有形迹。《到灯塔去》第二章第二节是这样开头的:
因此,当所有的灯都熄了,当月亮沉下去,当细雨敲打着屋顶,无边的黑暗开始涌来。没有任何东西看来能逃脱这黑暗的潮水……
这里的“看来”(it seemed)是个插语,由于它是过去的,所以似乎不是叙述者插入的口吻,因为叙述时间总是现在时。但它还是一个伪装的叙述评论,它隐指着一种主观的评价(在谁看来),一种对情景的猜测估量,从而给叙述一种不确定的语气。
有时,评论式干预可出现在类文本手段之中。例如副标题:《红楼梦》的回目“薄命女偏逢薄命郎”,“痴女儿遗帕惹相思”等等。有时评论会直书在标题里,如《忠义水浒传》《三侠五义》。
为什么叙述者要离开他讲述故事的“本职工作”而对叙述中的人和事进行评论?布斯认为“评论者最明显的任务是告诉读者他们自己不太容易搞清楚的事实”。这种看法只是在很有限的场合才是正确的,即只在所谓“解释性评论”中才是如此。《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有一段:
又过了一年,王美年方十五。原来门户中梳弄,也有个规矩:十三岁太早,谓之“试花”。皆因鸨儿爱财,不顾痛苦,那子弟也只博个虚名,不得十分畅快取乐。十四岁谓之“开花”。此时天癸已至,男施女受,也算当时了。到十五岁谓之“摘花”。在平常人家还算年小,唯有门户人家,以为过时。王美此时未曾梳弄,西湖上子弟,都说他似木瓜空好看。
这的确如布斯所说,是读者自己不大容易搞清楚的事实。当然,可以用另外方式介绍这“梳弄”的规矩,例如通过人物的口,在谈话中说出来,但像中国古典短篇小说这样紧凑的叙述风格,过多的转述使行文变得松懈。反正“拟话本”的小说叙述者可以假定自己处于说书人那样有利的地位,可以自由发表评论,因此不妨直接用个“原来”交代背景知识。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卷“少年”的第二部讲述了主人公与女裁缝萨皮纳之间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在这一部的结尾处叙述者忍不住抢过了克利斯朵夫的话头,自己抒起情来:
克利斯朵夫也知道,在他心灵深处有一个不受攻击的隐秘的地方,牢牢的保存着萨皮纳的影子。那是生命的狂流冲不掉的。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座埋藏爱人的坟墓。他们在其中成年累月的睡着,什么也不来惊醒他们。可是早晚有一天,——我们知道的,——墓穴会重新打开。死者会从坟墓里出来,用她褪色的嘴唇向爱人微笑;她们原来潜伏在爱人胸中,像儿童睡在母腹里一样。
这段评论是代克利斯朵夫不继续这段恋情说出理由,实际上是“我们知道的”,是“常识辩护”。
“补充性”评论所提供的不一定是背景知识,也可能提前说出未来发生的事。恰特曼举过特罗洛普《巴彻斯特修道院》中的一个例子:“软心肠的读者别担惊受怕,爱莉诺并不是命中注定将来一定会嫁给斯洛普先生或伯梯·斯坦霍普。”恰特曼认为这个例子是对述本发表评论,也就是说是个叙述形式的指点。笔者觉得这恰恰证明区分形式与内容,甚至区分底本与述本,都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个评论,既指出形式(预述)又评论了内容。
布斯说评论的目的是提供读者不容易了解的事实背景,但我们发现大部分叙述评论并不提供事实,而是与受述者作道德判断上的呼应,是一种主体性整合的方式。
在人物做了一个按常理来说是出格的行为时,往往用这种评论——我们可以称为“解释性评论”——来说明这种行动的合理性。还是《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例子:“你道天地间有这等痴人,一个做小经纪的,本钱只有三两,却要把十两银子去嫖那名妓。可不是个春梦。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懵教官”有评语说:“老人家的眼泪极易落的。”
不用再引了,随便一翻就可拣个满箩满筐。传统小说此类解释性评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讲的道理,并不是读者不容易理解的高深哲理,也不是曲里拐弯的强词夺理。恰恰相反,大多数情况下解释性评论是老生常谈。一般解释性评论正是试图用社会上大家都同意的规范来解释情节中的离奇行为(不奇就不成其为小说)。《金瓶梅》写到西门庆与朋友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私通,花子虚想请西门庆吃酒,趁机向他逼还几百两银子的借款。但李瓶儿“暗地使妈妈过来对西门庆说休要来吃酒,只开送一篇花账与他,说银子上下打点都使没了”。此时,来了一段评论,谈“御妻之方”:
看官听说,大凡妇人更变,不与男子一心,随你咬折铁钉般刚毅之夫,也难测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内,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妇人坏了者,为何?皆系御之不得其道。要之在乎容德相感,缘分相投,夫唱妇随,庶可保其无咎。
解释性评论绝大部分是如此老生常谈,并非作者低能,请注意,这些评论从叙述学角度说,是叙述者作的(例如上引段是“说书的”对“看官”说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叙述者的文化规定性:传统白话小说的文化功能不允许叙述者超越规范。吴趼人的小说《九命奇冤》第三十二回也有一段有趣的解释性评论:
看官!这几行事业,是中国人最迷信的,中国人之中,又要算广东人迷信得最厉害,所以苏沛之专门卖弄这本事,去戏弄别人。我想苏沛之这么一个精明人,未必果然也迷信这个,不过拿这个去结交别人罢了。
这段叙述者评论,以补充性评论开始,然后转入解释性评论。叙述者直接点明这段话是他的解释,而解释的基础也是常理——精明人借卜相与人交往,自己决不会相信。有趣的是这个苏沛之是陈臬台的化名,他微服私访,装做会卜卦相面,以打入罪犯集团内部去掌握证据。这个秘密,要等四章之后才会揭开,是小说这一段的关键悬疑。然而在此,为了作这个解释评论,叙述者心甘情愿地过早捅开秘密。由此可见这种我们看来似乎不太必要的评论对晚清科学世界观刚引入时的叙述者如何重要。
但是数量最多的,要算评价式评论,即叙述者跑出来对人对事直接作判断。茅盾的《子夜》第二节中写到公债要跌的消息传到吴公馆的客厅:
这比前线的战报更能震动人心!嘴唇上有一撮“牙刷须”的李壮飞固然变了颜色,那边周仲伟和雷参谋也赶快跑来探询,这年头儿,凡是手里有几文的,谁不钻在公债里翻斛斗?
小小一段,有两个评论,后一个是我们已讨论过的提供事实性的补充性评论,前一个不是人物说的话,是叙述者对消息惊人程度作的评价性评论。
我们前面说过的可以短到半句一字的评论,几乎全是评价性评论。但是借形容词作评价是太容易把叙述者态度强加给叙述。《李自成》小说中这种例子就太多:
刘仁达被李自成这种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和毫无通融余地的回答弄得无话可说……
“毫无通融余地”是来劝降的刘仁达这个人物作的评价,“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却是叙述者的评价性“表态”。评论把一种价值观直接加在叙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