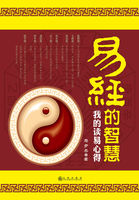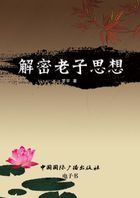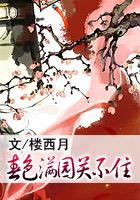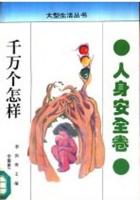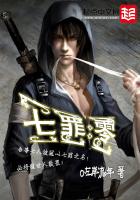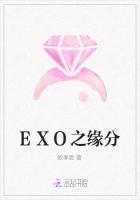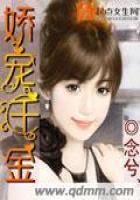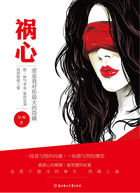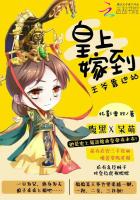学衡派的史学思想与他们对历史的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学衡派成员都不约而同地把史学作为以人类活动为客观研究对象的科学。何为科学,缪凤林认为:“于宇宙森罗万象之中认定其一部分之现象,从事完密而有系统之叙述,随所研究而立名,是日科学。”以“人事之递嬗”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也包括在科学的范围之中。张其昀的认识与此相似:“历史者,人道之纪录,古人之言行思想,藉历史以遗传后人,后人积累古人之经验以善其生,展转递增,展增递蜕,人类社会遂渐见进化之迹。”陆懋德也认为史学是以人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他援引英国学者的说法,认为“历史是民族团体发展之研究(A study of the growth of the nation and communities)”。他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并非同于一种记载,且远过于一种记载,而实为一种研究。历史既不是记载,而是一种研究,且是一种民族发展之研究,即是一种科学。历史既是一种科学,即必须有原理,有方法,有组织,而不得以单纯记载充之。”正如陆懋德所说,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不能满足于记载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而是要通过研究揭示其隐藏在表象背后之原理。缪凤林说得更清楚,历史研究就是要以阐明保生、乐生这一人类活动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史为人类之活动,人类各方面之活动,皆起于适应保生乐生之需要,研究历史,亦不外乎研究人类保生乐生之活动,见于宗教、美术、政治、经济、学术、伦理等方面者,了解其意义而已。”
可以看出,学衡派对史学研究的范围、宗旨的认识已较传统史学有很大的不同。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是宽泛与含混的。传统史学的研究偏重于陈列帝王将相的事迹,以政治史为主,正如梁启超所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而学衡派则提出以全部人类的活动作为历史研究,其视野显然要宽广得多。就史学的撰述宗旨而言,传统史学也比较偏狭。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读者皆求诸禄仕之家与好古绩学之士。夫著作家必针对读者以求获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缘读者不同而书之精神及其内容组织亦随而不同,理固然也。读者在禄仕之家,则其书宜为****帝王养成忠顺之臣民;读者在绩学之士,则其书不妨浩瀚杂博奥衍,以待彼之徐整理而自索解。而在此两种读者中,其对于人生日用饮食之常识的史迹,殊非其所渴需。而一般民众自发自进的事业,或反为其所厌忌。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在学衡派而言,研究历史的宗旨已有明显的不同。他们一致认为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探求历史嬗变的因果关系,揭示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规律。柳诒徵说:“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之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缪凤林更为注重发掘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这是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研究历史,其目的何在耶?日无他焉,史为人类之活动,研究历史.明白人类活动而已。人类之活动,递遗递袭,赓续蜕变,情态行为,互为子母。核实言之,不外一因果关系。研究历史,了解因果关系而已。因云果云,皆相对名辞。同一史实,以其承前事而来,对前称果,果为前事之果,以其能引生后事,对后称因,因为后事之因。”缪凤林还表现出为学术而学术的旨趣,他说:“讲学以明真也,非所以言用。研究历史而明白因果,至矣尽矣,高矣美矣,尚何用之足言。”可见,无论从史学研究的范围还是宗旨看,学衡派所从事的史学研究,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他们以整个人类活动为客观研究对象,试图从历史事实本身发掘历史嬗变的规律。这与传统史学强烈的政治意味相较,显然具有更为浓厚的学术气息。
学衡派并非不注重史学的现实功用。他们认为,只要坚持历史研究的学术性,其现实功用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虽不言用,而其用之随而自至者,亦可得而言焉”。缪凤林列举史学研究的八项现实功用,略可代表学衡派的观点:“现在史实,承前而来,不明过去,无以了解今兹,温故而知今,一也;未来现象,虽难预料,然因已宿具,亦可略测其可能之趋向,彰往而察来,二也;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蓄德而日新,三也;观恶因恶果之递嬗,察其何以至此,而知所去避,崇善而去恶,四也;穷通得丧,无事偶然,明其因果,爽然自失,失败成功,两皆无着,生活之超脱,五也;由果溯因,凭因索果,彻上彻下,通古通今,时不限于目前,地不囿于一隅,胸怀之扩大,六也;睹昔贤之事功,知立国之非易,处今兹之飘零,觉匹夫其有责,爱国之心发,七也;念先民之辛勤,感惠我之实深,将继志而述事,敢暇逸以娱乐,精进之心生,八也。”不难看出,学衡派对于史学鉴往知今,培植道德心、爱国心、奋进心之功能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和执著的追求。
学衡派对于历史研究科学化的努力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于史学研究范围、宗旨和功用的主张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吸取传统史学的精华,对于史学研究极为重要的材料、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精深的见解,并在实际研究中加以运用,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学衡派对史学研究中史料的认识是非常精到的。他们认为史料应该在历史研究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凡历史价值之优劣,不在文笔体例之高下,而全在采用史料之精确与否”。张荫麟说:“理想之研究须具二条件:(一)正确充备之资料;(二)忠实之艺术的表现。”史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作为史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是不可重复的,史学研究所依赖的只是即往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痕迹,也就是史料。张荫麟对历史研究的这一特殊性质解说得甚为明白:“一切具体的科学,按其研究对象之性质,可分为二类,其一为直接的科学,其所研究的对象,可直接实验或观察,而同样现象,可随意使之复现,或依自然之周期而复现,至百千万亿次而无所限,故其叙述推理及结论之所据,非某时代某人特定的观察,而为人人所能亲见之事实。此类科学,如物理化学其最著者也。其二为间接的科学,其所研究之现象,一现旋灭,永不复返,吾人仅能从其所留之痕迹而推考之。此种痕迹,又分为二类:其一,本身即为过去现象之一部分者,如地层化石、古动物骸骨及古器物之类是也。其二为某时某人对某现象直接或间接所得之印象,如史传、游记之类是也。而专以前一类为研究对象者,如地质学、古生物学及考古学是也。其研究对象兼前后二类者,历史是也。”如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史料,张其昀对此揭示得更为清楚:“典籍者,古人思想行为之遗迹也。古人已往,不能亲观,彰往察来,典籍是资。历史为间接之方法,无典籍即无历史,故典籍为史学之起点。”
学衡派认为搜集史料为史学研究的第一步,“寻求史料为历史家技术之最先的并最要的部分”。他们主张搜集史料的范围应当尽可能地宽广,柳诒徵提出:“钱币、金石、甲骨、符牌、印押、器具以及画像、图绘,皆研究史学者所当究心,姑就狭义而言,则书籍文牍,无往而非历史,其目录家所列史部诸书,又狭义中之狭义耳。其实经史子集,以至小说报章,佛道耶回各教诸书,凡属人类过去之思想言论事实记载,皆在历史范围之中。”他的视野显然已经不囿于传统史学的界限,一方面他认为应当打破传统经史子集各门类的界限。尽可能地拓展文献资料的范围。另一方面他已经注意到了钱币、金石、甲骨等文物考古资料的重要性。一代史学大师王国维在《学衡》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有一篇也谈新的文物考古资料的发现和运用对于学术事业的促进,他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山东曲阜县,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他敏锐地注意到,当时新发现的甲骨等新材料必将又是对学术事业一次极大的推动。其影响不亚于孔壁汲冢所出:“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能比者也。”王国维在其名著《古史新证》中将这一文献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思路系统化,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在这一点上,学衡派与王国维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广泛搜集史料后,学衡派认为必须对史料进行细致的整理,以确定其价值,有选择地加以使用。对于史料价值的确定,陆懋德提出了“原料”(Primary Sources)和“次料”(Secondary Sources)的标准:“‘原料’者,乃指‘最初之材料,即指由此以上不能再追其根源’者是也。所谓‘次料’者,乃后起之材料,即指‘由现存的或可寻的原料之中变化而出’者是也。此即所谓次料出于原料,而原料为次料所自出。”原料的价值,显然远在次料之上。因此在史学研究中,要尽可能地使用原料,“运用史料,大抵作史者或是作古代史,或是作现代史,其时代虽有不同,而总以取材于原料为主。故批评史书之价值,全以是否根据原料为定。”可见史料的来源与其价值高下息息相关,故此学衡派十分注重史料的来源,他们认为考证史料的来源是确定史料真伪的主要途径:“今之治史学者,罔不以考证史料为务,盖史料征实,始可从事编纂,然不知史料所自来,仅凭本文以意之,亦不能明其真若伪也。此审查史料之来源为尤足重也。来源正确,则史料不烦考而信矣。”不言而喻,越是第一手的、直接的材料,其价值就越高,陆懋德对此颇有心得,他强调原料必须是“直接的材料”,“直接材料必本于直接观察”。直接的材料分人证和物证两类:“所谓人证(Testimony),即谓亲见此事之观察的实证。所谓物证(Circumstantial evidence)即谓发生此事之情形的实证。”也就是说,必须是与历史事件直接相关的人与物,才具有最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