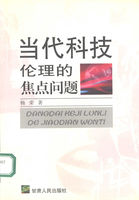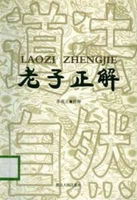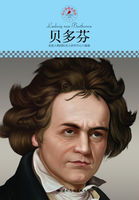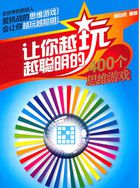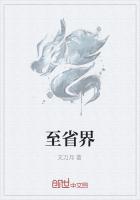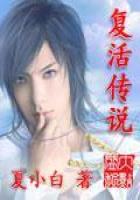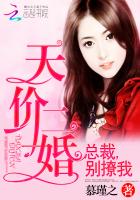中国思想文化界当时已处于欧风美雨的冲击下达数十年之久,传统的思想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必然要有所变化才能存在和发展。在西潮冲击下的中国思想界的变化有两个方向:一是全面的吸收西方思想,从体系到方法,无有遗漏;二是力图从传统中发掘有用的资源,与西方抗衡和对话。很显然,缪凤林、景昌极阐发唯识论是属于后者。我们看到,缪凤林、景昌极的哲学思想的归宿仍在于道德实践,仍是在传统的范围内。但其运思理路中显现出了高超的思辨智慧,具有完整的体系,论证中也运用了相当于西哲逻辑方法的佛教因明学,总体上显示出高度缜密和精致的特点,这又与传统哲学不尽一致,倒有几分西哲的特点。这当中可以看出近代以来中国倾向于维护传统的学人之苦心。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比较,有体系完备、论证缜密等特点,为在这一点上与西哲比肩而立,又不愿意完全借助于西哲,学者们于是转而求助于唯识学。沉寂千余年之久的唯识学近代以来在学界大兴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熊十力说:“佛家于内心之观照,与人生之体验,宇宙之解析,真理之证会,皆有其特殊独到处,即其注重逻辑之精神,于中土所偏,尤堪匡救。”熊十力这里所说的佛学,主要是指唯识学。章太炎也说:“盖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缜密矣。是故法相之学于明代则不宜,于近代则甚适,由学术所趋然也。”显然,章太炎认为法相唯识学具有思辨缜密的特点。唯识学正是有这些独到之处,它才为近代一大批学者重视。他们试图借重唯识学建立的思想体系,既不失本土的特色,又在学理上可以与西方哲学对话、抗衡乃至超越。缪凤林、景昌极即体现了这一思路。从学术上讲,缪凤林、景昌极等人对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重建是有贡献的,他们的努力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重建工作的一部分,体现了哲学本土化这一重要的方向。
与学衡派几乎同时兴起的现代新儒家的运思路向与学衡派大致相似。他们思想都是以弘扬道德为主旨的。而在思想构建中,都在借助西学的同时,又发掘传统的思想资源,致力于哲学本土化的建设。同学衡派一样,唯识学一直都是现代新儒家所依赖的重要理论。具体来讲,缪、景二人的思想与现代新儒家之间又不完全一致。他们的分歧实际上就是佛儒的分流。与现代新儒家的援佛入儒不同,缪凤林、景昌极其最终的思想指向是佛,他们认为,佛家要比儒家高明,但佛儒的精神又多是一致的。缪凤林在阐述“命”的概念时说:“儒家之于命,仅知其当然,且信其当然,而莫识其所以然也。然彼既知有命,故虽处境,栖栖遑遑,而胸中浩然,常有坦坦荡荡之乐,毫无怨天尤人之念。其牖民觉世之心,亦不以是稍易其初衷,且益努力于人格之修养。所谓‘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此则儒家知命安命立命之真精神,似又与唯识家若合符节矣。”由此可见,缪凤林、景昌极在佛儒之间偏向了佛,同时又对儒家保持了肯定的态度。由于偏向于佛学,在人生态度方面,缪凤林、景昌极显得相对消极,他们认为人生是空、是苦,因此须用种种方法修行以解脱之,是出世的。这与传统儒家勇猛刚健、积极人世的态度异趣。同是研习唯识学但以儒为本的熊十力的有关论述正好可以说明缪凤林、景昌极与现代新儒家之间的差异。熊十力说:“佛家对于一切行的看法,盖本诸其超生的人生态度。超生,谓超脱生死,犹云出世。彼乃于一切行而观无常。观者,明照精察等义。无者,无有。常者,恒常。观一切行,皆无有恒常。申言之,于一切物行,观是无常。于一切心行,观是无常。故说诸行无常。唯作此种观法,方于一切行,无所染着,得超脱生死海。此佛氏本旨也佛氏说世间是一个生死大海。人生沦溺于其中,可悲也。所以佛家说无常,即对于一切诸行,有呵毁的意思。本论谈变,明示一切行,都无自体。此与佛说诸行无常旨趣似相通,而实有天渊悬隔在。佛说一切行无常,意存呵毁。本论则以一切行,只在刹那刹那生灭灭生,活活跃跃,绵绵不断的变化中绵绵者,相续貌。刹那刹那皆前灭后生,不中断故。依据此种宇宙观,人生只有精进向上。其于诸行无可呵毁,亦无所染着。此其根柢与出世法全不相似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衡派是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每个人的思想有时不尽一致。吴宓的一些言论中倒能够体现出儒家精进奋勇的精神:“夫欲杜帝国主义之侵略,而免瓜分共管灭亡,只有提倡国家主义,改良百度,御侮图强。而其本尤在培植道德,树立品格,使国人皆精勤奋发,聪明强毅,不为利欲所驱,不为瞽说狂潮所中,爱护先圣先贤所创立之精神教化,有与共生死之决心。如是则不惟保国,且可进而谋救世。”应该说,学衡派中,吴宓的思想偏重于儒家,只是他对自己的思想没有进行很多深入的发挥。
从纯学理的角度讲,学衡派的哲学思想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尤其是景昌极和缪凤林构建了相当完备和精致的体系。但在学术之外的现实世界中,他们的思想默默无闻,几乎没有任何反响。本来,我们不应该苛求每一种学术思想在社会生活都有巨大的作用和强烈的反响,学术上的意义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意义。但是学衡派是以救世为宗旨的,因而他们遭受冷落就有悲剧的色彩和反讽的意味。这其实是学衡派的必然命运,因为他们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委实悬隔太远。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摆脱民族危亡,学衡派的道德理想主义,对完成这一课题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即在文化上强调民族主义并不能有效地完成民族自强、自立等民族主义的任务。大量地借鉴、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成果倒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必经之路,而西方近代文明又恰恰是学衡派不遗余力地批判的对象。这样,在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现实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主流思想的历史情景中,学衡派的道德理想主义遭受冷落几乎就是注定的了。此外,学衡派的思想在学术上讲不乏深刻之处,但这种深刻在社会现实中往往流为艰涩、琐碎与脱离常识,很难为一般民众理解,更遑论同情与共鸣。与学衡派思想相似的现代新儒家的历史命运与学衡派略有共同之处。在思想学术领域,他们始终是活跃的一支力量,一般认为,他们在思想界是与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比肩鼎立的三大流派。但从对社会的影响来讲,现代新儒家无法与其他两大流派相提并论。方克立先生对这一现象的论述充分反映了现代新儒家乃至学衡派的尴尬处境:“七十年来,现代新儒家派中不乏硕学鸿儒,他们一个个著作等身,名扬海内外,但是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群众基础的‘新儒学运动’(这是他们自期的)。新儒家的影响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学院内和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一般老百姓是根本不管你那一套‘内圣外王’、‘返本开新’的。由于他们实际上也未能提供出一套对组织现代化的生产、经济运作、政治管理有效的外王学问,所以不论在大陆,还是在港台,新儒学都是不受当局重视的,最多因弘扬民族文化有功而受到一下褒扬。”对于学衡派派来讲,他们的命运似乎更具有悲剧色彩,因为即使在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也没有现代新儒家的荣光,而是长期地处于被人遗忘的境地。
此外,在学衡派思想中还表露出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倾向。首先,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唯道德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在他们看来,世间的最高价值莫过于道德实践,个体价值的最终完成必须以对道德信条的体悟和践履来实现。由此推而广之,一切社会问题也可以通过提倡道德实行、推行道德规范而解决,“一人一家之连命,即一国之盛衰,一民族之兴亡,世界文化之进退,靡不以道德之升降,大多数人人格之高低,为之枢机。因果昭然。中西前史,可为例证”。在他们的论述中,甚至有把道德价值作为唯一价值的趋向,其他的事功乃是不重要的,甚至是无意义的。不能否认,道德价值是人类社会诸价值中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强调道德准则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是极其必要的。就个体而言,圆满实现道德价值也是个体完善必不可少的课程。但是,将道德律令视为绝对的、最高的乃至是唯一的价值却有偏狭、独断的危险。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注重伦理关系的探索,对于人伦之外的世界则关注不够,这种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伦理观念、政治模式足以维持传统社会的平稳运行。但近代以来,西方的武力入侵打破了中国社会固有的平衡,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仅靠传统显然难以应付这一危机。中国近代的历程,实际上就是拓宽视野,学习西方的科技、经济、政治、思想,变革传统以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至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呈现出多元的迹象。但学衡派对这一历史变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仍然固执地认为只有德治才是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唯一的灵丹妙药。对于西方近代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他们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排斥态度,因为他们相信科技的发展导致了道德堕落。这种偏狭的批判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状况而言可谓是文不对题。当时中国社会之所以存在种种问题肯定有道德堕落的因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多的问题出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乃至思想意识的落后,这需要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这些方面的建设中。仅靠体验内生活、参证无上菩提和实行道德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民族危机。
由于其唯道德主义的思想倾向,学衡派在认识论上又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艰难地挣扎。他们继承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道德理性,以详密的论证形成了一整套关于道德法则、道德实践的学说,其中充满了大量的思辨智慧和理性的光芒。但是由于要证明亘古不变的道德律令的存在,他们的学说中又有大量的非理性的成分。无论是白璧德还是缪凤林、景昌极,他们都设定了一个终极真理的存在,而这一存在是无法用人的感性和理性感知和辨明的,只能借助于直觉、参悟,因而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这种非理性的论证实际是要求人们对至高无上的道德律令的无条件服从和实行,而拒绝理性的分析和思考,实际上又带有愚民的蒙昧主义的倾向。
学衡派的道德观也非常容易导致****主义的发生。学衡派认为道德是亘古以来不变不易的超时空的法则,不承认道德的时代性。他们心仪的道德标准也取法自西方的古典文明和中国的传统社会。他们对于西方近代时代变化引起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持否定态度,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批判更是深恶痛绝,攻击不遗余力。事实上,无论是学衡派的道德观还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的道德观念,作为多元道德观念中的一元,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学衡派的道德观念强调群体的利益,新文化运动派则主张个性解放,都具有充分存在的理由,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二者应当是并存与互补的关系。但一旦企图以单一的道德观念独霸一尊,宰制群伦,就走向了独断论,这样单一的道德标准,常常会成为****主义的工具。应当说,学衡派独断的趋向是十分明显的。缪凤林、景昌极在宣扬唯识论时,将凡是与唯识不一致的思想列为“外道”,都属于破的对象。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尤其是思想界已经非常艰难地出现了由一元向多元转化的端倪,这一转化虽然在后来没有变成现实,但仍是值得珍视的。学衡派的思想趋向实际与此背道而驰。中国近代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无论何种思想形态高居庙堂之上,将其他思想视为异端而压制,这种思想形态就与独裁专制如影随形,难分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