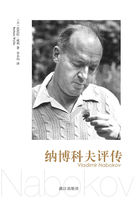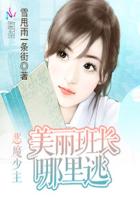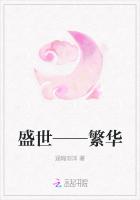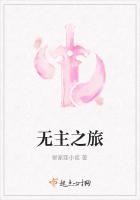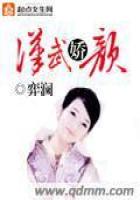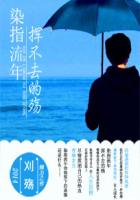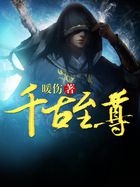六、董伯纯事件。至在行中立汇透支,在外搭伙做生意,用私人,不会做生意,不负责任,不知银行为何事等,尚不算在内,且一般人并不觉到是什么坏事。中国银行分行经理中,人人都具至少资格之一。”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陈光甫提出,应该编制会计规程和办事细则,以求精简业务手续,让客户不用长时间等待就能轻松办好业务,也让职工从繁琐的业务程序中脱离出来,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于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会计制度应运而生。制度加强了业务手续中的牵制和监督作用,为了降低出错率,他要求职工每天都要平衡账目,核实库存现金,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解决。
陈光甫一直在用人方面狠下工夫,就连一般职工,都是通过严格的考试择优录用的。当时的上海金融界,无论是钱庄还是银行,无论其规模是大是小,主要员工大多是亲戚故友,很少重用外人,而陈光甫却大胆任用不相识之人,且一律通过考试录用,对亲人朋友一视同仁,坚决不搞特殊化。
陈光甫很有魄力和胆识,对能做出成绩、表现优异的职工都会委以重任,一旦看到有合适的人选,就会千方百计地把此人网罗到自己麾下。当年,陈光甫想成立一个调查部,可是一直苦于找不到胜任的干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资耀华发表的一些关于人事管理、信用调查等文章,这里面的观点和思路让陈光甫大为赞赏。陈光甫就四处打听,发动各路朋友协助寻找,最后终于有机会能与资耀华进行交流。而就是这一次谈话,两个人十分投缘,陈光甫当即拍板决定,一定要让他来当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的经理。之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很顺利地办了起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有一个往来部,主要任务是把折子送给客户,请他们用款,而且要根据客户的情况给他们制定相应的金额限度(与今日的信用卡相似)。相比其他部门,这个部门经理的素质要求要高得多,既要有广阔的人脉,还要对客户的情况,包括一些重要大佬的个人喜好、习惯等情况了如指掌,因此往来部经理的地位相较于其他部门经理也要高得多。只是让很多人跌破眼镜的是,陈光甫找了一个看上去其貌不扬、又矮又胖、呆头呆脑甚至有些结巴的人做了往来部的经理,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光甫的选择是对的,这个人是典型的大智若愚,看似愚钝,实则精明得很,做往来部的经理游刃有余。
一路坎坷,顽强不屈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以来,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存款数额不断增加,给国内银行业填补了一项又一项的空白,历来给世人以严谨健康向上的姿态。殊不知它也曾历尽艰辛,遇到过重重困难。
在陈光甫锐意创新和独辟蹊径的经营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迅速在上海金融界立稳了脚跟,且悄悄吞噬了大量旧有钱庄和外商银行的业务份额。新势力的闯入必然会引起旧有霸主的排挤,日益加重的威胁感让各大钱庄和银行纷纷采取手段抵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前文中提到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建之初推出一元开户,同行派人故意开上百个账户的事情,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遭遇的最早排挤。
再后来,随着实力逐渐雄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每每到各地开设分行,几乎都会引起当地钱庄和银行的联合围攻和抵制。192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通分行的业务发展迅猛,从当地钱庄手里抢了很多生意,倍感压力的南通大大小小钱庄联合起来以“违背公所约章”为由断绝了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通分行的一切业务往来。后经时任总商会会长张謇出面调解和帮助,问题才得以解决。
除钱庄以外,外商银行也视这个新生力量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前,我国的国外汇兑业务几乎由外商银行垄断,以至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也基本上都由外商银行经营,为此,陈光甫不但提出了“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还在1918年花50万元设立了国外汇兑部,聘任国外银行家为顾问,派遣优秀员工赴国外学习外汇业务,开创了我国私人银行经营外汇业务的先河。陈光甫说,只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多做一笔生意,外商银行就会少做一笔生意。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明目张胆地嘴里夺食的行为触怒了外商银行,势力最大的英国麦加利银行宣布拒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外汇合同。不过,外商银行的傲慢与偏见不但没有让陈光甫屈服,反而使其越发坚韧,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陈光甫也宣布将不再接受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麦加利银行及其他外商银行大惊,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另眼相看,最终麦加利银行妥协让步,两行恢复了业务往来。
虽然陈光甫与外商银行针锋相对,但是对于国内钱庄和银行,陈光甫一直宽容相待。曾拒绝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往来的一家老钱庄,后来遭遇困境,向陈光甫求助,陈光甫很干脆地出手相助。诸如此类的事情屡见不鲜。陈光甫宽容大度的品质在业界流传开来,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也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金融业的发展更加顺风顺水。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于“一战”时期的1915年,那时候国内没有一天太平,到处都是普通百姓避无可避的“匪患”。国家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每一处分行的开设都可以说是一段曲折的故事。
无锡、常州都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粮行堆栈不胜枚举,尤其是运河两岸布满了米坊。当时,外地粮商都喜欢将粮食运到无锡运河边上,如果价钱合适,就卖掉,如果遇到粮价下跌,就选择在堆栈寄存,用粮食向堆栈押款或者用栈单的形式向银行抵押借款,以利于资金周转。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早的分支机构就是开在无锡和常州。上海总行创立的同年秋天,陈光甫为了开拓经营范围,就在这两处开设了代理处,专营堆栈押款业务。
无锡分理处因业务蒸蒸日上,后升级为办事处、分行。1927年时,因时局动荡,工人罢工接连不断,故一度停业。常州分理处最早只是经营押款汇兑业务,后来发展速度也很快。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兵刃相见,史称“江浙战争”或者“齐卢之战”。常州不幸处于战区,银行业务几乎完全停滞。第二年,孙传芳与张作霖为争夺江苏和安徽的地盘又起战火,战争结束后,找不到组织的溃兵就落草为寇,流窜在常州一带。悍匪横行使得常州经济极为萧条,直到1929年,常州分行才恢复营业。
1917年,总行聘请苏州贝哉安先生出任苏州分行经理。贝家在苏州是望族,后来被称为“金融世家”,贝哉安本人很善于理财,曾做过苏州知府的幕僚,掌管赋税和财会工作,人称“钱谷师爷”。他的三儿子贝祖贻是中国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后出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总裁,他的孙子贝聿铭更是被誉为20世纪最成功的建筑大师。言归正传,贝哉安上任之时,苏州已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江苏银行三家官办银行,私人银行则仅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家,别无分号。苏州在清末民初一直是江苏省的行政中心,各行各业都极为繁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此广开储蓄存款业务,收获颇丰,除了1931年长江水灾时业务稍受影响之外,其他年头的储蓄量都是有增无减。此外,汇兑业务在这里开展得也不错。
1924年,江浙战争打响,很多苏州人纷纷前往上海避难。这时苏州分行对储户特别照顾,特许苏州储户可以凭借存折到上海取钱,汇款也不收取任何费用。1927年,苏州分行因时局骤变暂时停业。1932年,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遭到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奋勇抵抗,一向相对安全的上海也变得惶惶不可终日。这时,苏州分行和南京分行一起代兑中央银行券,为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救济农村事业方面,苏州分行也很积极,开设了农产储藏所和农家抵押贷款所。
安徽临淮支行设立得比较早,在上海总行设立的第三年就由唐寿民在此开设分理处。当时主要经营汇兑贴现等业务,存款并不多。因经营日久,口碑逐渐传扬开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临淮很受欢迎。1922年,临淮发大水,银行不免受到一些影响。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奉军南下,二者相争于临淮,兵灾给地方经济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幸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未雨绸缪,对战争有了充分准备,所以损失不大,但是不得不中止营业。次年复业。第三年就发生了石友三劫银一事。
石友三这个人在历史上以反复无常闻名,曾多次投靠冯玉祥、******、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以及共产党,后又先后背叛。“火烧少林寺”这样的疯狂举动也是他干的,再多一件“银行劫银”对他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
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冬,济南因为银根奇紧,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临淮分理处遂向济南分行运送现款,助其渡过难关。当时运送的是5万元现洋,分别装在10个箱子里在火车站候车。本来是下午三点半的快车,可是等到五点还不见火车的影子。押款负责人到处托人打听,才知道有6列兵车过境,运送的是臭名昭著的石友三的部队。
这可怎么办,整整10箱现洋要是让这些兵痞看到了还能留得住吗?银行方面马上联络铁路局,希望能找到隐蔽的地方,把现洋暂存一会,但是铁路局方面不肯担责任,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担当不起。银行无奈,只得原路返回临淮。出站没多远,石友三的兵车就到站了。大兵们本是为了缴驻扎临淮的刘合鼎部队的械而来,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立即追了上去,搬运现洋的扛夫们看到大兵追来,丢下银箱就跑,石友三不费吹灰之力就劫到了5万元现洋。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员眼睁睁地看着这支暂时属于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现洋,却丝毫没有办法。他们只能记下这支部队的番号,回去上呈总行,请上级出面通过银行业公会转告财政部,再由财政部向军方交涉,希望可以挽回损失。军部无端得了银子哪还有退回来的道理,只是推诿说正在调查中。这件事就成了无头公案,最后不了了之。
安徽蚌埠位于淮河中下游,面向珠江三角洲,拥有千里淮河的第一大港口,目前是全国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城市,被称为“两淮重镇,沪宁咽喉”。 1918年,中国运输公司看准了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在蚌埠设立了分公司。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嗅到商机,即刻派李济民先生到中国运输公司为其办理押款业务。初始的条件很艰苦,没有办公大楼,只好寄居在运输公司内部,后来又迁到著名的寿丰面粉公司,继续营业。没过几个月,遇上大火,面粉公司被焚毁,银行的办事处只好再次迁址,搬到了利兴公司。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蚌埠的发展总是与火神结缘,利兴又遭受了火灾,银行接收的押款货物没能幸免于难,损失20多万元。经过一番清算,银行在蚌埠两年的盈余全都折了进去,仅剩血本。陈光甫见此狠心设立了单独的办事处,不再“寄人篱下”四处搬迁。
蚌埠为皖北门户,张勋、倪嗣冲等手握重兵的人都以此为根据地,大军进驻,征发频繁。袁世凯称帝后,军费激增,耗尽国库,北洋政府命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止纸币兑换银元,引发了挤兑风潮。中国银行在上海应对得很好,它直接抗命,继续兑换现银,没有引起慌乱。但是蚌埠不比上海,这里的军人手中还有很多没来得及兑换的中国银行纸币。这些大头兵哪管你是中国银行还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反正你是正在营业的银行,就得给我兑换银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蚌埠分行陷入两难,拒绝的话会引起这些军人的反感,保不齐出现冲突;兑换的话摆明了吃亏,等于白白把银元拱手送出去,收回的是已经没有价值的纸币。怎样应付,愁坏了主持蚌埠分行的负责人。
好容易应付过去军人强兑,北伐战争又开始了。南边的吴佩孚最先遭到打击,孙传芳见机马上向张作霖示好请求援助。张作霖就命奉系的张宗昌南下支援。北洋军阀方面不断有将领阵前倒戈,北伐军节节胜利,张宗昌亲征合肥,围城三月也没有攻下,见孙传芳已然逃到江北扬州,他也不再坚持,准备回济南老家。败走之时,路过蚌埠,因部队军粮缺乏,竟打起了银行公记堆栈的主意。公记堆栈里放有作为银行放款抵押物的粮食,张宗昌直接派兵围住,公然抢劫。后再三交涉,这支名义上属于政府军的部队同意以鲁省钞票结账,七折八折之后,银行方面损失近20万元。幸好公记堆栈并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家独有,而是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金城银行等四家银行共用,所以损失经过各家分摊之后才不至于伤筋动骨。
虽经多次磨难,蚌埠分行因经营有道还是逐渐兴盛起来,在1931年春天达到鼎盛时期。
无论是人还是物,历经诸多困境,成长得会更加茁壮。虽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路走来,坎坷不断,但是有了陈光甫和所有员工的坚持不懈,困难被一一化解,成为这家百年银行顽强不屈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