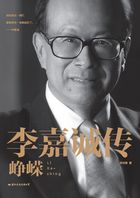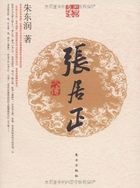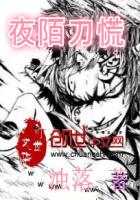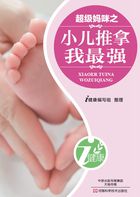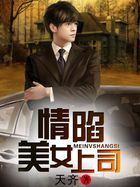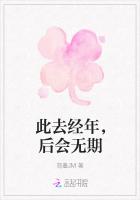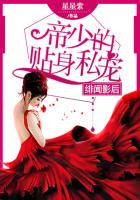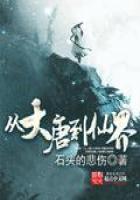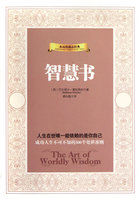南京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巩固其统治,也出台了一些挽救和复兴农村经济的举措。比较重要的有制定土地法规,根据当年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颁布了《土地法》,规定了地租限额,防止了地主无限制地剥削佃户,还对农村的无主荒地加重税率,对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村土地使用率都有积极的作用。可惜的是《土地法》虽好,却没有贯彻落实,成了一纸空谈。针对全国大面积的旱灾,政府建设委员会的张静江提议兴修水利,加强土地灌溉工程的建设。政府采纳了张静江的建议,将全国的水利工程建设督导权交给了新设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还命令各省建设厅务必负起本省的水利工程建设责任,接受经济委员会的安排。1937年之前,全国共完成了13个灌溉工程计划,这一举措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除了兴修水利,政府还设立了中央农业试验所,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陆续增设了农学院,着力培养农业技术人才。
关于旧中国的农村金融状况,提起来就是一部贫苦农民的血泪史。农村资金短缺、金融机构太少、农业经济停滞不前等问题是旧时农村的普遍现象。农民借钱,除了亲戚朋友之间互相接济之外,就是向地主、土豪、奸商等借高利贷了,稍微发达一些的地方有少量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银行。但是,相比较工商业贷款而言,农村贷款的利率更低,而且往往数额小、手续多,再加上农民都是靠天吃饭,还贷能力不稳定,所以一般银行都不愿意发行农村贷款。
不过,陈光甫对此事却很上心,他说:“此种贷款不特时短,具有流动性,数量零星,甚为稳妥,而且对繁荣农村、辅助农业经济之发展有很重要意义。”【范卫峰,郑华玲.晋商就是官商勾结的代名词吗[EB/OL].新浪财经网,2007-4-3.】他认真思考过怎样把钱贷给农民才能发挥更大的意义,因为此前并没有哪家银行有过农业贷款的经验,所以农民能否接纳贷款;银行是否要承担巨大的风险;银行的营业机构都在各大城市,贷款到底委托谁发放到农民手里,这些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此,陈光甫专门给金陵农业大学校长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对发展农村经济的看法,提出信用合作机构是比较适合在农村发展的金融机构,把贷款交给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下去比较安全。他还在金陵农业大学设立了奖学金,鼓励学生毕业后发展农村建设。
陈光甫做事一贯谨慎,发放农业贷款也是先在小范围内试行。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北平的华洋义赈会合作,发放了2万元到合作社,后全都按时收回。然后在江浙两省较为完善的农业合作社发放,受到热烈欢迎,后来又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村贷款在还贷方面的表现出乎一般银行的意料。到期之时,全额收回,没有损失,还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陈光甫感慨地说:“吾国农民之道德,尚未衰落,不虞外侮,他日中国尚可复兴也。”
这一善举并非陈光甫沽名钓誉、心血来潮的一时之举,他坚持了数十年,在发展农村金融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了陈光甫的成功在前,几年以后,其他银行开始纷纷效仿,相继开展了农村信贷业。特别是1935年,国民政府干脆把原来的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直接介入农业贷款领域。
中国农民银行是国民政府四大国有银行之一,虽然名字叫“农民”银行,而且政府明令公布《中国农民银行条例》,宣称该银行是“经国民政府之特许,为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之改良进步,依照股份有限公司之组织设立之”,而且根据条例的规定,农民银行的营业范围为为农业发展放款、为农民组织的合作社放款、为水利备荒事业等放款,但是熟悉它的人都知道,这又是国民政府的一个“欺世盗名”的伎俩。******当初设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剿匪”筹集军费。它的前身就是国民党“剿总”内部设立的一个农村金融救济处,后因救济处不能发行钞票而改称“银行”。四省农民银行深受******重视,******不仅亲任理事长,经常过问营业情况,还下令从鸦片税款拨出250万元作为银行的股金。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军事存汇款业务占据了整个银行业务的2/3还要多,放款方面更是以垫支军费为主要方向,为军队筹集军饷、代购军粮。
至于《中国农民银行条例》中提到的农贷业务则是顺便做做。抗战爆发之前,该银行对农业方面的放款比重不到1/5,抗战之后更是减少到1/10。尤其可恨的是,可怜的放款层层审批下来之后并没有多少到老百姓手里,而大半被乡绅包了,变成他们放高利贷的资本。
开办农村信托业务更是空谈,中国农民银行以搞信托为幌子,做起了商业投机生意,主要倒卖食盐、粮食、棉花等农民生活必需品以谋取利润。1949年,中国农民银行被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接管。
其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农业贷款上投入的数目并不是很大,但是它的探索,体现了陈光甫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商业触觉,同时对农村经济的建设、农村金融制度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重风险管理,为维护信用不惜得罪政府
与陈光甫同时期的银行家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张嘉璈、李铭、周作民、钱新之等都是有学问、有经验、有管理手段的一时人杰。他们经营的银行制度科学规范,重视人才培养,相互之间有合作交流,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有了风险防范意识和相应的规避风险的举措。
近代银行家们在发放贷款方面不敢效仿财大气粗的票号。山西票号一向号称“海内最富”,与王公大臣等上流社会有很深的渊源,他们放款全凭信用,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信赖,那么借多少银子随你开口,能如期奉还,就当交了这个朋友;到时候没还上,就自认倒霉。近代银行家们没有这么豪爽,更不欣赏这种中国式的信贷情谊,他们只相信抵押贷款。你有值钱的抵押品才能拿到真金白银,否则一概免谈。这样虽没有“万两银子一句话”那么潇洒,却安全可靠得多。
银行家们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预防风险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风险要分散。他们认为在放款时,银行“不可偏于一种职业之顾客,其在平时,虽无任何变动情事,究以采取危险分散主义,俾谋平安之为是”。对于选择抵押品来说,“如抵押品偏于一种物件,则经济界一有变动,其市价跌落时,势必难于立即脱手,故抵押品不偏于一种,其危险分散,较为平安也”。所以无论是放款还是选择抵押品方面,都把“风险分散”作为指导思想。
以陈光甫一贯谨慎的作风,当然更加重视对于风险的防范。20世纪30年代初,市场出现动荡,陈光甫立刻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所有分行发出了通告,明文规定放款时“不可多放同样工厂”。在投资民族工商业上,陈光甫也坚持风险分散的原则。193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别对70多家企业进行过投资,但是超过5万元的只有10家。
“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曾经邀请过专业人士来指导银行的调查部如何更好地展开调查工作。那位叫刘大钧的专家就提出“各厂号之信用,非一成不变者。今日信用为一等,明日或以亏蚀而降为二、三、四等,反之如营业有进步则本来为三四等者亦可升为一等。至于经理人之品行才力,与信用有密切关系,此皆非一两次调查所能得其梗概者也,必须详知该人该号以前之历史及随时营业情形,然后方能确定其信用之程度”。在他的指导下,金城银行调查部对信用调查的动态把握有了深刻的了解,由调查部职员提交的正式报告深受银行高层重视。总经理周作民就指示每周的“经济调查报告”分寄平、津、沪、汉、郑五分行副经理参阅,足见其重视程度。
1928年,天津瑞通洋行发生了一起金融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起因是天津协和洋行的总经理祁乃溪因经营失误,导致了大额的亏空。他不愿意面对现实,就和美商串通,造了假的销售单据,以瑞通洋行的名义向各大银行申请贷款。骗局揭穿时,很多银行在天津的分行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只有谈荔孙领导下的大陆银行没有被波及,这与他平时注重风险管理大有关系。
商业情报调查是企业正常运作的基础,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没有全面、准确、及时的情报支持,可以说是一步也迈不开。因此,商业情报信息的收集与调查能力的高低也是西方银行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例如,如今举世闻名的国际投行高盛银行,其在经济情报领域的收集与分析能力,比西方大国的国家级情报机构如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以色列摩萨德等还要强大。
早在90年前,陈光甫就发现了商业情报调查的重要作用,并将其运用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发展之中。在1920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首先扛起了市场调查的大旗,成立了调查部。陈光甫为调查部分派了两项最重要的任务:一是商情调查,即调查国内外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二是客户调查,包括国内各重要企业的资本、信用、营业甚至企业老板的性格、家庭、社会关系等情况。具体而言,要完成这两项调查一般会遵循三个环节:放款前审查、放款后控制、信用风险补救。
其实,要想做好详尽的市场调查,仅仅凭借调查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光甫深谙此道理,于是让银行所属各部、处,以及各地的分行也加入到向总行报告当地市场情况的行列。除此之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常常召开各种专业研讨会,预测市场,以供领导决策参考,尽可能地减少经营的风险。
除了加强商业调查以减少经营的实际风险外,陈光甫还十分重视银行的无形资产——声誉,凡是有损银行形象的业务,他一概不接手。
当时,烟土生意十分火爆,而且收益也很高,不少人为了巨额财富而沾染烟土生意,而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名流”是靠着烟土生意发家致富的。也曾有不少人劝说陈光甫接手烟土生意,但他认为烟土是个害人的东西,坚决不允许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烟土生意有来往,更不接受烟土押款业务,以免降低银行信用。
1928年,汉口的烟土商们开始对陈光甫进行游说,用极其诱人的高额回报劝其踏足烟土业,并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提出了押款申请。但陈光甫态度很坚决,以“土押款不合本行宗旨,决勿承做”为由一口回绝了所有人。
在陈光甫致杨介眉函中,他这样写道:
“前次比期风潮实因土帮解散关系。据是比应解三百万,而仅解两成,以致各庄受挤。此间土号共有六十家,禁烟局限令减三十家,两家合并一家,零售、雅室一律禁绝。而土帮之烟均在钱庄做押,并放与雅室之账一时不能收齐,且有藉故不交者,故市面银根骤紧。据花帮云,是日若非我做出押款五十余万元,钱庄必尚有倒闭者。闻汉上存土有一千余万,倘土帮问题不解决,恐市面当有变动。宏裕、聚兴诚均仍吃紧,是日倒闭者尚有协聚一家。兴同、大同为南昌帮,账面仅二三万;同胜、永美和亦已停业,连同德胜账面共计约二十万,由汤子敬请理,拟分四期还清。德胜经理汪耀光因个人做棉花吃亏,当时即行逃避。我行对于存放各庄之款,除裕中、永福近数日内有来商以烟土做押款,连来数次,均经回绝。聚兴诚亦托刘文钦来请通融,当告本行宗旨向不承做此项押款,实无从维持。日前陈化平介绍特业商会会长王君来与顺元商做押款,谓如不帮忙,市面必受极大影响。顺元告以与本行宗旨不合,无法帮忙,只能代为介绍中南、大陆,至该行等能否承做尚不可必。王君不满意而去,且云当由陈化平来谈。弟已坚嘱其坚持到底,即得罪陈化平亦所不计。陈为十九军经理处处长,极力代土帮帮忙,谅因军饷有关之故。土帮连日在太平洋会议,闻尚无办法也。”
由此可见陈光甫维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信誉的决心之大。陈光甫在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就表明:“办银行者第一在于信用。”他认为,银行的业务精髓就是信用,一旦缺乏了信用,银行就不可能长远发展,甚至有可能无法生存下去。他主张“金融贵在流通,流通贵在信用”以及“唯一是要恪守对顾客的信用”,以此求发展,稳固经营。就这样,在陈光甫的一再强调下,“诚信为本”成为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基本的经营之道,并一直坚持了下来。
客户总会担心银行拿自己的储金在做些什么投资,一旦银行进行激进、有风险的投资,客户的信心便会动摇,银行的信用度紧接着也会降低。陈光甫深知客户对银行的重要性,所以实行了透明制度,将银行进行的各项投资透明化,让客户知道自己的钱流向了何处。而且,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放款时,也从不涉及房地产及股市等风险较大的行业,并提出“不可稍事冒险投机”、“不可接近官场人物”、“不可做出呆滞押款”等要求,力求在客户心目中得到较高信用。
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出现财政问题,于是下令武汉各银行停止一切兑现业务。这一命令直接导致武汉币值大跌,不仅使武汉市经济、市场等各领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也让陈光甫看到了将要面临的巨大危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武汉分行的信用会因此受到损害。因为若是各银行真的听从政府的命令,拒绝兑现,那么势必会引起客户的不满和投诉,甚至会弃而走之,不仅会导致银行信用度下降,还会流失大量客户。
为了渡过这一难关,也为了维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信用,陈光甫毅然赶到武汉,决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武汉分行将继续开展兑现业务,尽可能地满足客户的一切要求,并亲自监督执行了长达6个月之久。虽然这一决定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度亏损200多万元,但它的总体信用度却得到大幅提升,在之后很短的时间里,其业务量就显著提高,单汉口分行的存款额就提高了3倍之多,一跃成为国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知名银行。
1931年夏天,长江流域发生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受灾面积超过了英国全境,40多万人遇难。当时国民政府的公开报道称,此次全国共有16个省遭遇不同程度的洪灾,而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受灾程度尤其严重。武汉地区更是重灾区的核心,只能划船在原本的“九省通衢”艰难前行。如此天灾当头,国民政府仅仅拨发了30万元的赈灾款,这么点钱还被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扣住不发。老百姓们如果坐等政府的救济,恐怕只能见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