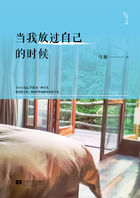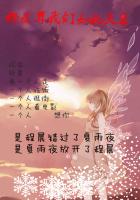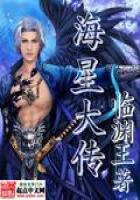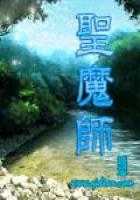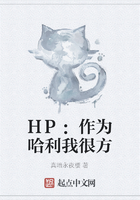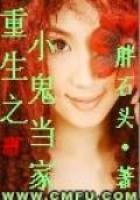对“昭通作家群”的批评是宋家宏云南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尤其是其中屈指可数的以评论见长的写作者,宋家宏见证并参与了这个群体在那贫瘠的寒荒岁月中艰难又不乏温情地守护着心灵的缪斯,对他们的困顿、奋争、挣扎感同身受。其中对夏天敏、潘灵、雷平阳、樊忠慰等人作品的追踪阅读,并在《文艺报》等著名报刊上发表文章,使人们对这个群体创作的整体精神走向有了明晰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宋家宏对昭通作家的研究并非单纯地以表扬评论达到推介的目的,他从一开始关注这个群体的写作,就把他们放置于全国的文学背景下来考量,在这个群体还处于迷茫的探索期时,便及时地以前沿性的理论评析来为他们的文学突围寻找前进的标杆,使他们在增强自信的同时也自觉规避写作中可能存在的误区。由于是对自己熟悉的对象发言,他的评判常常因爱之深而愈显苛严,因此很多昭通作家存在这样的心理:既想得到宋家宏的评论,又怕被他评论!
研究本土文学或隐或显会遇到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宋家宏的云南文学研究起步之初就有着鲜明的建构意识。他不是以“遵命文学”的形式说些不得不说的违心话,以此作为沽名钓誉的资本,而是清醒地知道,对文学批评这一种相对“速朽”的文体而言,如何在有限的语境中坦诚自己的观点,建构自己独特的美学体系,是文学批评家存在的价值所在。在2011年9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一书中,集中呈现了他对云南文学的研究成果,开创了将云南文学研究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大背景下的综合研究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新格局。从宏观上说,宋家宏提出了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概念,如“边地小说与主流文化”、“云南当代文学的两个传统”、“20世纪云南文学”、“云南四代作家群”等。这些概念的内涵是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的,总结起来,就是从云南文学的历史传统出发,打通现当代文学之间的通道,将云南文学百年发展史全景式的统一在“20世纪云南文学”的大背景之下,并根据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历程,研究云南文学的转型路向及与外界保持的张力关系。宋家宏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分野和创作特点,归纳出“云南四代作家群”这一概念,清晰有效地呈现出20世纪云南作家各个阶段的创作特征、作品得失和文学史意义,以及代际之间存在的沿袭、赓续和内在的超越关系。他在对作品进行历时性的纵向研究和共时性的横向比较中,发掘出对当前及今后仍具有借鉴作用的文学资源,为重提“边地与民族”、“城市与现代”等云南文学经验奠定了坚实的立论根基。他逐步完成了云南当代文学“两个传统三次浪潮四代作家”的宏观体系建构,而更为宽泛的“全球化语境下的西部文学”概念,则是他对被误解和压抑了的西部文学内在精神的重新审视,在与中原强势文化进行对比辩驳中,廓清长久以来对西部文学约定俗成的印象判定,为西部文学再一次摆脱困境,实现精神突围建立起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参照。这是他将云南文学研究继续深化的成果,是地域文学研究的又一次理论发展。
宋家宏赞赏印象派批评,并对其多有吸收与借鉴,但他的文艺批评并不是简单的印象点评,细致的文本解读是他一以贯之的批评自律与牍尺。他恪守独立的批评立场,悉心贴近作家的心灵,以平等对话的姿态走进文本,走进作家创作的深层心理。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审美解读,实现文学文本的再度创造,在阐释与评析的过程中,与作家一同建构独立自足的文学世界。他的博识、谦逊、坦率、体恤,令人深为感佩。在其批评视野中,走进了李乔、彭荆风、李霁宇、胡廷武、蒋吉成、范稳、存文学、于坚、张庆国、杨鸿雁、胡性能、杨佳富等云南文坛的中坚力量。云南文学界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很多都得到过他的评论,对一些崭露头角,但暂时没有多大影响的青年作者,他也能敏锐地发现其创作潜力,并给予及时的理论观照,如余继聪、艾傈木诺、谢轶群、任洋等,他都写了评论。在文体选择上,他根据批评对象的实际,充分运用作家论、作品论、文学现象论、文学思潮论等传统的文体形式,以自己所擅长的随笔体批评进行评论。他曾对文学批评大家李健吾、鲁迅、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批评文章做过潜心研读,从他们感性、丰饶、富丽的批评文字中借鉴灵动、自由的因子,在写作中崇尚主体审美感受的阐发和个人灵性的舒展,使得批评文字远离僵硬枯燥的“八股”体式而重获朝气与活力。这种“理性思考,感性表述”的写作方式在《走进荒凉》中就有了充分的体现,在云南文学的评论中显现出别样的风采。
2005年,宋家宏从云南人民出版社调至云南大学成立“云南大学云南文学研究所”,他的云南文学研究从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所成立伊始,便广泛向社会征集云南作家作品,丰富云南作家文库。为加强文学批评人才,尤其是青年批评人才的组织与培养,他呼吁并参与筹建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成功策划了“首届云南省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为集结评论队伍、展示云南文艺批评实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引导青年文学批评力量进入全国性的研究方阵中,他主持开展“云大评刊”活动,通过集中讨论与短评的方式,积极引导在校学生参与当代文学批评。2009年,“云大评刊”与国内知名度颇高的“北大评刊”在左岸文化网同时刊载,受到了当代文学批评界的热议与好评,开始出现品牌效应。云南大学的许多青年学子不禁感叹:没想到自己竟以这样的方式走进了中国当代文学!
三、自省与批判:知识分子的价值启蒙立场
宋家宏的文学批评不仅着力探究文学作品内在的审美内涵,对文学批评本身的文体形态、文体价值和批评家自身的素质建设问题,他也作了积极的思索。他以自身的批评姿态矫正评论写作中常见的误区和弊端,如友情批评和广告批评等,以批评实践来丰富其写作艺术,以随笔体形式规避与抵制文学批评的“八股体式”等。《重建云南文学批评》、《应高度重视批评家的自身建设问题》、《推动云南青年文艺评论家成长的几点想法》等文章,贯注着他始终如一的自审、自省与自律意识,以及对云南文学批评界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现状的忧心忡忡。他是一个有着清醒价值判断的批评家,当商业浪潮席卷文坛,他依然以孤绝的姿态守护着文学批评家的尊严。在近年的写作中,他又有着潜隐的转型和发展迹象,主要体现在《反腐文学的潜价值:呼唤体制创新》和《刘震云笔下的国民心理本相》等长篇论文中,他在尝试着以更宽泛、更前沿的文本解读与理论思考来努力实现自我超越。
启蒙与批判是知识分子最核心的价值选择,激昂的入世情怀与崇高的道德使命是其主要的生命理想。宋家宏深谙“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的伦理内涵,在他近年的批评活动中,融入了大量的社会文化时评。与纯文学批评相比较,社会文化时评的影响力、穿透力要更强大得多,它尖锐地切入社会生活的内核,对引导、改造国民的思想有着更直接的启蒙作用。同时,社会文化时评对一名批评家的道德、良知和勇气也是极大的考验,它往往抵达社会的敏感地带,触及人们生存生活的切肤之痛。如果说《郭敬明夸鲁迅:谁的悲哀》、《浩然:谎言时代的应声虫》、《从鲁迅说到反省》等批评文章还处于文化评说的范畴,那么《烈女邓玉娇掀开的社会危机》、《人心坏了,何以救心》、《培养公民还是培养奴才?》、《21世纪何以重现中世纪奴隶》就以凌厉惊骇的气势,逼近真相的发问,直追死穴的批判,凸显一名批评家独立健全的批评人格和良知。这些文章发表后,读者为他刚劲泼辣的文字风格和尖锐犀利的思想锋芒而喝彩!青年批评家谢轶群认为:“宋家宏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有数十年研究文学和文化的深厚学术功底和专业成就,也有关怀社会文明现状和进程的深沉理念、宏阔眼光、现代意识,以及思想传播技能。在这个现状纷纭、思潮激荡、期待与迷惘同在的社会转型期,他一直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操守,为学生、为文坛、为社会大众提供着鞭辟入里、闪烁着现代文明之光的思想资源。他对‘****’和红卫兵精神的批判、对出版和文化管理体制的审视、对公民意识的呼唤、对落后于时代的现象和思想的揭示和抨击,对世道人心走向的关注,使他的声音越出校园和课堂,一次次出现在震荡海内外的各种公共事件中。”①
认真勾勒宋家宏的文学批评之路,可以探究出这代批评家的精神探索历程与心理轨迹,从中管窥中国新时期三十年文学批评的艰难转折与奋进。三十年间,文学风浪激荡奔涌,批评主体几经沉浮,批评精神纷纷裂变。面对日新月异的新潮理论和风起云涌的良莠作品,宋家宏以他厚实的理论学养、敏锐的艺术直觉和悲悯的人生情怀,前沿而不趋新,稳健而不保守,在精神之境的漫游中塑造着一名理想主义者独立求索的生命形态。
注释:
①谢轶群:《坚守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2年第1期。
(原载《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09年第9期;收入《审美与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丛谈》,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