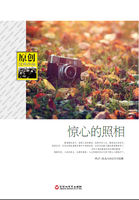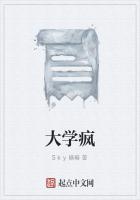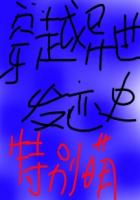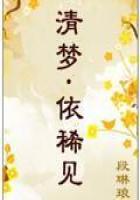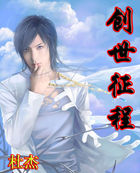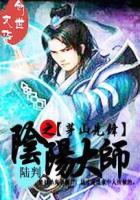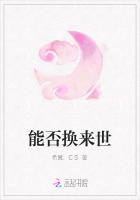列位看官,你道这“吼”字从何而来?“狮子吼”在禅宗里喻指佛说法喝断一切妄想痴迷。话说“红学”成为显学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探佚学当下更是成了显学中的显学。相比之下,考证与索隐这两门学问就有点过时了。索隐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而考证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将索隐的内容聚焦在与作者相关的史料上,这也就需要先行把曹雪芹的三代家史调查清楚。它们都仅限于少数专家的研究,多数的读者并不买帐。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些就是曹雪芹称之为“真事隐”的东西。
探佚学得以存在,有赖于一个基石。这就是全书的原稿曹雪芹是基本上写作完成的,只是后来不知怎么被乾隆读到后,指派程伟元和高鹗把80回后的结尾窜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原稿是如何结尾的(即所谓佚稿)再也无法见到了。这个说法的难点在于,曹雪芹在书里清楚地讲了,他所写的真事是被隐去了的。如果说由于疏忽,个别几处没藏好被发现了,那还差不多。可现在的情形是,竟然有多到几十回的文字整个被看出问题来了。你想,这还能叫做“真事隐”吗?被探佚学捧上了天的曹雪芹又怎么会笨伯到这个地步!
据我看来,书里头像是“以情悟道”,“引觉情痴”和“苦海慈航”之类的说法都是用来作为对“隐去真事”的提示。可探佚学却要说,这些都是作者为了避免文祸而用来打掩护的假语村言。好像《红楼梦》如果有个禅宗的主题,那就未免太不名誉,曹雪芹也跟着太掉身价了似的。要是说曹雪芹在书里头没有提到“真事隐”这回事,那也许还能起到打掩护的作用。现在提都提了,那还打得了什么掩护?就算没事的,也能给你找出事来,更何况还自己承认有事呢!
曹雪芹也是够奇怪的。你隐就隐吧,还公开地打招呼;打招呼就打招呼吧,又自己报出真名实姓,生怕没有人知道似的;这还不算,跟着进一步再把吴玉峰,孔梅溪,脂砚斋,畸笏叟,棠村,松斋等一干亲朋好友的名字全都写在了书上!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像我一样觉得奇怪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吧?经我仔细体会并替他概括了一下,用现代人的话语表述出来,无异于是说:“乾隆,我是曹雪芹。还记得江宁织造曹家吗?对了,就是那个被抄了家的曹家。现在,我把这件事写在《红楼梦》里了。告诉你也不要紧,我使用了一种叫做假语村言的写作手法把它藏起来了。当然啦,书里头隐去的不只是这一件真事,其中还有不少你不愿意见到更不容易找到的清宫秘史。不信的话,先试着找找。实在找不着,也可以去向我的亲朋好友打听打听,他们都是些深知这部书底细的人。我在书里提供了一份他们的名单,问去还是不问,你自己看着办吧。”设想一下,乾隆哪里受得了如此的戏弄?还不派人去把曹家再抄他个无家可归。
前一阵子我去逛书店,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红楼梦》,随手拿起一本翻了翻,发现署名不知何时变成了曹雪芹著,无名氏续。随后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是红学界中反对阴谋说的专家占了上风,认为续书的存在并非是程伟元、高鄂之流政治阴谋的产物。而是民间一个既无思想又无情趣的无名氏,却偏偏有那么一点运气。在他好心地替维纳斯接上胳膊的时候,碰巧保留住了宝、黛爱情的悲剧气氛。续书之所以能与原著并存下来,纯属是一次偶然事件。尽管如此,双方在如下一点上却达成了一致,即续书不论是出自政治的阴谋还是民间的好心,都一样地是赝品。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探佚学有这么一个原则,即:续书与原著必须保持风格与走向的不变,违背这一点都必然不会是同一个人所写,可以断定是赝品无疑。可以说,这个原则简直不堪一驳,它是用常人之心去度雪芹之腹的结果。如果谁心中先存了这样的成见,然后再去读续书,又怎么会不觉得它是赝品呢?而续书是赝品,这是新红学以来最大的一个谬论。在这一谬论的鼓吹之下,探佚学应运而生,它唯一的激情就是在书中找些谜语来猜。但是,探佚学自己也不清楚猜谜最终会在哪里结束,因为谁也不知道在这条“谜途”上,别人会不会走得比自己更远。于是,不知什么人又出来给定了个行规,说:“探佚要适度。否则的话,一味作过度的解读,连自己都觉得不像。”这个话说起来容易,操作起来可就难了。试问,怎样的解读还没有达到度?解读到什么份儿上就算过度了?谁能保证他的度就是曹雪芹的度?而且,就艺术品的创作而论,也不大可能通过公投的方式票选出一个度来,说这就是曹雪芹的度!
把续书的作者由高鹗换成了无名氏,也就是由“好心”说替代了“阴谋”说,这除了给发现隐去的真事制造障碍以外,我看不出有多少别的意义。尽管“阴谋”说与“好心”说都同样错误地不承认续书就是曹雪芹所写的原稿,但“好心”说听起来的确要比“阴谋”说合理得多,想去反驳它同时也就更加地困难。虽然,那也不是说它就无法反驳了。欲知反驳得有力与否,且听正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