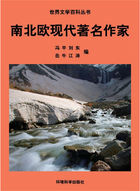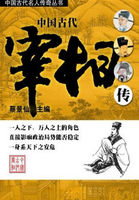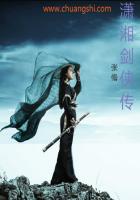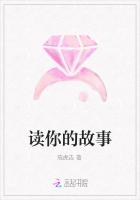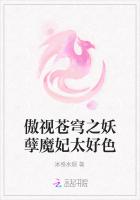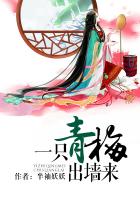******回到南京后,从戴笠口里得知了贺衷寒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所作所为,认为贺居心叵测,大骂道:“我还没有死,就把我出卖了,混蛋的家伙!”不久,贺衷寒被******撤销了军委会政训处处长的职务,要他到欧美各国考察政治、经济情况。回国后,贺衷寒担任了一年多的原职和新成立的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以后,便被******闲置起来,仅从三青团内担任了个临时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
贺衷寒对******的安排,满腹怨气。1941年,他与一位复兴社的兄弟吃醋狗腿,对方喝醉后,大发牢骚,痛骂******“昏暴”。贺衷寒也喝醉了,借着酒兴说:“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
郑介民
“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了。”
(《国民党高级将领列传》第53页)
〔郑介民〕(1898—1959)原名庭炳,字耀全。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黄埔军校二期生。1932年参加“复兴社”,为核心人物之一。曾任华北区区长,参谋本部二厅五处处长,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副厅长,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军统局局长,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国防部常务部长等职。1949年10月退往台湾。
〔解读〕
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新桂系势力的不断扩大,使******颇感不安,时刻想除去这颗眼中钉。郑介民了解到******心思后,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可以凭着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是同学,而且私交深厚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于是正式向******提出。蒋非常高兴,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得令,便神不知鬼不觉,悄悄跑到武汉,租下一家小客栈的下等房间,身着破旧衣衫,装着穷困潦倒的样子,步行去汉口第四军团总司令部找李宗义,谎称失业已久,生活无法维持,特来投效,希望收容。
李宗义看到他那副样子,便毫无怀疑,让他搬到总部同室而居。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老总”,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因“老总”的关系,受到各方面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表面上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李兄”,博得李宗仁的好感。其他一些高级将领,看到李氏兄弟和郑关系这么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这种机会开始倒桂活动。
郑介民收买了总部机要人员,偷出桂系部队联络密码,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秘密送给******,使蒋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李宗仁占领武汉后,为拉拢湖北人,曾提出“鄂人治鄂”的口号,一些鄂籍将领得到重用,引起桂籍将领不满。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的言论。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蒋便派人对那些有意见的将领收买拉拢,分化瓦解,可李宗仁根本没有觉察出他的部队已在内部发生变化。李企图不经中央政府会议批准,擅自越权免去亲蒋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代之以何键。蒋认为时机成熟,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于1929年3月间发动战争。
这时,被******早已收买的桂军李明瑞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却。桂系盘踞在湖北的军队一下子土崩瓦解,******毫不费力地夺取了武汉。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复命。******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又趁机当场把蒋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的称赞。
这一时期郑介民也做了一件令******失信的事,引起蒋的不满,一度对郑冷落。
******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去广西,担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住在南宁。当时俞作柏任广西省主席。郑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广西的桂系。不久,蒋令其任驻防柳州杨腾辉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郑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并同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伙同一气,控制广西省主要财源。广西部队的军政费用便都得仰蒋的鼻息。郑还重演武汉故伎,收买拉拢俞的部下。俞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
1929年秋,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压制困死在广西,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报告,一面连夜赶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
同年10月,俞作柏在南宁发难,通电反蒋。蒋指示郑介民留在广西暗中主持“倒的拥蒋”活动。此时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回南宁,便连夜化装只身逃往广州。不久,俞作柏垮台。12月,郑取道香港,回到南京。当然,这次他去见******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的重视。蒋当面责备他,在控制分化瓦解广西部队方面办事不力,无大成绩;特别使蒋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找过他,他也不敢去见蒋。1932年3月,******成立复兴社,郑介民被选为社干事会干事。该社成立特务处,郑被蒋指定为副处长。郑不甘心居于戴笠之下,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保荐自己去干别的工作。******告诉康泽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了。”后来,郑介民知道蒋不会调动自己的工作,只好与戴笠相处下去。
康泽
“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
(《******评传》,第565页)
〔康泽〕(1904—1972)字代宾,号北民。四川省安岳县人。曾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南京《中国日报》社长、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并组织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要职。襄樊战役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63年获人民政府****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
〔解读〕
康泽,曾是******身边红极一时的人物。他跻身“复兴社”四大台柱之列,出掌自成体系的特务武装——别动队,盘踞“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长要职,头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中将厅长的桂冠。他惟蒋命是从,深得******的信任与重用,成为******最忠实的信徒之一。
1948年1月,康泽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驻湖北襄阳。7月1日,襄阳之战开始,******吹嘘说,“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戍守”,由于“‘共匪’畏之为虎”,“相信此次战役定卜全胜”。可是言犹在耳,短短16天以后,康泽便战败被俘。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7月22日,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却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在******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1949年,******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很沉痛地说,在“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两人,这两人中便有康泽。”并将康泽列入“忠烈祠”。
以后,******在得知康泽未能殉难时,仍旧不肯死心,而要强调康泽“抗节不屈”的事迹。1964年7月,******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甚至有挽联赞曰:
襄阳当南北要冲,弹进而莫之济;粮竭而莫之援。十七日阁部扬州,赢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照党国史乘,劳改而终不变;酷刑而终不屈。二十五载文山土室,丹心正气,独有千秋。
事实果真如此吗?就在******大发感慨的前夕,即1963年4月9日,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改造的康泽,由于揭露******筹建法西斯组织的真相和搞“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罪行,确有改恶从善的具体表现,获得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的****。在改造期间,康泽一开始身体多病,又思想顽固,政府让他住院治疗,精心护理,每天给予牛奶鸡蛋补养身体,使他深受感动。继又通过学习和全国性的参观,思想认识不断提高。1965年秋,黄河三门峡工程竣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康泽在桥上深有感触地说:“过去黄河水治不了;长江桥修不好。如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黄河开始得到治理;长江架起了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大桥,使天堑变通途。这座桥的质量,和我在美欧所见过的大桥相比,毫不逊色,令人信服。”也在这10余年的改造中,康泽对******有了本质上的认识:“我跟******做事二十年,为他效忠了二十年……他对别动队、三青团的讲话,真是甜言蜜语,好话说尽,使人们死心塌地地为他去卖命。但转瞬之间,他所表现的全不是他以前说的那样……他只有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掌握政权,巩固他的统治和政权的世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