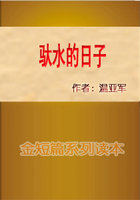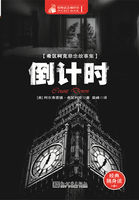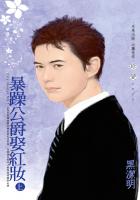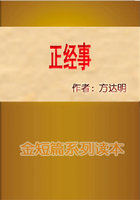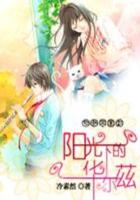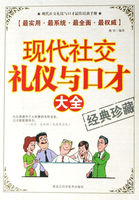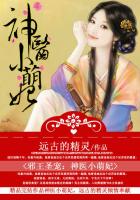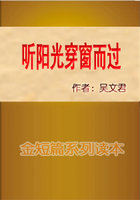总部设在西雅图的康达生物制药公司,很快给丹桂发来了面试邀请。丹桂利用学校的春假飞抵西雅图,走完了一整天的密集面试程序后,直觉告诉她,她该作好在秋天里搬到西雅图并开始新生活的准备了。
面试结束后的周四傍晚,丹桂住到了她当年在中山医的学姐晓红家里。一直单身的晓红插过队,披着一肩跟自己年龄不很相称蓬松长发,正在华州大学心理系拼终身教授资格。多年未见的她们,那天一直聊到深夜。当话题转到晓红如今的学业领域时,丹桂讲起了自己修读心理学的念想,那念想的来历,那来历间的种种困惑。晓红安静地听完,自语般地轻声说,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志,你该见见戴比。
晓红应该是凌晨时分给系里刚从杜克大学挖来的新生代女教授戴比·斯特林博士发去电邮的。晓红告诉丹桂,戴比的研究方向是创伤心理学。作为学界新秀,戴比当时从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申请到一笔相当可观的四年期研究基金。作为对新进教授的扶持,华大同时有相应资金跟进。丹桂到西雅图时,戴比正在积极招兵买马,着手创立一个自己的学术研究团队。
丹桂不曾听说过创伤心理学。她按晓红的指点,在网上点开戴比·斯特林的网页读进去,随着一个个链接走进这个心理学科新兴支流的深处,立刻被吸引住了。有一刻,她蒙住了双眼,感觉那个关于父亲的梦就要回来了。网页上一条条的链接,都在指向那个黑巷路口沉重的铁盖。
戴比在周五一早,就给晓红写来了简短回信,说丹桂可以在当天下午两点到办公室来谈谈,并让丹桂直接跟她联系。丹桂立即给戴比写了一封电邮,小心地描写出自己不长不短的来路--中国;广西;武宣;万里求学的旅程。她在信中告诉戴比,她在中国****的氛围中出生成长,其间的种种困惑,让她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丹桂将浓厚这个词删去又敲出,再删去,最后还是决定必须由它来修饰她的志向。但她没有告诉戴比,她度过童年的武宣县对这浓厚的生成贡献过什么。她更没有告诉戴比,父亲是在她三岁那年吞下过量安眠药,沉入穿流县城而过的黔江自杀身亡--其时,距武宣****中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吃人事件已有六年光景。
丹桂不知道父亲经历过什么--按母亲的说法,作为****后第一批分配来广西的大学生,时任武宣县革委文教办年轻干事的父亲,除了童年被仓皇出逃台湾的父母留在福州深巷里,与孤寡的祖母靠糊纸盒度日时经历过的那些无依日月,再不曾有过更大创痛。母亲每每说到这里,总要叹息,然后说,你要做一个开朗的人,不能像你的爸爸那样钻牛角尖,最后连命都搭上了。丹桂越往大长,越难以接受母亲如此潦草的说法。如果不是难愈的重创,一个男人,在他未及三十的黄金年华里,怎么可能抛下三岁幼女和年轻妻子,自没于时光的苦海深处?父亲创口的瘀血汇入黔江,百回千转之后,在她十二岁那年灌入她的心底。她从此也成了一个有着创伤的人。深重的创伤。或许,接近戴比·斯特林,她就有了走出那个黑巷的可能?
晓红在领丹桂去往戴比办公室的路上告诉她说,我比你年长好多,看过那么多的事情,晓得人最要紧的是看顾自己的心志。美国人讲那是内心呼唤。当它一旦发声,人最好不要错过它,不然会成为终生遗憾。人生很短暂,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应该尽量不要让它变成遗憾。至少要试一试,对吧?见丹桂不响,晓红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臂,说,不要紧张。心理学专业的资助可不好拿,再说你还不是本专业的,就当是去碰碰运气。丹桂点头。晓红又说,戴比的学术能力和公关能力都非常强,有那种天生的明星气质。我真是很难赶上的。她如今刚到华大,一切正在起步,手里有研究经费,又很需要学生。而且她的专业方向真的很有意思,你如果能进去,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见丹桂听得表情凝重起来,晓红笑了笑,又说,见面谈话时,自然就好了。她们见过多少世面的呀,很少会误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