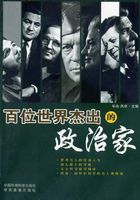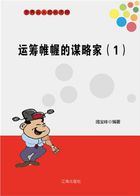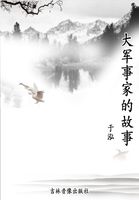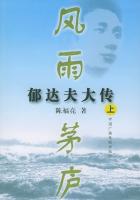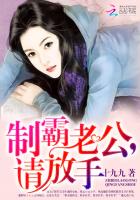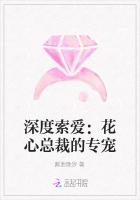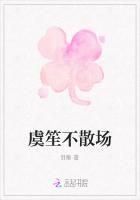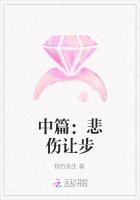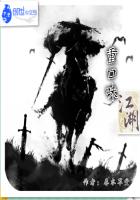和珅将侄女嫁给皇孙后,其在皇帝面前的地位又高了一等,和珅家族与皇室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但有一个问题,是和珅的儿子为乾隆帝之婿,而和珅侄女为乾隆帝孙媳。这样一来,和珅的辈份低了一级。而和珅为何毫无顾忌呢?
这有两个原因:
(一)因为汉族人在缔结姻亲时,一般习惯上讲究伦理辈份,所谓外亲、妻亲的尊卑,也常常注意辈份。但清朝统治者是满族人,在满洲旧俗中根本就没有这个观念,更没有严格要求。因此他们在缔结婚姻时只注意本人,而忽视其他,彼此没什么辈份要求,“父妻子婚”是清代满族社会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原始族外婚的形式,“父死子妻其母”的现象是常有的事。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曾娶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之女为妻;而李满又娶董山之兄权豆的遗孀为妻;摄政王多尔衮与其侄豪裕同娶桑阿尔寨的两个女儿为妻;清太宗皇太极的孝端皇后与孝庄皇后是亲姑侄关系,同属蒙古族博尔吉济特氏,在清世祖顺治初年同时被尊为皇太后;清世祖的废后与孝惠皇后也是亲姑侄关系,等等。
(二)和珅是为乾隆亲家,但其权势还没有达到一手遮天的程度,其地位也不甚稳固,与皇室结成更进一步的婚姻关系,可以加强自己权势和地位。
以上两点是和珅不计较辈份的原因。从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出,和珅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9.稳定局势,操纵军权
白莲教起义如火如荼,在湖北、四川、陕西一带迅速蔓延。和珅看到了战争给他带来的机遇,他紧紧地抓住这次机会,想趁时局不稳,在混战和乱世中壮大自己的权势,扩大自己的家业,大发战争国难财。
和珅身为军机大臣、内阁首辅,是乾隆信任不贰、依为心腹的宠臣。面对众多的军国大事,乾隆皇帝已无力亲自处理,又不想将权力移交给嗣皇帝,只好任凭和珅摆布。和珅每天替皇上起草谕旨敕书,发布廷寄,阅看各地的奏折。久而久之,各级官吏都视和珅为“二皇帝”,对于和珅的独断专行也习以为常了。
和珅凭借手中的军事大权,欺上瞒下,竭力捞取钱财,任用亲信。他不断向太上皇乾隆推荐自己的亲信,以出任各地镇压起义军的将领。
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军费开支,就连历年以来的积蓄也为它所用。有时,各地粮饷征调困难,直接从皇帝的费用中借用,由内务府进行调拔。因此,军中的官职皆成了肥缺。
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和珅的亲信如蝇逐臭般纷纷来到前线,奔赴军营。他们利用多报兵额、冒领军饷、虚报战功邀赏、克扣兵饷等方式,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甚至在军营中招募歌妓,自养戏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根本不把军务放在眼里,而是玩兵养寇,冒功邀赏、营私肥己。那些平日穷乏的官员如谙达、侍卫、章京等担任清苦差事的人,一旦得到和珅的任用,前往军营,不出数月,顿时丰饶富裕。他们借口祭祖拜宗,托辞请假回京,将在军营所蓄资产,运回家乡购买土地,营造家园房屋,甚至开当铺,出租房屋土地,收取租费。
这些自军营回京的将领,自然少不了要孝敬一番他们的主子和珅。
和珅除了向他们索取财物,更重要的是垄断当时的军事情报,完全控制了前线的动向,紧紧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以此来操纵朝政,挟制皇帝。
乾隆帝此时已年近九十岁,白莲教大起义使他时刻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他每日忧心忡忡,心急浮躁,神经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再经不住更大的刺激。和珅对此十分清楚,他把前线连打败仗的消息封锁起来,一概不提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免得太上皇经受不起,出现三长两短,失去后台和靠山。
有时乾隆问起前线的战况,和珅总是报喜不报忧。把军事战报上的战绩报告给太上皇。而这位所向披靡的十全老人,还陶醉在过去的辉煌战绩的喜悦中,对和珅的奏报未作过多的考虑,都信以为真。
和珅任用的领兵大臣,大多都是他的部下、心腹或亲属,按照清朝的规定,这些领兵大臣都兼任地方总督、巡抚等职,控制着当地的政权、财权和军权,如毕沅、秦承恩、和琳、勒保等人。这些人只会奉承拍马,对军事一无所知,而且胆小如鼠,一旦听到起义军到来的消息,吓得赶紧龟缩在城里。宣布全城戒严,不敢与之交战。景安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嘉庆二年,农民军在云南、贵州、四川和湖北一带受挫后,就迅速移师河南。而河南巡抚是景安。
景安是和珅的族孙,满洲镶红旗人,出身官学生,曾先后任内阁中书、户部郎中、山西河东道、甘肃、河南按察使以及布政使和工部侍郎等职。乾隆六十年,也就是1795年,在和珅的引援下,当了河南的巡抚。他对于行军施政,一点也不懂,当白莲教往河南移师时,他未作一点准备,只是为了应付君令,做做样子,率领四千人驻扎在南阳,敷衍门面,对于农民军他不闻不问,只是饮酒作乐,因此南阳这个地方妓女倒生意兴隆起来。
景安酷好女色,他的部下也毫无顾忌,没有钱的兵丁,去不起妓院,就到民间肆行****良家妇女,无恶不作。
你别看景安毫无施政治军之本领,但对和珅孝敬得非常好。所以农军越剿越多,以至于官兵忙得不可开交。而这个景安在农民军来时,他就躲得远远的,到农民军离开之后,他又率兵出现了。
不成器的景安,在起义军面前束手无策,一味躲闪,有时为避人耳目,也不得不做做样子,虚张声势,等农民军退去后,假意率兵尾追,然后具章奏报皇上,谎称打死农民兵若干,活捉若干,并赶出境内,以此冒功邀赏。
白莲教起义后,他又将军营将领换成自己的亲信,他们惟和珅之令是从,嗣皇帝对他们都无可奈何,军营中的封章奏折,必先送到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和珅验看后才进呈给太上皇,嗣皇帝极少见到,而且这些奏折均不是和珅主动送去,只有当向和珅问询时,和珅才拿出片言只语、无关大局的奏折给嗣看。和珅对前线动态了如指掌,而嘉庆则很少知晓。
久而久之,和珅胆子愈大,头脑发昏,变得利欲熏心,目空一切,在朝文武百官无人敢与他抗衡,朝野上下敢怒不敢言。
为明哲保身,满朝官员有的对和珅阿谀奉承,有的敬而远之,有的隐忍不语。这样和珅更加肆无忌惮,有时甚至欺侮到诸皇子的头上,乾隆帝的儿子们都对和珅望而生畏。
一天,和珅从宫中出来,用手玩弄着着身上佩带的剔牙杖,边走边说:“今天太上皇对诸皇子很不满意,八阿哥应杖30板,十一阿哥应杖40板,十七阿哥应杖50板。”
嘉庆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宣和珅进宫,问道:
“听说太上皇对皇子不满意,要用家法侍候,到底出于什么原因?”
和珅回道:“八阿哥不习国语骑射,十一阿哥附庸风雅,崇尚虚名,十七阿哥胸无大志,得过且过。”
嘉庆闻言,猜知乾隆与和珅一起议论诸皇子,必定也对他有番评论,于是又试探性地问道:“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太上皇怎么现在还生气?”
“奴才与太上皇论及政务,太上皇认为朝中无一人可用,奴才就向太上皇推荐诸阿哥,没想到太上皇听后就生气了。”
“由相公辅佐太上皇,还用诸皇子何为?”
“现在白莲教声势日大,一日不平太上皇一日不安。以前圣祖在世,多次亲驾出征,八旗兵无不以一当十,奋力出击。太上皇年轻时运筹殿廷之上,决胜千里之外,赫赫战功彪炳千秋,现在太上皇年老力衰,已无法亲征,希望诸皇子能有所作为。”
嘉庆帝听到这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好像有人狠狠抽了他一鞭子似的,立刻感到浑身不自在,他深知,乾隆皇帝的这些牢骚根本不是针对阿哥他们说的,而是针对他嘉庆皇帝说的,只是他们皆为皇子,才可以家法处置,而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尽管只是名义问题,国体在此,不能造次。
现在太上皇衰老了,而嗣皇帝嘉庆精力充沛,正是大有作为的时期。但与他的先辈们如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比起来,他的军事才能就逊色多了,既无实际作战的经验,又无军事韬略可言,指挥作战确非特长。就现实情形而言,朝中由太上皇主政,和珅辅佐,嘉庆实际是个多余的人,他完全应该离开皇宫,亲临前线督战,力争早日天下安宁,但缺乏才能的嘉庆帝只是一个平庸的皇帝,仁孝有余,才能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