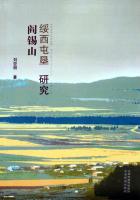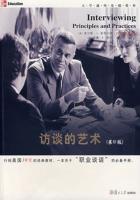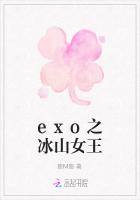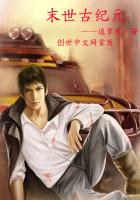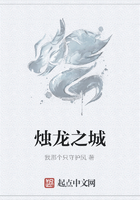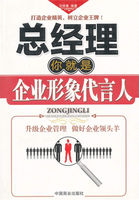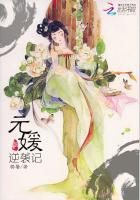从务工时间看,在3年以下的占被调查人数的74.3%;在3~5年的占被调查人数的12.2%;5年以上的占被调查人数的13.5%;3年以下的占了较大的比例。从月工资收入看,低于300元的占被调查人数的13%;301~500元的占被调查人数的50.1%;500元以上的占被调查人数的36.9%;301~500元之间的占了较大的比例。从籍贯看,外省市务工人员大多数来自四川、安徽、福建、甘肃、河南,本省大多来自陕南和陕北。从务工的行业看,大多数集中在建筑和餐饮服务业。
这份调查报告反映的虽然是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的状况,难以完全代表全国的情况。但是,从调查反映的情况来看,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在一些数据上存在差异。因此,可以大致看做是全国进城务工人员状况的一个缩影。从这份调查报告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既有成功经验,也还存在不少问题。
“离土又离乡”,让广大农民离开土地,迁居城镇社会,是城市化的最终目的。不过,几十年的实践也表明,由于人口转移压力过大,制度安排存在缺陷等原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镇社会转移时也出现了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如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们的子女受教育权益受到侵害、男女比例失调、夫妻长期分居、工作条件恶劣、工资水平偏低等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且,绝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是农村的青壮年劳力和素质较高的人口,他们的离开造成了大面积农田弃耕抛荒,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弃农离乡,各地普遍出现了“精兵强将走四方,老弱病残务农忙”的局面,农田里剩下的多为“38(妇女)61(儿童)99(老年)部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使我国城乡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所以,“离土又离乡”的模式虽然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是我国主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但在实践中还是要稳妥推进,以便产生最好的社会效果。
(四)“离乡不离土”
所谓“离乡不离土”,是指农民离开家乡,流动或迁移到其他乡镇企业发达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因为那里的当地人都已进入乡镇企业做工经商,没有人务农了,因而吸引了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农民到那里接替当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这部分人在转移出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同时,他们在新的环境里从事的仍然是农业生产劳动,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说他们就从农村转移出来了,只能算是一种受利益驱动而产生的人口异地迁移行为。笔者以为,这种迁移只能是一种调节中西部农业收入差异的权宜之计,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社会的转移。
上述四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伟大创举,为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相比较而言,“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两种形式更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因而作出的贡献也更大;而“不离土又不离乡”和“离乡不离土”相对来说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贡献要小得多,而且在本质意义上也没有真正解决农民走出乡村社会的问题,因而只能算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适时选择,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和被其他形式所代替。
§§§第三节转型期的社会流动及其正负效应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与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流动,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的总趋势是朝着更加开放、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一个比较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模式正在逐渐形成。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流动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合理性,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因此,本节将在讨论有关社会流动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况对转型期社会流动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展开讨论,以便对目前社会流动的整体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和认识。
一、社会流动的含义与类型
所谓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地位的移动。由于社会关系空间与地理空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一般把人们在地理空间的流动也归于社会流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个人社会地位结构中的任何变动都可视为社会流动。在现代社会里,职业地位在个人地位结构中的意义尤为重要,因此,社会流动研究尤其关注人们职业地位的改变。
从表面上看,社会流动似乎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它不仅对个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结构也会产生影响,从社会流动的速度、比率、方向等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运行状态甚至该社会结构的性质。
根据社会流动的方向,社会学家把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
水平流动指的是人们在同一个社会垂直分化阶层内部的位置转移,大规模的水平流动往往是由科学技术进步引起的。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巨大科技进步都带来了社会职业的结构性变化,使大量的人从一种职业流向另一种职业,由此引发大规模的水平流动。由于水平流动是同一阶层内部的位置转移,所以它不会改变人们在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但是,水平流动对社会结构的意义有时却非常重大,它可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如第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他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仍然是处于社会分层结构的中下层,但整个社会结构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垂直流动是指人们在一个分层结构层面中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垂直流动意味着人们在分层结构中地位的上升或下降,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改变。
因此,无论是个人的社会地位还是社会的结构性质都受垂直流动的影响。垂直流动中,又分为上向流动和下向流动。上向流动是指流入层次高于流出层次;下向流动则指流入层次低于流出层次。
在一个社会中,是否有垂直流动是衡量该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在一个完全没有垂直流动的社会里,社会分层体系是封闭的,各阶层之间完全没有流动的可能。像印度的种姓制,就是一种几乎没有垂直流动的社会封闭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性也很强,除了科举考试等少数途径可以改变人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垂直地位外,几乎没有多少途径可以为人们的垂直流动提供便利,属于半封闭社会分层结构。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提供的垂直流动途径很多,则这个社会就是开放社会。随着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垂直流动的途径越来越多,社会日益从封闭走向开放。
除了根据社会流动的方向对社会流动进行分类,社会学家还根据衡量流动的不同参照基点把社会流动分为一生中的流动和代际流动。前者指个人一生中地位的升降变化,参照基点一般是人们的最初职业;后者是通过同上一代人进行比较而确定的地位变化状态,参照基点是父亲(母亲)在同一年龄时的职业或其他地位。
根据流动原因,代际流动又可分为结构性流动和自由流动。结构性流动指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结构而造成的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自由流动则是由于个人原因所造成的地位变化,它主要由个人因素所决定。一个社会自由流动状况反映了该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开放以及开放程度,人们在选择、获取社会地位方面有没有平等的竞争机会等。
二、转型期社会流动的合理性
如果把社会流动放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就会发现,社会转型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从正面来看,社会转型增强了人的流动意识,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流动空间和机会,使中国社会流动机制更趋合理。
(一)社会流动机制更趋于开放合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从前那些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政策和制度,比如出身、所有制、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等,有的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有的正在逐渐弱化,不再是影响人们地位获得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个人能力和业绩等自获性因素正在逐渐成为影响人们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社会流动机制正逐步趋向于公平合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有关专家关于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的调查资料也可以证实中国社会流动变化的这一趋势。从代际流动率看,1980年以前代际总流动率只有41.4%,其中上升流动率是32.4%,不流动率是58.6%。而1980年以后,代际流动率达到54%,比1980年前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上升流动率40.9%,亦即有四成的子女实现了比父辈上升的社会流动。从代内流动看,1979年以前,从前职到现职的总流动率只有13.3%,1980—1989年为30.3%,1990—2001年为54.2%,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前,有86.7%的社会人员往往是在一个职位上长期工作,很少流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流动有了大幅度增加:1949—1381979年,从前职到现职实现向上升迁的流动率只有7.4%;到了1980—1989年阶段,向上升迁的流动率提高到18.2%;1990—2001年,向上升迁的流动率进一步提高到30.5%。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社会转型以后,中国社会流动速度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二)社会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广阔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国家对个人控制有了很大的放松,国家开始逐步取消对个人的身份限制,个人可以在合理范围内自由流动。
这使得人们的流动空间不再局限于以往狭隘的地域范围内,而是越来越超出个人长期生活的封闭空间,呈现出一种边界越来越向外延伸的趋势。
社会流动空间的扩大首先得归功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出于各种考虑,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实行“以钢为纲”的工业发展战略,其结果是导致了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奇缺。改革开放后,国家迅速调整了产业结构政策,轻工业和商业服务业开始受到重视并快速发展起来。
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动不仅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日常生活用品,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非农就业岗位,从而造成了职业流动空间的大规模扩张。
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的是改革开放后的流动农民工群体。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都守着土地,过着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居的农耕生活,他们几乎很少流动,更谈不上向外求索。可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就几乎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开始走出田间,走向城市,创造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中国2.2亿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村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属于农民工,他们占1999年全国总人口的15.9%,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28.3%,占农村就业人口总数的40.3%。
在2亿左右的农民工中,进城务工经商的占到36%左右,形成一个庞大的农民工流动群体。2001年以来,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又有相当大的增长,……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在这个产业大军队伍中,有一部分是离土不离乡,就地从事非农产业,但流动农民工群体的队伍已经相当庞大了,他们已成为中国当今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中国农民工大规模跨越时空流动的事实足以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给他们提供了日益广阔的社会流动空间。
在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社会流动的空间已不再局限于本土,而是呈现出社会流动国际化的趋势。许多人开始走出国门,到国外工作,到国外做生意,到国外投资……凡此种种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可以说,改革开放短短几十年,已大大扩展了人们的社会流动的空间。
(三)社会流动机会越来越多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政治上高压政策等原因的影响,中国社会几乎是一个没有多少流动机会的社会,所以,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基本上是生活在一种封闭半封闭的环境中,社会流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只是他们梦中想象的天堂,而不可能奢求能够有机会到那些地方工作或生活。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人们之间的关系大多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这种交往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流动机会十分有限,基本上是局限在亲属、族人和同乡人的范围内。换句话说,人们的活动范围大都被限定在自己生活的村落里,而村落之间的相互隔绝又使得一个个村落都处于彼此封闭的状态,这种时空条件决定了人们社会流动是十分有限的,几乎不太可能给人们提供多少流动机会。
社会转型打破了这种相互隔离的封闭生活。因为现代社会要求越来越广大范围的统一市场,要求资金、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各国普遍实行开放的政策,给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流动机会。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身份制度、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等曾经严重束缚人们流动的制度开始逐渐放开,给人们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流动机会。
关于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教育制度改革和升迁的更新方面。1977年,在******同志的倡导和直接领导下,中国恢复了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从此,高考成为一件牵动千家万户的大事。教育制度的这项改革,给那些没有多少上向流动机会的人提供了难得机会,不少人通过高考成了国家干部、高级经理、高级技术人员等,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此相关,国家人事制度改革也把文凭作为干部提拔的重要条件之一,考试逐渐成为公务员选拔的重要途径,甚至干部身份也可以通过考试来获得,过去干部与非干部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被打破,人们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都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