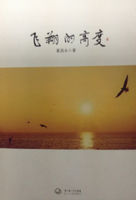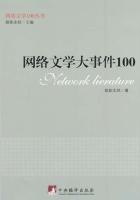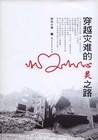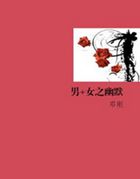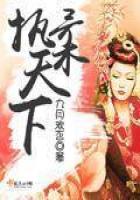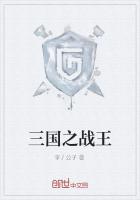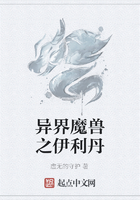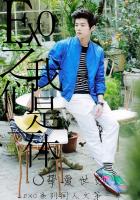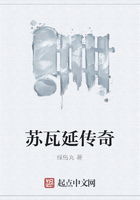但我还是非常赞赏一些朋友大呼猛进,倡言人文精神的激情,沉闷的文学界太需要振聋发聩的新声了。“精神萎缩症”也确实存在。为了疗救这种疾患,我主张宽容精神,而不是“拒绝宽容”,应该让文学的精神空间无比广阔,只要不失其审美特性,应该允许各式各样的眼光、视角、价值立场的存在。文学的人文精神应该比人文学者的人文精神更宽泛、更丰富,艺术家应该比科学家的个性更缤纷。你可以持历史的尺度写得冷静而理智,我也可以抱道德的爱憎投去批判的冷服,你热衷文明的喧嚣,我偏要回归自然,你沉湎于世俗的欢乐,我神往于宗教的高洁,你陷入历史的暮霭,我迎着现实的太阳……这一切不但允许,且越多样越好。问题是,现在有种“终极关怀”崇拜,大有以“终极关怀”与否划线的倾向,这就又有点不宽容了。“终极关怀”一词的出处我还不太清楚,大约源自宗教教义,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去关怀人,也即人文精神的顶峰。要求所有的作品都“终极关怀”是不现实的,也是奢侈的。我是比较相信马斯洛的塔尖式的“需要说”,也相信老祖宗的“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对一个饥饿的农夫来说,你一手拿着“终极关怀”,一手拿着馒头,我看他还是首先要馒头。文学也分层次,也是多功能,如果认为只有表现了塔尖上的需要的文学才是文学,文学岂不显得太清冷了么。
三 文学的时态
看一些讨论文章,我最不解的是,有些人几乎不由分说地对当前文学现状采取了近乎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近年来的文学迷乱、颓败、下滑、后退、庸俗、浅薄,根本没有人文精神。在一些论者笔下,文坛到处是媚俗的嘴脸和堕落的身影,一片荒芜,没有什么作品可看。事情真的糟到这种地步了吗,人文精神真的已经丧失殆尽了吗?
前面说过,我对当前文艺创作的现状也不满意,但我同时认为,不能忽视近年来众多作家为重建精神价值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他们的成就和不足尚未得到认真总结,他们在创作实践中遇到的真正难题,也许对未来文学的生长和发展很有参考价值。如果把人文精神的标准定得过于高玄,能够寓目的作品自然极少甚至没有,如果不那么高不可攀的话,人文精神丰沛不丰沛、深刻不深刻的话题也就变得可以讨论了。
在我看来,近年来的文学中人文精神不但有,还很不少。这就牵涉到怎样理解人文精神了。我想,所谓人文精神,核心应该是人,是对人的关切,尤其是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无告的人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是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的关切,舍此之外到哪里去寻找人文精神呢?倘若文学不能反映人民大众最迫切的愿望,不能对时代最重要的精神问题发言,人文精神就会落空。就拿80、90年代之交的新写实小说而言,它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风景》的作者对河南棚子里“贱民”所倾注的同情和怨责,能说没有人文精神吗?《烦恼人生》写一个普通工人的生存窘境,能说不是人文精神?《单位》、《一地鸡毛》都很琐细、麻烦,其中有没有人文精神?近年的长篇里,《曾国藩》剖析了一个“三立完人”的人格结构和文化人格,《白鹿原》正面观照家族制度和宗法文化,进而探究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命运,它们有无人文精神毋需多言。事实上,近年来的文学外观平静,内在结构则变动剧烈。一部分作家经受了由中心而边缘,由上层而下层,由先生而学生的变化,强化了平民意识,平民视角和体验性,而在都市、乡土、历史、知识分子等题材领域,都有新的萌芽增长,作家们对新的市民意识的描写,就含有新东西。至于文化视角的广泛运用,整合趋势的出现,都还没有得到认真梳理。
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当今的文学好得不得了了,相反,我认为它有明显的薄弱和严重的缺憾,但我主张,人文精神只能在生活实践中建设,文学也应该在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寻求出路和发展,而不可将自身封闭起来。王晓明同志认为,今天的文学要发展,“有一条特别值得重视,那就是回到真正的纯文学传统”。晓明写过不少优秀论文,我很看重他的观点,但他的这一看法,却是模糊的。什么叫“真正的纯文学传统”,怎么个“纯”法呢?若说非功利的艺术精神,我可以同意,无奈这里真正“纯”文学的含义是剔除非文学的因素,为艺术而艺术,等到把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市场、社会问题的因素全剥离光了,还剩下什么呢?曹雪芹“纯”吗?并不。鲁迅“纯”吗?也并不。鲁迅曾针对朱光潜所说“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说道:“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恕我直言,在古今中外第一流伟大作家的行列中,是从来没有“真正纯文学”者的位置的,他们中的佼佼者,顶多只能达到二流水平。
人文精神当然不止表现于创作,它同时表现于作家和文人的人格精神,品性操守,道德理想。我曾表述过大致相同的看法:“负荷沉重的现代作家,既无法摆脱锱铢必较的市场的笼罩,也不能脱离现代人文环境而遗世独立,他们怀着比古人更发达的七情六欲,注定了要在物质与精神的二律背反中忍受更大的煎熬。然而,他们的存在困境又正是他们的优势所在。如果他们坚持不让物欲主宰心灵,并且深刻地写出了人们挣不脱物欲的痛苦和反抗物欲的勇气,他们就展现出古典作家不曾有过的现代魅力,就在通往终极关怀和人的自由的路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论当今小说的精神走向
当今小说创作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对精神价值,对思想含量,对现实的超越性的追求在逐渐增强。原先的薄弱已引起了许多作家的焦灼和深思,走向现实、关怀当代人的灵魂,正在日益成为他们思考的焦点。
若干年来,人们对小说创作的状况不大满意,是有道理的。总体上看,虽然出现了许多惟妙惟肖展示生存状态的作品,但精神的匮乏带有普遍性,虽然文学的格局被称为“多元”,但各式各样新口号的理论含量令人怀疑,整个文学在激荡的市场经济大时代面前显得被动,尚未发出足够有力的声音。我们知道,进入90年代以来,小说审美意识的大趋势是“回归写实”,由于我们文学的即性精神和浪漫精神向来比较薄弱,于是很容易沦入平实化、琐细化、平面化,难以张扬强旺的主体精神。批评界不断强调着写“新状态”和“新体验”,无非是希望作家主体尽可能地亲历亲知时代,尽快摆脱隔膜和陌生的窘境。但这显然算不上是个很高的艺术标尺,现在,随着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矛盾的深入化,越来越多的作家较前更迫切地意识到,同步地跟潮,平行地模写,收敛文化批判的锋芒,驻足于对状态的揭示,已很难回应时代的提问了,文学要成为社会的良知,时代的心音,就要铸造不同于市场价值的人文价值,开辟物化世界之之更广大的精神空间。
我这样说自有根据,并非人为地夸张某些正在生长的因素。现在,我们容易注意到理论界对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很投入,至今也没有停息,却不大注意在创作界对人文精神的思考也一样紧张,它并不限于某一题材某一流派,也不限于某几个所谓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它几乎是全方位的,牵动了众多严肃的作家,只是有的激烈,有的温和。一谈到人文精神问题,有人总喜欢把它看成是某些高智商的小圈子中人才配谈的问题,或者把它缩小到只是个“知识分子的自我灵魂拯救问题”,其实,它是全民族精神生活的大问题。最早提到这个词的人,虽然敏锐,却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个问题(不管用何种具体词语表述)的讨论必然要在90年代的中国来临,它是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价值选择多元化必然要提出的重大时代精神课题,即使争论到本世纪末,也不算长。
它正在由朦胧而明晰,由模糊而自觉,小说创作的精神走向怎能与此无关呢。如果说,80年代文学的精神主干是继承了“五四”反传统的文化批判精神,它政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性强烈,一方面它进行深沉的政治文化反思,为恢复人的价值、尊严、权利而呐喊,另一方面它与解放生产力相适应,反封建、反封闭、反禁锢,充满改革开拓的气息,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文学的生态环境已大大变化了。从世界范围看,现今的时代被称为后冷战时代,两极对位的思维模式渐趋解体,但文明的冲突却加剧了,一度掩盖的文化意识问题更形突出。从国内情况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改变一切,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金钱与良知、灵与肉的冲突日趋明显。为了抗拒物化,人们痛切地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坚守道德理想和寻求精神超越的重要。于是,整个小说创作的精神,就不可能不循此方向摸索、发展。不妨说,这种寻求超越的努力,就是当今小说创作的精神主线。
大家都说当今小说创作的格局是“多元并存”,但真要为它勾画出一幅比较清晰的精神走向图谱却很困难。用作家的年龄断代,用作品的题材分块,均不能说清;用先锋派与传统派来划线,也远远不够;用诸如“寻根”“新写实”这种历时性的潮流来归纳,业已过时。这是因为,现今所谓的“多元”,并不仅仅是题材、形式、方法、流派的多样,根源还在作家们评价现实的眼光,把握生活的方式,以及各自所抱持的价值立场和道德理想,出现了更明显的差异和分化。长期隐匿在“生活化”后面的创作主体,一旦撩开面纱,对比就格外分明。
有人把当今的小说领域划分为三个大圈,一、新理想主义,代表作家有张承志、张炜、粱晓声、韩少功等;二、新保守主义,代表作家有陈忠实、贾平凹,还有原属先锋的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等,以及擅长极度个人化叙述的林白、陈染、海男等;三、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有王蒙、刘心武、王朔、刘震云、池莉、方方等(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这种分法,在具体作家的归属上可能出现错划漏划的“冤案”,但我以为,在大的思路上倒比较切近创作的实际,在几乎无法分解的情况下,能做出如此的梳理,也算是勉为其难,它毕竟接触到了最核心的问题--作家宣扬的人文理想和精神价值的差异。但是。任何的分析和归纳都有局限,何况其对象是很难定量定性的、流动的、交叉的、盘根错节的创作现象,这种划分法的漏洞和破绽也自属难免。比如,新理想主义的“理想”,究竟是新的,还是向传统的回归?新保守主义就没有理想了吗,它的理想与新理想主义的理想之间究竟是姿态的不同还是实质的不同?抑或姿态的不同大于实质的不同?同样,新现实主义与新理想主义、新保守主义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有多大?
如此追问下去,这种分类法恐怕就难以成立了。我想,所谓分类只能是从外在表征和大的取向上的划分。我们既要看到作家们价值立场的分化,又要看到他们所处的时空、所面对的问题的共同性和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恒定性相通性;既要看到一些作家坚执道德理想、坚守精神家园的可贵及其先驱性,又要看到众多严肃的、富于良知的作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追求精神超越的艰苦努力,否则,我们的文学就可能被描述成少数几个作家的孤立的奋斗史,文学的整体面貌和动向反而模糊不清。事实是,现在处在一个多向度的精神探索期,许多问题只是开始,道路正长,即使被视为特立独行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也带有不确定性,只是整体的时代思潮和文学思潮的一种表现。这倒不是要削平差异,而是要突出整体;只有在整体性的把握中,各个方向的出击才会看得更分明些。本文不拟采取“新理想”、“新保守”、“新现实主义”的三分法,而准备用更加综合和整体的方式,评述当今小说的精神走向。
只要把眼光放开,我们就会看到许多耐人寻味的景象;
为什么在王蒙写《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的同时,又有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陆文夫的《人之窝》,邓友梅的《凉山月》等等长篇的出现?这股怀旧风是无端而起,还是别有意味?这些成长于建国初期,崛起并受挫于50年代中期,后被称为归来的一代的作家,他们的怀旧与以往有何不同?为什么他们的回忆眼光都从往日的社会政治层面移向了人性的、灵魂的、民族精神解放的层面?
为什么知青一代作家或其他中青年作家,在离开了知青视角或文化启蒙式的寻根视角之后,不少人转向家族视角?在《白鹿原》出现的前后,就有李锐的《旧址》、老城的《人祖》、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赵本夫的《逝水》、张炜的《家族》、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等等。这是一种凑巧,还是别有深意?其实,张承志的《心灵史》,虽为宗教史的长篇随笔,仍与此风有关。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更广大的文化视角的建立?
为什么在更年轻的一代作家身上,写个体情感史、心灵史的作品忽然多起来,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述平《某》、刁斗《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徐小斌《双鱼星座》、陈染《与往事干杯》、何顿《我们像葵花》等等,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否表明,为了抵御物欲世界的袭扰,人们更愿意走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出现了某种内观化,甚至私语化的倾向?
事实上,精神走向的变化迹象何限于此。有人不拒斥眼前的繁嚣,却有一颗顿悟的道心,遂使繁华如落定的尘埃(史铁生),有人在着手整理文明的碎片,重新观照文化传统的血脉流向,好重新辨识昨天、今天和明天(余秋雨),有人在传统题材中重新开掘,并注入新的理解,力图开发一种适应90年代读者的历史美感(二月河),还有更多的人,重新审视反法西斯战争,不再局囿于具体时空中的阶级对立和军事对抗,而是站在历史的、人类文明的、人性人道的高度来处理战争与人……凡此种种都在说明,文学界不但没有放弃精神的探索,这种探索还很紧张,还很强烈。但为什么读者又不甚满足呢?这是因为,正如人生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绝对的答案,面对我们这个新旧交错,五色杂陈的时代,作家们的精神探索也必然是带着尝试性,且不无惶惑,无法定于一,甚至也无法比读者高明很多。艺术家不同于政治家、社会学家,由于艺术的个别性特征,艺术家的人文态度必然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当我们在对以下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分析时,这种体会或将格外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