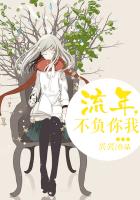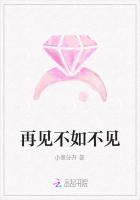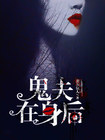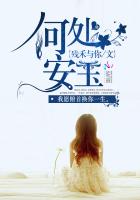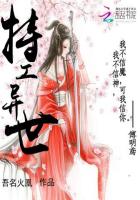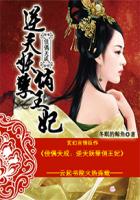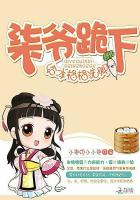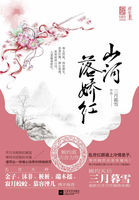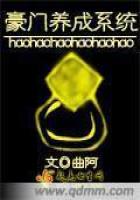刚进屋的那一分钟,就在灯快要灭的那一秒,二丫觉得黑暗中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吃饭,朝门这边望来,灯恢复后,他们仍保持前一秒的表情,他们这一秒的静止就象被像机定格下的画面,都带一种满是疑问的惊讶。
他们的惊讶好像是在问,这一老一小的俩人是谁?以前怎么没见过?这时候来他们家干吗?他们的眼睛如聚光灯一样把不认识的爷孙俩从头到脚扫视一遍。二丫本能地往老爷的身后躲了躲,歪着头也用满是疑问的怯怯眼神看着他们。
昏暗的灯光下,只见那户人家户,老老少少至少有八九个正圈围在炉边吃着饭,好热闹。肚子正饿的二丫巴不得立马坐过去,抬上一碗饭,风卷残云一般吃完。可她站在这,只是一个陌生人。
“我就说,啷是这儿,你龟儿子让我好找半天。”老爷进屋后对着那帮吃饭人中,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说道,啊!老爷认识其中一个,那应该不算陌生人。
那老头一直端着碗,眯着眼等灯恢复后,这才看清楚推开门与他讲话的人,是谁?立马说到:“孟大哥是你啊!快来吃饭。”真不是陌生人,他一眼就认出老爷,可二丫为什么重来没见过他,也许熟悉的人,还是要经常走动,不然再熟悉,也会变陌生人。
“不啦嘛,丫头快叫高老爷,问问高老爷还有米浆粑或荞粑吗?”老爷这时喊二丫喊人。
二丫叫了声高老爷,这才知道老爷是带她来买粑粑。
高老爷家在原来的社会里,就是做粑粑买的人家户,他家在小城做的耙耙手艺算是非常好的人家,他家蒸的米浆耙、甜苦荞粑,还有旱的红粑是小城味道、口感最好的一家,曾跟老爷是邻居。
高老爷赶忙把筷子搭在碗边,顺手把碗筷放在火锅板上,就从坐着的床边,边过来边说:“不敢做,市管会的管得紧,每天喊着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买卖都不行。被他们逮着,轻一点的游街示众,重的可要判刑。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只有偷偷摸摸就做那么一点,我看看还有没有。”
说完直接朝屋角那一堆,满是簸簸、木桶、木盆走去。那堆里物品的旁边,还摆有一个推浆用的丁子磨担的石磨顺墙而放,二丫知道小城做豆腐的也是用这种石磨,有些人家户里也有这种石磨。
“哎!有,有。”只见高老爷说着,就把一簸箕里已成一团的白纱布打开。
“哎哟,怎么才有手心大的一小坨,你看只能给丫头混混嘴,就不收钱了。”看到少,高老爷很难为情。
“哪怎么得行。”老爷说完便从雷锋帽的帽沿缝里抠出一张一角的纸币,硬塞到高老爷的手里,转身牵上二丫没拿粑粑的手,就朝屋外走去。
身后那高老爷急喊:“老东西找你钱,要不了那么多。”
可老爷仍走他的路,没有回答。
走在路上,电也来。
回到家,屋里的浓烟已散尽,只留下淡淡的烟尘味。家里十五瓦的灯泡下,奶奶的火气已消,正提着火钳站在炉边看着进屋的爷孙俩,就说道:“今天这火也怪,老是温不温,火不火的。”
说完走到三抽桌前,右手伸进装盐巴的沙罐里抓出一撮盐,转身丢进了炉心里,一下“兹兹”“呲呲”的声音便在炉心中跳跃,随后激动的一大团桔黄色的火焰带着盐燃烧的味道从炉心窜起,炉里的煤坨表面,如霜降后的早晨,铺上一层白白的霜。
火被奶奶这样一侍候,火势也就大了许多。
奶奶这才把装有苞谷饭的甄子放在有水的沙锅里,端来放在炉上。
正当二丫坐在床边拽瞌睡时,奶奶喊她去上隔壁杨阿姨家,喊妈妈她们吃饭。
不情愿的二丫,连走路也是睡意绵绵。困倦不停地让她打着哈欠;困倦让她的小身板柔软得如一滩软泥,只想找个地方趴倒下去。哪知刚一出门,一阵冷风直冲她灌来,让她倒吸一口气,睡意全被冷风带走。
一下精神抖擞的她就推开了杨阿姨家的门。
杨阿姨家跟二丫家差不多一样宽,他们家没有缝纫机与案板,看着比二丫家宽了许多。
电都来了,妈妈怎么还在煤油灯下,帮杨阿姨拆那件军绿色的衣服?这不是杨阿姨最喜欢的那件吗?怎么就给拆了。唉!大人们的事真麻烦。
二丫推开门,却没进屋,她歪头对着妈妈:“妈,电早来了。”
到是歪靠在床头坐着的杨阿姨“哦”了一声后,顺手把灯绳拉了一下,屋里亮了许多。
二丫前面炉子旁,大姐正领着三弟、仙咡蹲围在一条小凳子旁玩小石子。看着大姐玩的三弟不时用手去拿石子,大姐拿了一颗递给三弟,三弟便朝嘴里塞去,他认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看到的大姐急忙用手去三弟的嘴里抠出石子,抠岀石子就朝自己的身上擦了擦,擦去口水,她又递给三弟并告诫道:“不准吃,再吃就不给你了。”
二丫知道那小石子有七颗,大小有大人的大拇指尖那样大,是上学的女生们在课间玩的游戏,也可以用指头粗的塑料管,一小截一小截剪来用线串成。
这时,杨阿姨看着二丫,对妈妈说:“你家这丫头,来我家一声不响,从门缝里瞄一下就跑,我会吃你,你跑那样,你妈妈叫你喊我,你喊了吗?”
二丫一下子紧张起来,杨阿姨知道她来过,她像做了坏事一样心慌慌的,这一分钟她只想离开这。她不自然地看了看杨阿姨,又看了看杨阿姨的脚,她的脚也穿上了鞋,她急忙对妈妈又说:“妈,奶奶喊你们吃饭了”
妈妈这才回答她:“我们在你杨阿姨家吃过了,你回去告诉你奶奶与老爷。”
杨阿姨的脚还是吸引着二丫的眼睛,她又看了一眼杨阿姨的脚,又看了看杨阿姨,这才转身慢得跟蜗牛一样,一点一点往回走。
身后传来杨阿姨说她的话:“今天,你家这丫头的形为真奇怪。”
“哼!你才奇怪。”听到的二丫嘟噜着。
“你不要管她,我家这小人就是这样。你看这衣服我已拆好,我看了看知道你为什么喜欢穿它的原因,这腰线的确收得好,明天我再用尺子把这比例,再准确地量一下,才知道怎样去做衣服。对了这一件是不是改小给仙咡穿,你舍得吗?”原来这件衣服是让妈妈学技术的,看样子能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给朋友,俩人的关系一定是闺蜜。
“你看着办吧,到时候我叫仙咡来试衣服就是了,………。”杨阿姨的声音就象含着一颗糖样,含混不清。接下来二丫便不清楚她在讲些什?她只觉得仙咡又要有一件衣服,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罩衣,都穿了好长时间,袖肘处还补了一块颜色极不相称的补巴。白天穿了,夜晚洗了晾烤在炉上悬挂的两根平行的竹竿上,第二天又可以接着穿。
妈妈把仙咡的衣服改好后,款式还是列宁装。
没过几天,杨阿姨又拿来一匹布,要妈妈重新做一件,一模一样的款式,这两件衣服被她俩娘母一穿出去,自然跟妈妈做起了,免费的广告,来家里做衣服的人点名要妈妈做。人一多妈妈忙了起来,老爷反而成了妈妈的下手,帮忙熨烫衣物。
奶奶的活也就跟着多了起来。
二丫成了野马到处溜达。
三弟时不时被住在公房中段,一个姓王的中年女人抱去她家。
这王姓的中年女人,妈妈让二丫喊她王伯娘。
王伯娘瘦高个,头上包打的黑色头帕一年四季不离头,脸色偏黄像长期性的营养不良,那满脸的细细皱纹,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七八岁,可她实际年龄也只有四十来岁。
每天一脸的倦容写在脸上,嘴里一个接一个的哈欠,形如一个烟瘾很大的瘾君子,可二丫平时也没看见她在抽烟啊?那一定是什么原因让她睡眠不够?才让她拥有如此疲惫的倦容,还过得踏踏实实,没有半毫的怨言,就连穿也是非常的简单节俭。咖啡色的裤子裤脚口完全塞进黑色雨鞋的筒筒里,土黄色的油毡围腰与袖套,也是常常不离身,看她这装扮,只有小城食品厂杀猪的才这样,可她瘦挑的身材,是不能胜任这工作。
食品厂在小城人眼里是油水多的厂,不然那里工作的人,不会是浑圆的营养过剩,对于黄伯娘这种营养不良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可望可不即的奢想。要想进食品厂,即使是个临时工,没有关系别想进去,物质的困乏,这类单位简直就是嘴边的香肠垂涎欲滴。
食品厂吃香,肉类紧张,王伯娘养猪当然要养猪。
二丫去过她家,她居然养了三头猪在自家屋里。家里猪臊味,煮猪食的味很熏人,让二丫一分钟也不想呆下去,只会蹲在中山路上俯看着她的家。
养猪在家,是小城人的另一道风景。
物质困乏、肉类紧张、住房也有限,在有限的空间里,把猪养在家里,也是为了改善自家的生活水平,但有一半是要交到食品厂,供应给另一部分没有养猪的人。
可王伯娘养的三头大肥猪,却不是自己的。
一样的公房,二丫为什么要蹲着俯看王伯娘家?
原来,公房的房子从这为分水岭,全凹下路边一大截,房梁自然跟着矮下去向东延伸,称为东段。高过的东段房顶的西段端头屋顶边,同样是翘翘的展翅欲飞状,与整幢房子构成比较谐调的美感。
因房凹下去,门头便与中山路水平,进屋自然要下坎,二丫也会坐在坎上,看她在家忙碌的身影,侍候着那三条大肥猪。
早上与傍晚王伯娘把猪赶出家门,让他们来到桥头边堆灰的垃圾地拉屎、撒尿。时间一久,猪自然养成习惯,从不在家拉屎、撒尿。从家里放出,便朝桥头跑去,看到的人,都说王伯娘训斥有方,把这猪头猪脑的笨物养得又肥又壮不说,还比人乖巧听话,习惯也养得好。自然有人来跟她取经,怎样才把猪养好?她只会说,用心了,什么东西都会做好。
取经的人还是不明白,老追着她打破砂锅问到底,怎样做才能算是用心啊!
是啊!怎样做才算是用心?也许分辨在于各人领悟的程度,同样在养猪,竟有那么大的差异,有人成功,就有人会失败。
王伯娘看得出,她是个善良的人,不然来二丫家,看到家里人多,家里的人顾不上年幼的三弟,总让他在这热闹的环境下,孤独无奈地坐在床上自己玩自己的。看得出她喜欢三弟,自然心疼没人顾及的三弟。便跟妈妈打一声招呼,就把三弟带走。她抱走三弟时,自然也会喊上二丫。
王伯娘是二丫家的常客,她不紧跟妈妈摆得拢,也跟奶奶摆得拢,是个很随和的女人,她也是有班上的人。
每天,下班早一点的王伯娘,准会来二丫家摆几分钟的壳子,摆完便把三弟抱走。等到傍晚时,放猪去桥头的王伯娘,会给三弟一截长的小竹竿,让他屁颠屁颠的跟在猪的身后撵赶着。三弟一边打,一边开心地“咯咯咯…哈哈…”地憨笑不停,笑声让人听起来很是舒服养耳,就冲着这笑声,人们都很喜欢他。二丫也喜欢三弟,她喜欢三弟的劲头,就是把三弟逗哭或想着法子去折腾他,好让他哭个不停。老爷说她这是恶想,不得不喊奶奶把他们隔开。
二丫家斜对面是一个山包,山包的顶部是小城的酱菜厂,王伯娘就在那上班,她养的猪也是属于厂里的公共财产,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她说既然是工作,就要尽心尽力把它做好,心里才不会愧疚。在厂里她还有另一分工作,是豆腐车间专门做豆腐的师傅。做豆腐就有豆渣,豆渣用桶担回来专门喂猪,难怪猪会长得膘肥体壮,每次撵去食品厂样样达标,“咯噔”都没打一下就评上一级,所以年年被厂里评为养猪标兵,让她感觉很光荣,所以再辛苦也是值得。
养猪做豆腐在二丫眼里,不是一件轻松的活。
王伯娘每天半夜三更,就开始上班。等她与同事把黄豆在石磨里推成浆,天也就放亮。等浆在大铁锅里放在炉灶上熬制的这段时间,她又叮嘱其他上班的人看好,抽空回家把家里的猪撵出家门,去桥头边拉完屎、撒完尿后,急忙把猪赶回家,吃上第一顿猪食。
猪食是昨晚上就备好,不然哪有时间准备。
看着猪吃得差不多才折回厂里再上班。
上班途中顺便来二丫家,例行公事般的走一趟。二丫起得早的一天,很乐意跟着她去对面的厂子里上班。要去酱菜厂,从二丫家门前过街到对面,绕过街边的一棵大槐树,在槐树后边一点,爬上几级向左倾斜的土坎,就上到与中山路平行的一条小道上,小道成一条平缓的斜坡向下连上中山路,往上一截就酱菜厂的大门斜对着二丫家。紧挨着酱菜厂大门的是一幢茅草顶,白石灰墙的平房,平房修得很特别,中间开的两道大门紧挨在一起,大门两边各开一扇窗户,二丫知道这是全城认为最光荣的人家户。因为这户人家户的施姓男主人,曾参加过红军,人们称他为施红军。虽住在二丫家对面,可他家总是关门闭户,让二丫觉得他家有一种神密感,同样让人可望可不即,越是这样越想让二丫想去他家窜门。
此时,就站在施红军家门前,他家依然紧闭着大门,二丫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这几眼完全流露出二丫对他家的崇拜,也是二丫幻想着能拥有这样的光荣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