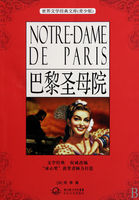妮可被吓着了,一阵哆嗦。但是马上平静下来,悄声说道:BABY,靠在我身上,是电影让你伤心了吧!我什么都没有说,双臂环着她的腰身,我深深地吸进茶花的香味,我的嘴巴贴在软绵绵的胸脯上。这样持续了几分钟,我觉得好受了一些。妮可的镇静令我吃惊!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没有接吻,没有抚摸,我只是头晕,在她身上靠了一会儿。
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夜风把我吹醒。我向妮可道了谢,要付电影票的钱给她。她说,你请客吃饭,我请客看电影,我们打平。妮可说了声"晚安",便独自走了。我怎么站不住了呢?只觉得天旋地转,脚一软,便倒了下来。妮可奔跑过来,一把扶起我,大声地问道:你怎么啦?要不要打911?
不要,不要。妮可,不要离开。
不离开,不离开,我送你回家。我同意了。我没有理由拒绝她。如果她有非分的想法,早该在我抱着的时候做了。我曾经幻想她来抚摸我的头发,俯首亲一下我的前额,……都没有发生。难忘的初夏之夜,至今历历在目。
一盘满月,几乎把幽蓝的天空滤得透明。月光如雪,白茫茫覆盖大地。坐在妮可旁边,我像赴国宴那样兴奋,热血沸腾,又像得伤寒那样虚弱,全身颤抖。我给妮可指方向的时候,上下牙齿打架,话都说不清楚,只能像哑巴似地用手势配合以示左转右转。而妮可却真的以为我病了,好心好意地劝我明天不要上班,她去帮我向老板请假。
一进家门,我马上去厨房,想给妮可煮杯咖啡,她却半推半抱地把我拥进了卧室,我不躺下她不罢休。我正紧张得双腿发软,身体像被掏空了一般,只好顺其自然地倒在床上。
妮可伸过手来搁在我的前额,想测试一下体温,一边说,我给你去弄点水来喝。我一把抓住她的手,不让她离开,两行眼泪不知不觉地滚了下来。我说,妮可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不是一个好男人。
妮可轻轻拍了一下我的手背,温和地说,因为我也有过远离家乡、流落异邦的经历呀!我很理解你的苦恼。
给我说说你的故事。我请求她并把身体往床的中央移,腾出位置让她坐上床沿。床边灯从侧面折射过来,照在她飘逸的头发上,金辉熠熠。妮可明眸坦诚,面颊红润。我细心地打量着她,眼睛停留在那件无袖丝质白衬衫的扣子上不肯移去。扣子很低,连着那道幽暗的****。
那是我十岁的时候,父母到处办SHOW,几乎要荒废了我的学业。他们把我送到了葡萄牙的奶奶家。我在那里住了六年,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期。我的情况比你好,年纪小,容易适应,而且父母一年有几次机会来葡萄牙做生意,带来许多礼物和美国食品。但是,到我能够自己料理生活以后,我选择回来,不愿意留在那里。
哦,我说。当然是美国好。所以,我们不怕吃苦,千方百计想留下来。我怕的是这个社会不接受我们。
她说,我在欧洲有亲人,你们无亲无故的,真不容易!她犹豫了一下,身体微微倾向我,问道:平,要如何做才能帮你申请绿卡呢?麦克和汤姆都想帮助你,但是不知道如何做?是否一定要和公民结婚?
是吗?太感谢他们了。和公民结婚当然也是一个途径。但是,我有太太,这条路走不通。
你爱太太吗?她蹙着细眉,睁大了清亮的蓝眼睛问我。
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怎么能说不爱呢?
如果你们很相爱,平,你应该很幸福,很快乐的。
那得看对幸福的理解了。
我的意思是,浪漫得********的那种?她调皮地笑着说。
老夫老妻了。我笑着说,是相依为命的关系。
那么,那么,……她说了几个"那么",欲言又止。突然,她说,你好好休息吧,我应该走了。
妮可--!
再见!她头也不回。
妮可!妮可!我连喊了几声,她没有回来。我翻身下床,快步冲向走廊。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干什么?这一晚,从双双进饭店到看电影回家,我有多少机会可以挽着她搂着她,抱她吻她,触摸她的身体,我都克制住了。我想做个好男人,想把她留住,我们不过界线,只要她不离开我。现在,她走了,唤也唤不回,我还剩下什么顾忌?我像旋风一样冲上去,一把抱住了她的腰。妮可没有准备,本能地想从我怀里挣脱出来,她要往前冲,我要阻挡她。脚步碎乱,前跌后仰,我们倒在客厅的地毯上。我把她按在地上,硬把舌头伸进她口中,不让她叫喊出声。同时压在她的身上,手对手脚对脚地把她卡住。两人就像一个重叠的" 大"字,僵硬地贴在地上。不一会儿,她放弃了挣扎,闭上眼睛,全身软了下来。我抽出一手解她的扣子,一边说,你不是说我的太太和你没有关系吗?你为什么要走啊?
她回道:你不怕******吗?
你报复,看你报复!好厉害的女人!
我吻她的脖子,把衣服拉开,发疯地吮吸她的****。
妮可呀呀叫起来。
从我认识妮可开始,她身上最吸引我的就是那对饱满的柔软的大**。啊,今天我得到了。我满足极了,好像回到了母亲身边,一切忧虑和恐惧顷刻土崩瓦解!我吮了左边的,再换到右边,圆圆的****像甜蜜的糖果一样,在我的舌根和舌尖之间滚来滚去,越吮越甜。啊,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归宿,我的墓地,如果让我马上死去,我心甘情愿!
在这幸福的时刻,整个世界除了我就是**和****,我把脸埋在两座嫩白的小山丘之间,舔了又舔,亲了又亲,全身心地享受。那是我的爱,我的命,是金山银山,是我生命的起源和终点。
妮可在我的身下扭动身体,大口喘气。她在我的身上摸上摸下,但是,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只想躺在**的山脚下,等着两乳合一,把我埋葬在里面。不在乎有没有明天,不在乎我有老婆,不在乎她在为我加班,争取绿卡。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妮可的**。就这样,我玩得筋疲力尽,趴在她的胸口上睡去了。
我在地毯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妮可竟然睡在我的旁边。我再次剥了她的衣服,贪婪地吮吸起来。翻卷的舌头,抿动的双唇,高耸的**,淡红的****,弹性十足的****。我完全沉浸在现世之外的幻想之中,我成了微不足道的小蚂蚁,连滚带爬地攀登雪白的山峰。
你真性感呀!妮可被我搞醒了。
这时,天刚蒙蒙亮。
我一分钟都不愿意浪费,脸孔和下巴在两乳之间磨来磨去。
她搬弄我的一条手臂,拉直了,移到腹部。我晕呼呼地任她摆布,仿佛经过了毛茸茸的丛林地带,我陷入了滑腻腻的河道池塘。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推着我跃身,离开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山丘,掉头转向她的下面。我觉得唇干舌燥,嘴巴里冒着火焰。泉眼!我找到了泉眼!即刻使出来吃奶的力气,一个劲地伸进去往嘴里吸。啊,甘泉,天水,蜜汁,甜滋滋的迷魂汤!
天啊!天啊!妮可呼叫着,腹部和双腿都跳动起来,胯部左右摇晃。她把我翻到侧面,我爬上去再来。再翻出去,再冲上来。啊,啊!简直是一场征服和被征服的两性战争!浑身是汗,她的和我的,黏乎乎渗透在一起。直到我感到胀裂无比,体内的炸弹马上要把我炸得粉身碎骨,我才想到应该上下对称。
啊,我进去了!进去了,我的家园!我的港湾!我的天堂!
霎时间,妮可没有了!任平没有了!两个灵魂咿呀呀叫着,合为一体,像一缕青烟消失在激情洋溢的空中。
这一夜,是我生命中的里程碑。第二天,我搭妮可的车到电影院,把自己的车开回来,没有再去上班。我病了。这种病不是头痛脑热伤风感冒,不是胃痛拉肚子,外伤内伤都不是,这是一种精神错乱病。怎么能去上班呢?我还陶醉在********的梦境中。闭上眼睛,便看到风尘滚滚中,一个气宇轩昂威风凛凛的骑士!哈哈,我来了!英武剽悍,一往无前,就像西部电影中的强盗,走南闯北,所向披靡,凭着一匹马一把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妮可就是我的马,生殖器就是我的枪,她载着我横冲直撞,把社会秩序搅得稀巴烂。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一个眉清目秀、热情开朗的教师,教育学生遵纪守法,自己却和另一个女人非法私奔。他不就是今天的我吗?英雄啊,拐上女人偷渡香港。父亲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否则女人哪里会跟着他去冒险?失败的偷渡换来13年徒刑,刑期未满,父亲病死在监狱里。
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妮可问了我许多问题。她仿佛感觉到我有些不正常。她问,什么时候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什么时候有了触摸的愿望,什么时候见了心仪的女孩子感到难为情。我不愿意谈过去,我的过去都删掉了,一片空白。我说,都忘记了,陈芝麻烂谷子的烂事,记着干什么?
我为什么不告诉她父亲的故事呢?还有我的大哥,"****"中被揪到台上,被皮鞭抽得皮开肉绽。大字报贴在家门口,说他流氓不要脸,把女孩的肚子搞大了。
我当然记得什么时候对异性产生兴趣。那是刚有记忆的时候,大概三四岁吧!我在托儿所看到老师给一个女婴擦屁股,白白胖胖的臀部,被中间的一条线分成两爿。为什么她的前面光滑滑的,和自己的不一样?我把小手伸过去做好奇的探索,被老师恶狠狠地斥骂一通,还被打了手心。
我的邻座是个圆脸蛋的女孩,大概在幼儿园的时候,扎着两条羊角辫,皮肤特白,白得几乎透明,看得见里面的血管,脸颊上是红的,眼睛旁的血管是蓝的。我常常想轻轻地去摸她一下,但是只能幻想,再也不敢了。
我还记得念小学的时候,在礼堂里开会,大家坐在一条条的长板凳上。我的前排坐着一个女同学,我故意把膝盖往前移,顶着她的屁股。顿时心花怒放,因为她一动不动,好像喜欢我的样子!
我还记得自己遗精,做噩梦,虚汗直流,不敢对人说,偷偷地换裤子。长大以后,对女人的漂亮脸蛋、大**、大臀部,身上的曲线装做没有兴趣,心中却十分向往,越向往越不敢和性感的女人接触,宁可找个性冷淡的佩芬做老婆。
啊,今天我终于无所顾忌啦!压在我身上的石头被妮可一脚踢开。哈哈,原来我是一条铁铮铮的好汉!
脑子里都是男欢女爱浪漫多情的画面,就像放电影一样转个不停。男的是我,女的是妮可。办公室里,妮可扒开双腿,坐在我身上,一边**,一边做实验。洗手间里,妮可坐在马桶上,我跪下去舔她的下身。实验室的地板上,我和妮可像泰德和她的老婆一样,翻来覆去,颠三倒四。饭店里,我抱着妮可吃饭。电影院里,我们脱光了衣服,在灯光下走来走去。
下班回家了,我熟练地用单手开车,另一只手总是被妮可捏着不放。她对着我痴笑,一会儿亲我的手背,一会儿侧身过来抚摸我的大腿。车一进车库,我们已经粘在一起,一边走向室内,一边互相扒衣服。我解她的纽扣,她松我的皮带,一路衣物狼藉。……我必须爬到妮可身上,首先和她的**亲热一番。我轻轻地咬****,像孩子对母亲一样任性。妮可啪啦啪啦打我的屁股,用指甲在我的后背和臀部轻轻地划上划下,我用力冲撞她,她的指甲嵌入我的皮肉,真痛快真痛快!妮可称赞我光滑的皮肤和健美的肌肉。我夸奖妮可丰满的**。我在妮可的**上获得雄性。一旦满足了,便是常胜将军!
胡思乱想,想得精疲力竭,好像这辈子输掉的所有情债,统统都被赢回来了。白天疯狂地**,妮可的影子无处不在。身体像座活火山,岩浆在胸腔里翻腾,轰隆隆喷涌出来。到了晚上,我呼呼大睡。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天三夜。佩芬想送我去医院,我昏昏沉沉,根本醒不过来。
第四天早上,外面下大雨,我一觉醒来,尚未睁开眼睛,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狂风吹着唢呐,雨珠弹着钢琴,树杈枝叶拨动细密透明的雨线,啊,大自然的交响乐,多么奇妙多么动听!我冲到后院,站在雨中,放开歌喉……
现实中的我没有丝毫变化,没有绿卡,没有成果,老婆忙得团团转,银行里没有很多存款。我有足够的理由悲观消沉潦倒自暴自弃。但是,这场病让我脱胎换骨,变得耳聪目明,五脏六腑息息相通。我快乐了!我开朗了!我活出味道来了。
说来也巧,葛莱西雅要带孩子外出度一个长周末,需要三天,佩芬跟着一起去。我兴高采烈地告诉妮可,我们将有72个小时!72个小时,让我们将都化在床上!度日如年啊,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倒计时日。
周末的前一天,妮可说,我很抱歉,只能陪你一天。
一天?只有一天?我沮丧得话也说不出来。
停车场里阴森森的,四周都是墙壁,像个封闭的盒子。我咳嗽了几下,到处都咳了起来。妮可要走了,本来应该和我在一起。我那呆滞的目光,从她的脸上往下垂,痴痴地停留在她的胸前。薄薄的衬衣下,**和****在我的目光下缓缓地胀肿和挺立起来,我扑过去,真想咬上一口。妮可在我的怀里,公共场所,我顾不了这么多了,妮可,你得把时间给我。
亲爱的,我有自己的事情要料理啊。她把我的手轻轻地扳开,给了我一个吻,独自走了。
妮可把车门关上。啪,啪,啪!上下左右都是关门的声音。这声音重重地敲在我的脑门上。居然把我敲醒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醒悟得如此之快,如此透彻。过去的那几天,我在爬山,我已经爬到山顶,领略无限风光,现在应该下坡了。我没有权力强留她,更没有权力问原因。我们萍水相逢,没有爱情投资,也没有做永久伙伴的任何打算,得到了就是幸福的,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是,我不能不猜想。长周末在美国就像假期一样,如同打开鸟笼,大家都想往外飞,妮可不例外。她和谁一起去玩呢?难道真的另外有男伙伴?转而一想,有了,又怎样?你不拥有她,她是自由的,要不要保持关系请便。现代人崇尚松弛的男女关系,****也好,**也好,表面上自私自利,不敢承担责任,实际上要维持关系还真不容易,只要一方不愿意,嘣地一下全完了。
没有妮可,也没有佩芬,这两个夜晚真难熬啊!第一个晚上,我感到委屈,妮可的表现就像骑马冲锋中的急刹车,差点儿搞得我人仰马翻。第二个晚上,我感到羞愧,想到今天自己的荒淫无度,我无地自容。第三天,妮可来了。我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之间怎么会变成这样?妮可听我一五一十地倒出了过去的故事,劝慰我说,你可能有性压抑症,需要治疗。
不知为何,我想到了佩芬。佩芬从来没有性的快乐和高潮。如果我有病,她不比我更惨吗?任平以前来接我总是在车里等着。三天前的一个傍晚,他找上门来。葛莱西雅听到门铃,以为推销商或者邮差送货,开门后,听说是找我的,便问他是我的什么人。
葛莱西雅第一次见到任平,我从来不谈家事。
佩芬的丈夫?她惊讶地喊道,好像被烫着了似的,声音都走调了。佩芬,你的丈夫来了!
也许她怕我被丈夫接走,不再给她带孩子了。脸上是强装的笑容,冷冰冰的眼睛里满是忧虑和疑问。第二天,我去上班,一进门,她就问,家里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将信将疑地看着我,好半天才缓过气来。我说,葛莱西雅你放心,我不会走的。
她跟着说,不会走的,太好了。过一会儿,她才松弛下来,开玩笑说,你的丈夫好英俊,佩芬把他藏得真好呀!
我笑了,说道,哪里是我要藏他?他喜欢安静,不爱与人打交道。
从那以后,任平天天来敲门,敲得我心烦意乱。他要干什么呀?画蛇添足,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