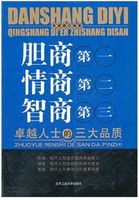【序曲】
你说过会永远保护我
你说过要永远爱我
你说过想永远陪着我
我跟你说:
“一边去!谁稀罕!”
我无数次地从梦中看见你
你笑着问我那天是不是在撒谎
我抓着你的袖子不停地点头
你甩开我的手,说:
“没想到,我也是。”
1。
去年清明节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开车到SX去看壶口瀑布,空闲之余想到夏莉,便打电话喊她出来喝酒。
夏莉是我大学的同学,大学毕业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老家SX,并很快地在一家报社谋了份编辑的职业。尽管薪水不是很多,但日子倒过得清闲得很,她接到我的电话以后,于是欣然赶来赴约。
我和夏莉在我下榻的宾馆的附近见了面。她还是老样子,一头简单利落的短发,一张免受化妆品蹂躏的脸,一件特步的运动服上衣,以及一条洗的有些发白的浅蓝色牛仔裤。
“几年没见,你这男不男女不女的风格还真是一点没变啊。”我张开双臂想要给她一个温暖的怀抱,却被她一巴掌给扇了回来:“你倒是变了,变得比以前更丑了。”
“我擦,夏莉你这样不好吧?再怎么说我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久别重逢你嘴就这么毒,也太不友好了吧?”
“友好?跟你?”她不屑地白了我一眼,“快得了吧,我没骂你已经算是很克制了。”
说得也是。我想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不存在寒暄的,有时甚至连微笑都显得多余。
“走吧,”她指了指旁边的一家小饭馆,“好不容易来SX一会,我得进一下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大餐。当然了,你如果非要埋单我也不拦着。”
你想得到美!于是我俩进了那家饭馆,要了一盘土豆丝、一碟鱼香肉丝、一盆西红柿炖牛肉和一箱啤酒,便就着店外的路灯和来来往往的车辆上演了一出“他乡遇故知”的戏码。
点完菜我们就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不一会儿土豆丝便炒好了,一个穿着红色上衣的女服务员把土豆丝放在了我们面前,说:“请慢用。”
等那个服务员转身离开后我对夏莉朝服务员的背影使了个眼色,说:“哎,这女的不错啊,长得白净衣裳也好看,普通话说得也挺好。你们SX还是有漂亮妹子的嘛!”
“德行!”她说,“她一看就不是我们SX人。现在来我们这儿打工的外地人多着呢!”
她起开一瓶啤酒递给我,又起开一瓶给她自己:“咱是用杯子喝还是直接对瓶吹?算了,杯子太麻烦,就这么喝吧要不。”
“别介!”一股凉意从我背后窜到脖子根儿,四年前毕业聚会那晚夏莉也是这样和我们对瓶吹,结果我们班一个男生被灌到胃出血,硬生生住了两天院才从病床上爬起来离得校。
看来选在清明节叫她出来是不理智的,今晚凶多吉少。
果然不出所料,从七点十分喝到十点半小饭馆关门,我们总共喝了将近有两箱啤酒。不过唯一我没想到的是,这次喝醉的不是我,而是夏莉。
2。
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很多回忆,每段回忆里都会有很多故事,那些故事就像餐桌上摆着的一个个啤酒瓶一样,你可以找个厕所用指头抠抠喉咙把那些水吐出来,却没办法吐出那些被酒精渗透过得血液以及那些血液对你神经的每一次刺激。
我和夏莉边喝酒边聊天,筷子渐渐地都懒得动了。夏莉与其说是陪着我喝酒,倒不如说是自斟自饮。开到第六瓶啤酒的时候,我们还是五五开地喝;但开到第十六瓶的时候,我明显败下阵来;等到开到第二十六瓶的时候,我喝了加起来连十瓶都不到。
我不知道夏莉是因为看见我心情激动还是故意要把自己灌醉,但终于她还是喝醉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喝醉的样子,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于是夏莉开始名正言顺地耍起了酒疯,我则理所当然地成了她耍酒疯唯一的见证者。
她问我:“荆小墨,你这辈子有没有玩儿命爱过一个人。”
我说:“有。我妈。”
“那你有没有被她像捅刀子一样伤过。”
“没有。我妈用的是菜刀,要伤也只能是砍。”
她一拍桌子站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到我背后,拍着我的肩膀放肆地大笑:“哈哈哈哈,你这个龟孙呀,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可以活得这么没心没肺?”然后她把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声音里带着颤抖:“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为什么?”
我没有说话,满脑子只想着一件事情——求求你,别吐我身上。
没多久我就感觉到肩膀上开始潮湿,我知道那是她的眼泪已经浸透了我的衬衫。夏莉趴在我的肩膀上哭泣,声音虽然不大,却让我感到她整个身体都在晃动。良久,她开了口,既像是对我倾诉,又像是喃喃自语。
她说:“我也那么玩儿命地爱过一个人,我也没有被他伤过……可是我为什么觉得,那比被人在心上捅一刀子更疼?”
夏莉开始渐渐地有些站不稳,头开始从我肩膀上往下滑,我赶紧回过头拽住她的胳膊,才幸好没让她坐在地上。我说:“夏莉,你喝醉了。”
她点点头:“我知道。我喝醉了。我总算喝醉了。醉了真好。”
我搀着她从饭馆出来,进了旁边我和朋友住的那家宾馆,开了一间单人间。我给那几个同行的朋友打电话说今晚可能要晚点才能回去,他们说好啊你TM居然敢在我们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和女人开房?我说***滚,然后又说:“等等先别滚,你们谁帮忙出去一下,找找这附近有没有夜市啥的,去买一套便宜的女装回来。”
我带夏莉去洗手间呕吐,一边给她拍后背一边用两根手指头捏着鼻子。不一会儿朋友把衣服买来了,我怕自己酒后乱性,于是给了服务员100块小费麻烦她帮忙给她洗洗澡把衣服换上。就是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让我从十一点多一直忙活到凌晨两点,尽管没有XXOO,却依然让我身心俱疲。
洗过澡换完衣服的夏莉已经有些清醒,她仰面躺在床上,两只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灯棍一动不动。
“荆小墨,我这身衣服你从哪儿淘来的?”
“不知道。我让朋友现买的,应该是从夜市地摊上吧!”
“难怪!这么大的味儿!”她一脸嫌弃,却又有几分高兴,“不过,还挺好看的。”
“德行。呸。”
“荆小墨,你现在困吗?”
“有点儿。妈的你现在怎么这么沉了,刚刚为搀你上个楼我都累了一头汗。这一晚上让你闹得,我现在浑身发虚一点力气也没有,估计躺下就能昏过去。”
“切。别昏了先,再坚持一会儿吧,”她头微微朝我倾斜,眼镜从天花板移到我头上,“我想和你说会儿话。”
写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些困了,于是我把手从键盘拿开,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叼在嘴里,烧红的烟丝随着我的呼吸一闪一闪地发着红光,冒出一缕缕青色的烟悠悠上飘,最终遮住了我的视线。我隔着这烟看窗外的夜空,却看见夏莉正躺在远处暗淡的星空里,她上身穿着一件廉价的粉红色上衣,下面穿着一件有些发白的淡蓝色牛仔裤。她仰面躺在那里,眼镜盯着头顶的那颗星星一动不动,突然她把头扭过来微微朝我倾斜,眼镜从那颗星星转移到我头上。
她说:“别困了,再坚持一会儿吧,我想和你说会儿话。”
3。
我搬了张椅子在她床边坐下,准备等她开口。她把头重新扭过去眼睛继续注视着天花板上的那根灯棍,开始讲述她的故事。
故事里的那个男的名字叫做冉秋——HN人,老家在驻马店附近,比夏莉大三岁,是在夏莉做现在这份工作之前认识的。夏莉说他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准确地说也许应该用“很差”更合适,否则也不会沦落到要用抽签来决定哪个孩子能读书的地步。
冉秋告诉夏莉说,他们家那边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一辈子都得要靠天吃饭。有一年赶上气候大旱,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一年下来的收成别说还要给他和妹妹交学费,就是单单填饱肚子也不一定够。有一晚上冉秋他爸妈一夜没睡觉,第二天把冉秋和他妹妹叫到跟前,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和一支笔。
他爸先是把白纸对折撕开,撕成两张一样大小的纸,然后当着冉秋兄妹的面在其中一张画了个圈儿,另一张啥也没画。他爸把两张纸揉成了两个纸团,放在手掌里笼着跟摇骰子一样地晃了晃,最后伸开手把两个纸团摊在了桌子上。
“爹娘没本事,供不起你兄妹一起读书。今儿个你俩抽签,谁抽到有圈儿的那个谁去上学,剩下的那个跟我在家种地。开始抽之前我想告诉你俩,不管谁去谁留都不要记恨另一个,这是你们自己个儿的命赖不着谁。实在要恨就恨你这个没用的爹,就恨老天爷瞎了眼。”
就在妹妹刚要伸手去抽签的时候,冉秋突然拍着手大喊大跳起来:“哦哦哦!太好喽太好喽!终于可以不上学喽!!!爸你不知道,这学我早就上够了。我脑子比我妹笨学习不好不说,光是学校大磊那帮人就够让我烦的。”
冉秋他娘在边上插嘴:“大磊?哪个大磊?”
“还有哪个!!!”冉秋没好气的说,“就是教我们数学的那个老师家的孩子,他和他爹一样都是属龟孙的,就喜欢串通别的同学欺负我,还老给我起外号……爸,妈,我真是不愿意再去上学去了,我明儿就跟着你们下地去!”
冉秋他爸听着不乐意了,眼睛一瞪冲冉秋大呼小叫起来:“别瞎说!谁教你在背后骂人的?你还小不懂事,你知道地里的活儿有多累吗?老老实实过来和你妹妹抽签儿,没准儿一会儿真抽不到带圈儿的就是你,到时候你再跟我下地。”冉秋说他爸向来是个暴脾气,但那次他爸发火冉秋知道为什么——在农村,在他爸妈的眼里,儿子比他妹妹更重要。
冉秋随他爸也是个烈性子,从桌子上抓起两个纸团直接放嘴里嚼了嚼咽进肚子里,然后大摇大摆地进了屋。
听夏莉讲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在嘴里嘟囔:“恩这人是个爷们儿!换成我的话估计我也会这么干的。”
夏莉懒得拿正眼看我,只是冷冰冰地说:“估计?连你自己也知道你不一定会有那个勇气不是吗。”
我瞬间没了话,没有问号的问句也许也就没有必要再回答了吧。于是我继续听她往下说。
冉秋下了学开始跟着爸妈种地,扶了两天犁第三天早晨赖在床上死活不肯下地,他爸踢了他两脚觉得不顶用就去求村里的建筑队看看能不能带带他,就这么着下了学的第二个星期冉秋扔了书包提着瓦刀进了工地。那一年,他十五岁。
这不足以让我大惊小怪,毕竟我也算是在农村里长大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我妈常说一句话,穷人眼里的人不分男和女、老和幼、俊和愁,只有穷和富,穷了遭啥罪都是活该,富了享啥福都是应当。
只是冉秋这罪遭的时间有点太长了,一遭就是八年。本来也可能会更长,但第八年的时候建筑队里突然有个人从十米高的架子上摔下来摔出了脑浆,冉秋他妈连哭带跪的硬是把他从工地拉了回来。我问夏莉为什么是他妈不是他爸,夏利说,冉秋说他21岁那年,他爸在水库里洗澡淹死了。
一头是自己再也不能去工地挣钱,一头是母亲岁数越来越大妹妹即将考大学,冉秋想了一晚上,他觉得爸爸已经走了自己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既然是男人就该担得起自己肩膀上的担子。他想来想去,觉得在他那个穷地方根本赚不到什么钱,于是决定第二天天一亮就去邻近的SX瞅瞅,听说那里赚钱会相对比较容易。
结果两年后钱没赚到多少,却赚来了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女朋友。
4。
我很想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怎样从相识到相恋的,夏莉却并没有要告诉我的意思,我便也没怎么问。我只记得夏莉跟我说起过一件事情:她和冉秋刚刚谈恋爱那会儿有次夏莉在酒桌上被人灌得烂醉,是冉秋骑着摩托车把她带回了他的住处,晚上他让夏莉睡在自己的床上,自己垫了床毛毯睡在地上,没碰夏莉一根指头。
夏莉说:“我知道我长得不算多么漂亮,但我更愿意相信,一个能守得住自己道德底线的男人一定不会对他深爱的女人不负责任。”
两个人就这样确立了情侣的关系,夏莉跟我说随后的那一段时间算得上是她生命里最美丽的时光。白天两人各忙各的工作各上各的班,一到晚上都下了班两人便开始骑着摩托车在这个城市疯玩儿——滑冰场、烧烤店、KTV、夜店、水上公园、荒郊野岭……这些地方他们都去过,有时候两人玩儿累了就干脆就近找个地方对付一宿。
“我们曾经在公园里的长凳子上睡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起来两个人都被冻感冒了,连续挂了三天吊瓶。”夏莉和我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得意和幸福。
一晃到年底,夏莉决定带冉秋去见她爸爸。夏莉说她知道她爸爸一定不会同意,他一心只想让自己找一个有钱的人家嫁了,好让他出去脸上有光彩。可是夏莉不在乎,夏莉说她就是要让她爸爸看看,她自己的生活她有权利自己进行选择,谁也干涉不了。
果然不出所料,问过冉秋的各方面条件情况以后,夏莉的爸爸把饭桌一掀,指着夏莉吼道:“你要跟了他,就别进这个门。”
夏莉说着说着忽然停了,从床上坐起来,直勾勾地看着我,看的我心里发毛。
“荆小墨,”她说,“给我根烟。”
我从兜里拿出一盒烟,抽出一根给她。夏莉把烟放进嘴里一停没停地吸完,然后从喉咙里咔出一口唾沫啐在地上,她开始像个市井泼妇一般疯狂地骂脏话:“艹他妈的他以为他是谁?他当年把那个婊子娶回家的时候问过我吗?他是个什么爸爸?呸,狗杂碎!狗杂碎而已!!!”
我想平复一下她激动的情绪,也为了让她把她的故事讲完,于是我问她:“然后呢?”
夏莉终于不再咒骂她爸爸了,回过头来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往下说。冉秋在他爸爸面前一句话也没说,把饭桌重新竖了起来,他走到夏莉身边拍了拍她的肩膀,之后开门走了出去。夏莉说她自己一边冲她爸骂着脏话一边哭着追了出去,哪怕是和她爸爸彻底断绝关系追到天涯海角也无所谓。
冉秋知道夏莉一定会追出来,所以就站在楼下等她。夏莉追过来拉着冉秋的胳膊就往车站走,说自己从再也不会回这个家。冉秋没有听夏莉的,他两手按住她的肩膀,跟她说过完年他一定能准备好钱回来娶她。
夏莉一把把他抱住,哭着朝他喊道:“冉秋,你个混蛋,麻痹你个龟孙不会不要我了吧。”
“你自己想想看,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哪一次骗过你?”冉秋把夏莉从怀里松开,“夏莉你听着,我现在对你发誓,我过了年一定要风风光光地把你娶进门,要是我不回来了,你骂我一辈子龟孙都行!”
说到这儿夏莉的声音又停住了,我抬头看她,发现她在流眼泪。
我问她:“他最后还是骗了你,对吗?”
“恩。”
“他没有再回来吗?”
“没有。永远也没有。”
“那你没有去他的家乡去找过他吗?”
“没有。”夏莉想去用手拂拭脸上的泪水,刚刚擦干净却立马有新的从眼里渗出来,“回去的路上他被一辆卡车撞了出去,头磕在了路边石上,当场死了。”
我愣在那里,忽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前一刻我脑海里还在浮现着“薄情寡义”样的词汇,这一刻却突然被告知原来是“生离死别”。
她也没说话,只是不停地用那件粉红色的衣服袖子擦眼泪,泪水渗进袖子的布料里,红的跟血一样。
终于她不在擦泪,又开始跟我说话,只是声音变了太多。她说:“荆小墨,我的故事说完了,你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这要在平时,我一定会说些什么无关痛痒的自以为能安慰人的话,但在这一刻的夏莉面前我却什么也说不出口。我于是从椅子上站起来往门那儿走,夏莉忽然又开了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
我还是没说话,因为我还是没有听出问号。
她说:“这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一个身边的朋友提起过。”
我以为她要我替她保守好秘密,于是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你放心好了,没有人会知道的。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不是,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帮我把它写出来。”
我转过身,看着她两个已经干涸的眼睛:“为什么?”
“不为什么。请你帮我把它写出来。好吗。”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推开门走出了她的房间。因为我知道,没有问号的问句,已经不需要回答。
5。
时间总是会过得很快,尽管我们有时候不愿意承认。自从去年和夏莉一别我再也没了她的消息,推迟了一年直到今天才肯动笔把它写出来,并不是因为需要长时间的酝酿,而是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她一定非要让我来做这个故事的旁白者。论文笔她不比我差,论感情我们也算不上至交,所以我一直想等有个机会见到她时亲口问一问。可惜从那以后她换了电话号码和各种社交账号,我去年那次清明以后又去过一次SX专门想要找她,却也还是无终而返。
今天又是清明,今天上午我从qq好友列表里无意看见她的名字,便随手点了她的空间进去,里面的内容意料之内的几乎没有什么更新。只是我从她留言板里看见一条她自己的留言,既像是一段话又像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你说过会永远保护我
你说过要永远爱我
你说过想永远陪着我
我给了你一拳,说:
“一边去!谁稀罕!”
后来我无数次地梦见你
你问我那天是不是在撒谎
我抓着你的袖子不停地点头
你甩开我的手,说:
“没想到,我也是。”
我最善良的朋友夏莉,如果远在天边的你能够看到这篇文字,希望我没有辜负你当年的信任,也希望此时的你能够早日从那个噩梦中醒来。
2014年4月5号,农历三月初六,清明。
没有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