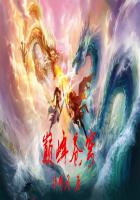据说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条线,这些鲜活流动的线条五彩缤纷,纵横交错,组成了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世界,人类也才得以健康、平衡地发展。
我的生命线是弯曲而又粗细不均的,不再有复原可能的残躯由流动的血供给的心胸支撑着,使得它们的每一个失去功能的细胞都在显示着它的律动。这颗生命的种子由发芽到成熟,就在这个具有完整体系的世界里,守着自己的冰山一角。尽管它时而弯曲如蛇,时而摆动不定,却自始至终地生长着,既有人工雕琢的修饰之美,也有鬼斧般神工般的瑰丽神韵。在同一环境生长起来的生命,林林总总,各有千秋,内涵所在,其每一束光华,都显示出自己不同的魅力。
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每个人都会有错,每个人都会受到惩罚,你的残疾已经表明你的苦该受的都受过了,命中注定不会再有恶疾缠身,你会长命百岁。这似乎给了我某种暗示,按他的说法,我好象可以尽情去挥洒生命的笔墨,在各种各样的纸上去涂画,去着彩,可以一切顺其自然,也可以定一个目标去索求,结果都会是一样美好。
其实我一向不信这些,有人算出今天之前发生的事情,便觉得神乎其神;朋友给我算出来的与其相比有些空洞不实,我还是不信的。明天的事谁知道呢。
生命总有个质量的划分,大患没有,小病不断,纵然长命百岁,受着这样那样的折磨,以我看,倒不如活着的时候健健康康的。一个人过了三十岁,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病痛,二十岁出现健康问题,很多都是与心情有关,失学失业的阴影无法排除,夜不能眠,各种毛病乘虚而入,一会头疼,一会牙周发炎、一会又心律失常,打针吃药折腾了好几年。亲友们背地里无奈地猜测,我可能活不太久了。
婚后生下儿子后,我身上的病痛突然奇迹般地不治而愈。十几年来,我好象重新活了一次,如同初升的太阳,俨然是我生命中的黄金期。“生男去病”,老人留下的祖谚,把我这个什么都不信的人也给蒙了。可能这就是命运吧,失去一些,便会得到另一些。
身体一时好一时不好,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九九年,我前胸长了个很小的瘢痕,有时会痒,其它无碍,我也没当回事。后来在社区组织的一次体检中,我问过医生,得到的回答说这是体质问题,有些人会有,不太好治,手术拿掉它还会长。这样就又拖了几年,瘢痕越长越大,痛痒也频繁发作。于是下狠心去看医生。所以要下狠心,是因为我小时候为了治腿,吃够了打针吃药做手术的苦,再不想走进医院的大门。
只是生老病死没有谁能躲得过,说好不再走进医院的大门,也算不得打自己的脸吧。
原本是想在不冷不热的春天时出去看病,这一年却是春寒无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个冷春。到了六月初,仍不见夏天的踪影。虽终究没那么凉,却又每天一两场雨地下个没完,想等到我期盼的那种好天气总是等不到,于是就摸着规律,趁上午一般不太会变天的时候赶紧出发。
我先去了五院,这是本区最好的一家医院,如果他们看不了,就只得去油田总院,再不行,那就得去省里——这是我和家人最不情愿的,我们在那里没有亲友,如果需要手术的话,将会很麻烦。
果然,五院的女大夫一看就说你还是赶紧去总院吧,我们这治不了,她奇怪地问我为什么才来治,看起来有很长时间了。
离开五院,我们直奔总院。路上塞车,便和司机聊天,我问他,如果我们这样的人单独出门打车,司机们会不会拒载。的哥有五十岁左右的样子,很直爽的性格,他说那怎么会,你们这样已经够苦的了,打车出门一定是遇到了难处,我怎么也得把你送到地方的。这话让我听了很感动,飘飘然想着哪天自己单独出来一次,到处走走,看看是什么样子什么感觉。
想起几个和我一样坐轮椅的朋友,他们出门办事都是一个人出行,不用家人或朋友的陪护。老悠就是,他的旅游梦想是要走遍中国所有发达的都市,都市的路好走,无障碍设施也跟进得很体贴。他说我是女子,出门会比他更方便,因为我的体重轻,成年人都能背动抱动。最初家人一定是极力阻止,顺利出去过一回就好了,还会得到很多方便的支持。他说你成功一次,亲友们就会对我们的能力有所认可,很多事试过了才知自己行不行。
几年前的一次中残联作家会议上我认识了内蒙古女作家敖继红,和我一样,她也使用轮椅。她说她经常外出采访、开会,都是一个人出行,有时还需要坐飞机。惊讶过后便是敬佩和羡慕,一直以来,不用说自己一个人走,就连家里人也很少带我出去。
老悠说的一定没错,他有经验,试过了,他行,为什么我不行?
轮到自己想要付诸实施,却始终不能成行,怕这怕那,下不了决心。
等到从总院出来时,我想,或许担心都是自己吓自己,就拿这次出来看病,我真的可以自己来,一路上全都是无障碍。
看病过程很顺利,清瘦干练的主任医师为我诊看后打印出病历,开了针剂,然后交钱拿药去处置室打针。主任医师告诉我,我的病程长,可能要多打几针,而且第一针会很疼的,你得挺着点儿,下回就会好多了。我想着医师的话,越想越怕,小时候经常打针手术的实在是怕了,不由得问护士,听大夫说这针很疼的是吗?护士一边往针管里打药,一边回答说是的,很疼。我近乎低声下气地求着她说,那你轻点打行吗?谢谢啊,我晕针!她笑了,说行,不过再轻也不会不疼。
只好豁出去了。
原以为一针就是一针,谁知道这一针是要围着包块转圈打,差不多打了十几次。每扎一下,我都会疼出一身汗来。药水浸入包块进行全面封杀,简直就是上刑。
我又想起主任医师的说的,如果我早治就不会这么疼,也不必打很多针了。你这一个月一针,不知要打多少针呢。医师的话说得很实在,就象亲朋邻友在和你交谈,这让我看透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道理——有病还是早治的好,少受苦,少花钱。
在医院大厅里休息了一会,三三两两出出进进的病人不时从我身边经过,他们的脸上因为病痛布满了愁云。
几个目光淡漠的人推着一个从头到脚都盖了白布的人从我面前经过,两个白衣男子在一边引路。我看到了病人的手给夹在床的边框铁柱间,那手雪白,仿佛是浮肿的。这应该是一个死了的人,他的家人眼里没有泪水,甚至也看不出悲伤的影迹。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个离去的人一定是受了太久的苦,以至累其家人精疲力竭,经济与精力让他们变得麻木了吧。
人到世上不是来享受的,我们要受完这样那样的苦,苦其一生,最终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只是,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苦,生命几十年,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安排,完不成任务,谁都无法安安详详地离去。
在我们就要走出医院大门时,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儿从我们面前经过,她由三个家人陪同,从一个走廊里一步一停地走向另一个走廊。女孩走得很艰难,有两个人分别扶着她的胳膊,后面还有一个人两手托稳她的腰。从她的情形看,好象是车祸所致,那三个人看起来该是她的长辈了。她这代人少有兄弟姐妹,长辈们的爱浓而又浓,在这份浓浓的深情里,女孩咬牙坚持,一声不吭,执着地一步步往前走。
康复有望,看过这一幕的人都会相信这个女孩儿最终会站起来的,药方一半是医疗,另一半是亲情。
阴了半日的天,终于在我们回来的路上下起了小雨;雨水掉在路边的湖里,泛起层层水泡。又令我想起前不久发生在宁安沙兰镇的洪灾,有个小学生哭着对记者说,他眼看着他的同学被洪水冲走,而他却无力去救助,心里非常非常难过。他说他很想那些死去的同学们,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在大水淹过的校墙上,有一些手抓的印痕,据说这是那些被水冲倒的孩子在挣扎中想抓住什么东西留下的痕迹。看到这样的描述,你一定会想到那个情景,一种无法比拟的悲伤揪痛而来,而我们不过是与那些孩子没有血缘的人,他们的亲人怎样熬过去,如果有天堂,恐怕只有到了那里见到自己的孩子才能终了。在残酷的灾难面前,生命显出了它的脆弱,不能战胜它,就该学学预防和自救的办法。就象疾病一样,无论你是高官显赫,还是平民百姓,都躲不过最终的结局,预防的好,疾病会来的晚一些。
鲜活的生命总是要延缓它的命脉,丝丝缕缕不停地分裂着它生长的细胞。相比之下,我这点病就不算是病了,甚至可以不去治疗。只是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我们得学会爱惜自己,让我们这个个体的生命线流动出它绚丽的色彩。因为很多时候,很多看起来糟糕的事并不都是很难处理,忍一忍,大事化小;让一让,小事化无。活着,还是简单点儿好。
这样的简单应该算是一种境界,一种需要积累和磨砺的境界,不能承受的放弃或中转,便总是在起点上兜圈子,很可能生命的几十年都一事无成;人们向来敬佩那种能够坚持的人,因为他们的坚持,最终看到了照清了路的曙光;如果我们坚持,也会有一天自然而然地进入这个状态,这时你会发觉痛苦变得渺小了甚至感觉不到了,生活的妙不可言不知不觉中融进了我们的五彩生命线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