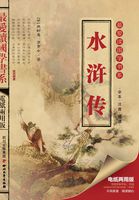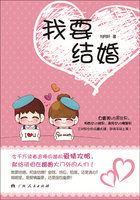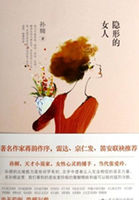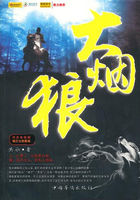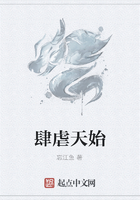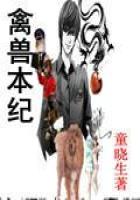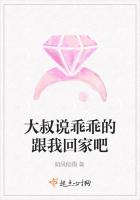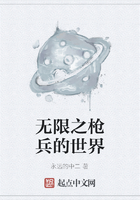当年,双塔大队有个颇有点头脑的小队会计,在被上边逼迫编报了虚假的产量后,看到粮食被征走后空空的生产队和空空的社员家,心里越想越有愧,就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向他反映了生产队干部被逼弄虚作假的真像,也反映了当时小队粮食的实际产量,结果这封信也不知在哪个检查机关被检查出来,结果那个会计的命运还不如彭老总,彭老总讲了真话后是批判、罢官,那个会计讲了真话则直接就被公安局开来的警车带走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铐上了手铐带走,送到监狱一关三年,后来人是稀里糊涂放了,可放出来的时候连路都不能走了。
然而,那么多说了大话吹了牛皮的人面对空前的灾难还都活得有滋有味,活得心安理得,活得无动于衷,在饥谨铺天,在无数饥民处于死亡边缘,叫天不灵,呼地不应的情况下却仍然官运亨通甚至连升三级,多少人民公仆能对着下边嗷嗷待哺的饥饿子民仍然高唱莺歌燕舞,说形势一派大好,更有那人民公仆,为了项上乌纱帽戴得安稳,下去追逼粮食不惜捆打农民,而这位书记却能良心发现,以死告罪于他的臣民,怎么说他也有可取的一面。
对于那场空前的******,后来的舆论宣传把它叫成三年“自然灾害”。
************,这让亲临那场灾难并亲手参与制造那场灾难的老百姓怎么想也想不通,明明是自己不拿当日子过生生糟害的,明明白白是自己折腾坏的,怎么硬把帐往老天爷身上算,把责任往老天爷身上推呢?如果老天会说话,也一定会委屈得叫起来。况且这个“************”,纯粹是无中生有,根本经不起推敲,别的地方是什么情况大家不知道,但辽南地区,1958年是丰收年,地里庄稼长得挺好,可惜到了秋天,壮劳动力全被集中到“大兵团”里去干“大事”了,留守在家的老弱病残又只会磨洋工,好多庄稼因秋天雨水多都烂在地里,丰产年却没有丰收。
1959年,基本上是风调雨顺年,这样的年景庄稼再长不好,实在对不起老天。1960年的夏季雨水是多了点,但对已长成青纱帐的庄稼,雨水多根本就不算什么灾害,老百姓说春旱夏涝,哪年不是这样,但凡拿当日子过,旱点涝点怕什么,庄稼这东西属草性,只要上足肥,像对待婴儿一样地好生莳弄,不是三年大旱,不是大水冲跑就没有不收的。而1961年就更没法说了,1961年生产队的庄稼确实是瞎了个一塌糊涂,可个人家自留地和开荒地所种作物特别是地瓜,却好得不能再好,这怎么能说是自然灾害所致呢?
1960年的秋冬,收完庄稼的大地显得很壮观,到处是一片白茫茫——那是经严霜打过的枯草。这一年,广袤的田野是茅草的天下,大田里什么庄稼都不肯长,就茅草肯长,几场严霜下来,丰收的茅草全部褪去绿色,为大地披上了素装。
往年只要庄稼收完,大部分地块都被犁杖翻耕过来,经过秋翻的土地容易储存雨雪,化乱草为腐殖质,还能防止害虫繁殖,这一点凡是庄稼人都明白。可明白顶什么?当人们肚子没有粮食武装,天天跟自己闹革命时,就得过且过起来,为了减少体能消耗,能不动就不动,所以秋收以后的劳动力大都躲在家里储存体内能量,谁还顾得上去赶牛扶犁搞秋翻?也有特殊的人像五类分子,只有他们不敢躲在家里,然而光有几个五类分子也不行,生产队的牛都倒台了,别说拉犁杖秋翻,连路都走不稳。而阶级斗争再严,还没严到命令五类分子去拉犁杖翻地。当然,命令了也不顶事,一村三两个瘦骨嶙峋的五类分子,还能奈何了到处是一片白草皑皑的原野?
没有人没有畜,只能留下野外一片茫茫大地真干净了。
由于粮食奇缺,一天习惯三顿饭的辽南地区家家户户都变成两顿饭制,建在农村的七中学校因为大部分学生带不起午饭也改变了正常的作息时间,改成上午一口气上五节课,上完后就放学回家,下午没事。
那个冬天,每天早晨我顶着严寒步行在去学校的山路上,走十几里路也难得见个人影,偶尔能看到个把空着肚子在地里吃力地一筢一筢搂茅茅草的老汉,他们所搂的草不是用来烧炕取暖,而是加工粉碎做成代食品给人吃掉。当时国家大力提倡“低标准,瓜菜代”,老师同学还集中起来学习讨论。其实低标准不用提倡,从1959年的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到如今已低到每天三两带皮的毛粮,再低还能低到哪去?瓜菜代就是叫大伙吃瓜吃菜吃代食品,瓜菜也根本不用提倡,老百姓没有粮食果腹,不吃瓜吃菜还能吃什么?只可惜地倒场光天寒地冻,加上两年多的菜地归公,集体又没管理好,瓜菜也没得吃的,人们眼睛能盯到的,就剩下代食品了,那些往日只能当烧柴的苞米棒子芯,大豆秸还有老汉们搂的茅茅草经过加工都可以成为“上好”的代食品,被人吃到肚子里占领粮食的位置,这些代食品如果有灵性,它们一定会无比自豪,无比骄傲,一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它们空前尊贵的地位,就像长虫一下子变成了蛟龙,乌鸦一下子变成了凤凰,这些烧柴得以使它们由往日微不足道的烧火位置,一下子提升到人们体内的“卡路里”。
快要过年了,往年这个时候应该是农村街上最热闹的时候,到处都能看到玩“打牢瓦”、“过山过海”、“打溜溜”(即弹玻璃球)、“跳房子”等五花八门游戏的顽童,一帮一簇玩得热火朝天。
打牢瓦,是一种采用各种形式手法把对方支在远处的石瓦打倒的游戏。可以两个人打,也可以几个人分成两拨搞团体赛。武器是每人找一块可以在地面站立的石片,再在地上按一定距离划两道横线,一条支瓦,一条作为打瓦人的立足线,双方就可以交战了。
交战的程序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先“打板子”,就是站在线上直接把对方支的瓦片打倒,相当于现在体育比赛时的热身,再“跳老一”、“跳老二”,接下来是“老三淋煎饼”,“老四砸鳖盖”,“老五扒山墙”,“老六过河”“前三脚”,“后三脚”……每个名字基本概括了每项动作的内容,每道程序都是在做完规定的动作后再拿起石瓦把对方支在远处地上的石瓦打倒。
一套“打牢瓦”的动作花样百出,一道道程序编排得紧凑、活泼、科学,集瞄准、投掷、跳跃、体操和舞蹈为一体,充分显示了农村孩子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创造力,有些高难动作像“老三淋煎饼”,需要围着石瓦长时间的单腿跳跃,“老四砸鳖盖”“老五扒山墙”得有相当准确的距离计算,“老六过河”时必须腾空跳跃;“前三脚”“后三脚”则是体操和舞蹈的优美结合……一套动作下来,不光锻炼了孩子们的体力和耐力,也考验了每个人的信心和毅力。
童年时代我最喜欢打牢瓦,而且喜欢团体赛,但把式却不怎么样。团体赛视参加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每拨人数可以两个、三个、四个不等,团体赛时如果其中有人在操作过程中失败,成功的可以来搭救。如果一拨人里有多个失败者,搭救往往很困难,待你搭救也失败时,就换另一拨做主家。
因为把式臭,我在打牢瓦时经常因为动作做得不符合标准被罚掉,或者动作合格最后却没有把对方支在地上的“瓦”击倒而宣告失败,这时成功做完整套动作的人就来搭救我。由于经常麻烦别人来搭救,所以一失败,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有点惭愧,但大家救我,毫无怨言,一个没救成,另一个再来,前仆后继,义无返顾,待他(她)们为我把这项程序成功地做完,再集体进行下一项。
在打牢瓦的游戏中,孩子们的集体观念和团结互助的精神特别强。
“过山过海”我也比较喜欢,那是一种群体游戏,一群年龄不等的孩子分成山派和海派两拨,每拨选个较有组织能力的孩子当大王。大王负责给自己臣民一一起名,名字都起得稀奇古怪,山派起的都是山里的东西,像山里红、酸丁子、野葡萄、狗尾巴草……海派当然是海里的特产:胖头鱼、虾爬子、老鳖精、小虾米……
起名都是单线联系,叫什么名字只有大王和本人知道,得了名字的孩子都兴奋得手舞足蹈,活像被授予了元帅或将军的军衔。名字起好,游戏就拉开帷幕,双方面对面坐成两排,双方大王用划拳形式决定谁先出击。如果山大王赢了,山大王就两手捂住海大王一个喽罗的双眼,然后喊自己的喽罗:“酸丁子”来打!叫“酸丁子”的孩子就兴奋得满脸通红,赶紧站起来蹑手蹑脚走到被捂住眼睛的孩子面前,照额头轻轻一敲,然后立即回到自己的山头,山大王松开了手,双方孩子就一齐拍着手“嗷嗷”叫起来,那个热闹劲简直像今天正在比赛的足球场。海派被击打的孩子则揉着被捂花的两眼,在两方狂喊乱叫的干扰中到对方山头艰难地寻找击打过他的人,找对了,就算过了山,山派打人的喽罗就成了海派的俘虏,找错了,自己则成了山派的俘虏。最后的胜负就看两家的俘虏多少来决定。
“过山过海”不仅气氛紧张热烈,让参加游戏的孩子愉悦了身心,而且通过游戏培养了大家的良好习惯。譬如在辨认对手的过程中,双方孩子绝对得纪律严明,严守秘密,谁也不准向对方透露半点蛛丝马迹,被击的人全得靠个人能力从对方的表情神态上去识别,这就需要一方善辨,一方善装,认对认错,就是一次能力的较量。生活单调的农村孩子从这些自编自演的有趣游戏中还真受益匪浅,我至今看起来还算健康的体魄和大脑,很可能就得力于童年时代的那些游戏。
可家家户户的大人们都不喜欢孩子们玩这些游戏,因为玩这些游戏费衣服费鞋袜还耽误干活,粮食不富裕的家庭还怕孩子运动过量吃得多。可那时不管各家的家长怎么禁止,孩子们照玩不误。现在好了,不用谁来禁止,那些让孩子们玩起来上瘾的游戏一齐销声匿迹,坑坑洼洼的街道上连个孩子的影儿也找不见了。
以前这个时候街上不光孩子扎堆,还有成堆的忙完了农活有时间聚在一起说东道西的大人,男人们聚在一起抽烟,说着让妇女脸红心跳的荤话;妇女们手拿针线活,三三两两站在不远处,虽然嘴里不住地笑着骂着,可就是不肯走开。如果街上响起货郞鼓声,她们立即就围上去,你说我笑地互相参考着挑些过年给大人孩子做衣服做鞋袜的针线、纽扣等小玩意儿。
街上也时而响起卖芝麻糖的小锣声,还有用碎铜破铁破麻袋片换糖豆的,引逗得正在弹玻璃球或者打牢瓦的顽童立即停止游戏跑回家去向大人们要钱,要碎铜破铁……
啊!那些可爱的过去,那些温馨的记忆,现在都不复存在了,现在所见,村村是断壁残垣,户户是破屋漏风,共产风后紧接着******,人们以前没有心劲,现在又没有力气来整顿自己的家园了。村村户户,没有鸡鸣,没有狗吠,没有玩耍的小孩,没有农闲时聚在一起胡泡乱侃的男人和喜欢听男人胡泡乱侃的妇女……到处是死一般的沉寂。如果不是这儿那儿的墙壁上遗留下来的那些什么“青年赛武松,老人赛黄忠,少年赛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什么“猛干一冬春,誓叫粮食亩产超万斤”,什么“快马一鞭三千里,一天赛过二十年”等等雄壮的标语口号,谁会想到死气沉沉的这儿那儿,都刚刚进行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的大“变革”呢?
在寒冷阴沉的天气里,我独自一人走在寂寞荒凉的山脊上,头上顶着的是铅灰色的天空,眼睛里看到的是白茫茫的原野,耳朵里听到的是从远处传来的火车尖锐的鸣叫,心里真是凄凉无比……在这个时候,饥肠辘辘的我,总是无端地想起鲁迅先生对故乡的描写:“……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啊!鲁迅先生笔下故乡的萧条是因为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兵匪官绅,我的故乡呢?
1959年的秋天,上高三的四哥背着简单的行李随他们学校学生一起去一个山区公社淘铁沙,淘铁沙任务结束,四哥背着行李步行几十里直接回了家,四哥这次回家的目的就为告诉我别再走读上学了,宁可多花钱也一定想办法住到学校,他说他这次出去,走了几个公社,没见到一块好庄稼,而且看目前的状况,下一年的生产也好不到哪里,以后两年肯定会有一场空前的******,若住在学校,也许还能保证每天有几两粮供应,在家里就不好说了,农村,什么时候都是最苦。
四哥是有远见的,现在一切都成为事实,一切都应验了他的估计。只可惜他的远见没管用,当时的学校可能也和四哥一样有远见,为减轻负担再不肯接受任何一个走读生住校,我只能肚子空空每天徒步十几里往返于家到学校,学校到家的路上,艰难地完成我不甘心放弃的学业。
因为饥荒,才上了一年中学,学生就开始大批大批地辍学,刚上中学时每天和我热热闹闹同路的伙伴一个接一个都不念了,转过年的冬天,寒冷崎岖的山路上孤零零就剩下我一人,每天早上肚子里装了两碗菜糊糊出门,出门不远就消化没了。母亲见我皮包骨头,跟生产队的毛驴一样快要倒台了,就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黄豆炒熟,每天抓一把给我装在兜里叫我中午在学校吃。我装了这把黄豆,往往刚出门就吃开了,一路上,我一点一点地咬着每颗黄豆,以便充分享受一会儿黄豆跟舌头接触时那种美不可言的滋味。即便这样,走不多远一把黄豆也被我品尝完毕。那时我曾发誓:等有一天日子好过了,我什么也不吃,就吃炒黄豆,吃它个够。
有人劝我:小胖,你也不稀念吧,保命要紧,没见你瘦得风一刮就倒了?
让我也辍学,我怎能不念书呢?自打入学起,我就把读书求学看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有那么多的理想,都要靠上学读书实现。小学二年级时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书中丁玲的照片久久凝视,心想,丁玲是女子,我也是女子,丁玲能写书,我为什么就不能呢?等着吧,等我念好了书,我也写书,像丁玲一样当作家。上小学四五年级时,我迷上二哥订的《大众电影》,对里面介绍的白杨、张瑞芳、陶玉玲等人的崇拜,决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那一阵子,我又是那么想当电影演员,我常常一人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脸,觉得除了那颗不雅观的小牙,其他条件都可以。可我又能通过什么渠道当上演员呢?当时的天真想法就是好好读书,只要读好书,读完小学上初中,读完初中上高中,读完高中再上大学,总会有机会的。
上中学后,因为是新建的学校,招生又多,学校一下子分来那么多的年轻男女教师,他们大都二十岁左右,中师刚毕业,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对生活也充满了爱。他们讲起课来热情洋溢,课后和学生一起唱歌跳舞朝气蓬勃,好多时候他们又三三两两在学校周围的田野里悠闲地散步,成为农村田园中一道靓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