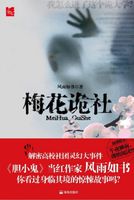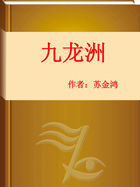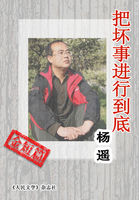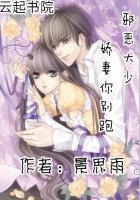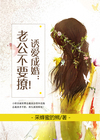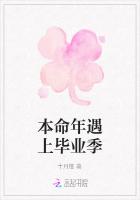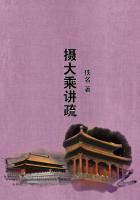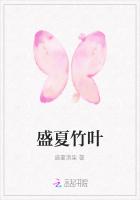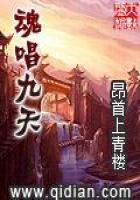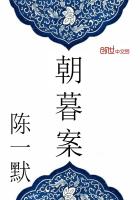这颗彗星的出现,引得地方老百姓惶惶不安,大家纷纷议论,莫不是又要出现灾难了?老天爷呀,你行行好,你就让大家过几天安生日子吧,才太平了几年啊!
从土改到1957年,是老百姓心中的太平年,虽然这期间也发生了好多大事情,像“镇反”、“肃反”、“****”、“五反”、“整风反右”,还有学术界反这个批那个的,但这跟种田吃饭的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普通老百姓的要求不高,生活也简单得很,每天不过是干活吃饭睡觉,任你外边世界闹翻了天,只要跟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不发生冲突,只要让老百姓能安稳地干活,能安稳地一天吃上三顿饭,老百姓就知足了,就认为天下太平了。
在老百姓纷纷猜测和惶恐不安中,公元1958年来到了。
难忘的1958,把全国人带入大灾大难的1958。******,******,英雄的气派英雄的心。战斗指标定出来,鼓起革命干劲。******,******,共产主义大进军,为了亿万人民,为了万代儿孙,决心苦干它三年,幸福就来临。
还在这年四五月份,村政府的有线大喇叭就成天播放起这支雄浑有力的歌曲,一场掀起全国革命热潮的******开始了。各村凡能张贴东西的地方都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凡能写字的墙壁都写满了各种各样气壮山河的口号,什么“为了造福亿万人民,跃进跃进再跃进”;什么“苦干三年,大干一春,猛干三十天”;什么“拿出革命干劲来,超英赶美不用十五年”;什么“要拿出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气势,唐僧取经的毅力,武松打虎的精神……”;什么“只要有决心,粮食亩产超万斤”;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大干苦干加巧干,一天赛过二十年”……
舆论的气势猛烈得让人透不过气,猛烈得像孙悟空在天宫大擂天鼓,快把天鼓擂破了。村村队队,学校机关,各个团体都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誓师游行,打擂比武,一切军事化,战斗化……以后就跃进跃进再跃进,早战午战加夜战,小组战,连队战,兵团大会战……人们在数不清的这“战”那“战”里,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应该说活累不到哪儿去,人们在干活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里,站的时候比干的时候多,大呼隆干活,怠工与时间成正比,但上边偏让人们在山上这么耗着,说白了就是特意要走这个形式耗这个时间,否则怎么能体现全民在******?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平民百姓开始感到新鲜、振奋、激动,它让人们暂时忘掉了因为扫帚星出现带来的不安,也为农村死水般的日子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带来了对未来的畅想和期盼。既然苦干三年幸福就到,谁还不愿意,谁跟幸福有仇?
那个时期,******带来的新鲜花样也真是多,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当时的精神是人人都要敢想敢说敢做,只要发挥人的敢想敢说敢做精神,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没有什么实现不了的。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老百姓从没听过从没见过的稀奇事热闹事都出来了,比如全民大炼钢铁,过去农村很少有人见过高炉炼铁什么样,现在社社队队都大炼钢铁,社社队队都土高炉林立,连学校也不例外;以前人们只见过单斗汽车在街上跑,现在拉矿石大炼钢铁的汽车后边能挂三四个拖斗,硬把汽车变成了“火车”;以前种庄稼一亩地只产几百斤,现在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一亩地要产一万甚至几万斤;过去磨粮食一头驴拉一盘磨,现在改进到一驴拉八盘磨;以前农民种苞米一墩种一株,现在改种双株密植,水库工地以前运土靠肩挑人抬,现在一律车子化……
伴随******的急风暴雨,老百姓的日子也彻底变了样,农村青年男女生活上军事化,行动上战斗化,每天到这儿那儿干活不叫干活,叫大会战。大会战时红旗招展,歌声此起彼伏,叫号比赛,打擂比武不绝于耳,把干活现场弄得像开运动会,热闹非凡。
因为要全民跃进,那些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家庭妇女当然也不能例外,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成天在家里围着锅台转,也要跃进跃进再跃进。为解放妇女劳动力,让小孩从小就接受革命教育,各村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办起了托儿所和幼儿园;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们,也一律吃住在学校,说这样能脱离家庭私有观念影响,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做共产主义新人。
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会议后又多了一项新指示,那就是铲除资产阶级残余,把自留地和私养牲畜取消,在这一新花样的指导下,社员家正长着作物的自留地和正准备种秋菜的蔬菜地全部收交集体,由集体统一经营,猪呀羊的全都赶到生产队,由集体统一喂养。再往后,是自家的财产,特别是铜铁制造的家用器具也都归公,为国家制定的庞大的钢铁数字增加一个分子,美其名曰“工业抗旱”。
然而,诸如此类的敢想敢做和花样翻新,最后其结局都一样,都是——昙花一现。就说全民大炼钢铁吧,那一时期,只见社社队队都在大张旗鼓炼铁,用人工摇动的鼓风机日日夜夜轰轰响,夜间天空红彤彤一片,煞是壮观,然而,大小社队高炉盘了无数,铁也炼得轰轰烈烈,可最终也没见谁炼出铁来,黑糊糊的废渣倒是折腾出不少。那拖了三四个挂斗的汽车,虽然在乡间公路上跑起来像小火车,煞是好看,但干活效率比单车还低,并且事故连连。
再说亩产万斤田吧,******时期国家还没有研制出能提高产量的杂交种子,促使粮食增产的化肥也几乎没有,创高产的唯一办法是像挖战壕一样地深翻地,好像地挖得越深,粮食打得就越多。人们在上边的督促和压力下,虽然费尽力气把地挖成了“战壕”,但到秋天庄稼非但没达到万斤,反倒瞎了个一塌糊涂,原因是土层打乱了,翻到上面的生土不长庄稼,这还不说,下雨天老牛不敢进地,因为牛腿陷进去拔不出来。
至于最新发明一驴拉八盘磨,纯粹是摆样子,尽管靠滚珠轴承作用磨扇是转起来了,可轻飘飘的一点压力也没有,什么活也干不成,白白耗费了时间浪费了材料。双株密植苞米如果有充足的粪肥,倒不失是一项增产的措施,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民们不用上级督促逼迫,种庄稼普遍采取密植,而且年年丰产。可在那时就不行了。那时国家学苏联,强调发展重工业,轻工业上不去,化肥极缺,生产队种大田就靠点农家肥,而且质量极低(稍好一点的农家肥社员都下到自家自留地和蔬菜地里了)。因为肥料不足,双株密植苞米长得面黄肌瘦,秸杆细得像麻杆,连个棒子都结不出。为此农民编了首歌谣:双株密植拉拉稀,不打粮食怪上级,上级说别怪我们,只怪你们粪下得稀。
那个时期,西方国家正跨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正在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利用高新技术成果,改进传统工业的生产技术,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就连几乎被战争摧垮的小日本,也能制定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经济政策,引进最先进的科技,很快跨入世界科技强国的行列。
而我们,却关起门来在家搞这种例似小孩子做游戏的******。
至于村村社社办公共食堂,办托儿所幼儿园,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特别是公共食堂,在农村根本行不通。
先说农民公共食堂,******主席当年不遗余力倡导农村办公共食堂时,老人家想得挺美:打破小锅小灶,改变一家一户的传统生活,集体出工,集体吃饭,吃饭不要钱……
而农村公共食堂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除了吃饭不要钱,老人家的其他目标哪个也没实现。农村的公共食堂可不是城市的机关食堂,一天三顿有饭有菜,农村的食堂吃饭不要钱,可以随便吃,但伙食实在不敢恭维,天天千篇一律是苞米粥和窝窝头,菜根本没有。没有菜,要集体出工集体吃饭的劳动力拿什么下饭,总不能一天三顿空口喝点苞米粥,啃点窝窝头去战天斗地吧?
当然,公共食堂刚刚开办时,还是努力要贯彻上级精神的,为体现“改变一家一户的传统生活,集体出工,集体吃饭”的精神,全村老少曾经到食堂吃过几天饭,那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到了食堂快开饭的时间,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扛着饭桌端着菜盆小孩则提拎着板凳浩浩荡荡向公共食堂进军,阵势热闹而又壮观。到了食堂打了苞米粥和窝窝头,就在屋里或院里找一个地方支上桌凳,就着自家准备的简单菜肴大吃起来……
吃了几天,问题来了,原因是公共食堂屋子和院子地方有限,根本容不下全村人,于是每天还没到开饭时间,一些家的小孩就赶热闹似的提前跑到食堂抢地方,其踊跃劲就像占地方看电影,那时农村很少放电影,偶尔演次电影,家家小孩把占地方看成是头等大事,日头还老高就拿着小板凳跑到放映场……现在,大家又把这股劲头用在吃饭上,都拿着粉笔在地上圈自家的地盘,结果有的圈上了有的没圈上,有的占的地盘好有的占的地盘赖,于是为争抢地盘每天都有孩子大打出手,以至打得头破血流……即便这样,家家户户那些走不动路的老弱病残还是来不了,还得家人把饭端回家……如此几天,不用百姓烦,村干部就先烦了,告诉大家以后饭可以打回家吃,但对外不要声张,谁声张出了乱子谁负责。
所以,公共食堂断断续续办了三年,真正的作用,不过是替千家万户加工苞米粥和窝窝头而已,而且到后来,苞米粥和窝窝头也没得加工的了,在上边不让公共食堂解散的情况下,公共食堂每天只能稀汤寡水勉强凑合办着。
农民吃公共食堂,是对粮食的极大浪费。
农村有句话是庄稼饭,菜一半,强调菜在农民生活里的重要。农民家家都有菜园子,吃菜不用买,凡农村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天天都是半菜半饭,既省了粮食,饭菜又合口味。而吃开公共食堂,就谈不上饭菜对半了,在公共食堂还有粮食的时候,一天三顿,社员的饭食全是苞米粥和窝窝头当家,庄稼菜退到了次要地位。
农民吃公共食堂,是对生活质量的极大破坏。
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即使没有所谓的自然灾害,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低下,以种苞米为主的辽南农村,细粮特别缺,不是过年过节,人们很难见到大米白面。往常农村人改善生活,也就是吃个苞米面做的大馅饺子、苞米面烙的茄合子、苞米面包的菜饼子,细苞米面轧的河漏(一种类似面条的食物)……自从吃开公共食堂,这些农家极低层次的生活改善都成了奢望,粮食一律由村公共食堂统一管理,个人家里什么也不准存,就说我们家吧,从吃开食堂,家中里里外外,连颗耗子吃的粮粒都找不见,哪里还有条件去粗粮细做?而给千家万户做饭的公共食堂,根本不想玩也玩不起这些粗粮细做。
记得1959年的夏天,四哥从学校回来,病了,想吃点茄子合。为了生病的儿子,母亲硬着头皮去生产队菜地央求蔬菜组组长才称了二斤茄子,又自己去生产队的蔬菜地间了点白菜苗,做茄子合的馅总算有了,可烙茄子合的油呢?面呢?想弄到油和面只能去找村里公共食堂,母亲于是颠着小脚去找了队长,队长允许了又去找食堂伙食长,找来找去结果是称点苞米面还可以,但只准许称二斤,而且是粗面,粗面是无法烙茄子合的,至于烙茄子合的油,那是一滴也没有。
没有面没有油,四哥的茄子合只好到梦里吃了。
说公共食堂在农村行不通,还有几个原因,一是打饭问题,辽南农村,一个较小的村落也有五六十户人家,大的都是上百户,而且住得分散,有的户离屯中心有一二里地远。那时农村的穷百姓,很少使用轻便的铝制用具,用的大都是土窑里烧制的泥瓦盆。让这些分散的人家一天三次端着笨重的泥瓦盆到公共食堂打饭吃,看起来是个空前的壮举,实际上是个不小的麻烦,是个相当沉重的负担,特别是下雨天和风雪天,一些没有人手的家,去食堂打饭成了最大的难题,远道人家,饭打回去,连热气都不冒了。
二是辽南农村家家睡火炕,这种火炕即使在大夏天,也得通烟火,否则,用石板和泥土盘的火炕会返潮,睡起来腰腿受病。辽南地区又是个烧柴匮乏地区,家家户户给火炕加温,就靠一天做三顿饭时产生的热量。现在家家户户不做饭了,火炕就得特意烧草加温,结果饭不做了,草得照样烧,事得照样费。所以老百姓说吃公共食堂是一枪两个眼,浪费了粮食也浪费了烧草。
三是吃公共食堂,粮食得全部集中在生产队,这就等于禁止家家户户养鸡鸭猪鹅狗了,而在当时,在国家靠农业养活工业的情况下,农村的农民普遍贫穷,鸡鸭猪鹅是农村人生活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农村人就靠从这些鸡鸭猪鹅身上抠索几个钱来换取灯油和咸盐这些生活必需品。才能把上边发的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火柴票等等换成具体的东西,(即便这样,有好多家还是没有钱,于是这样的家就干脆让孩子光着屁股把布票,棉花票卖了,卖了钱买灯油和咸盐)所以,让农村人离开鸡鸭猪鹅,等于断绝了他们的财源。
和公共食堂同时并举的托儿所、幼儿园,完全是为应付上级而设的摆设。农村妇女基本在家坐着,谁愿意把刚生下的孩子送到什么设施也不具备的“托儿所”?村干部没有办法,就每天带人到一些有幼儿的家庭把那些五六个月大的孩子强行抱到生产队(那抢孩子的架势不像送孩子上托儿所,倒像土匪进屋绑票),找几个老太太看着,又去把一些六七岁的孩子召集到一起,找个年轻妇女领着,这就算办起了托儿所和幼儿园,然而,费了好大劲召集好了的幼儿和儿童,在一起只呆一小会儿就散伙了,孩子们还是各归其家,第二天,村干部再继续召集。
从农村一办开公共食堂,一办开托儿所和幼儿园,就开始有人偷偷说俏皮话风凉话,说办公共食堂是脱裤子放屁,费两道手;是盲人翻跟头,瞎闹。说办托儿所、幼儿园是拐筐掐糜子,找穗(事);说托儿所、幼儿园是冬天窗玻璃上的霜花,日头一出就化了。
相比之下,倒是被集中到小学校吃住的我们兴致蛮高,农村孩子第一次过集体生活,虽然每天吃苞米粥窝窝头就咸萝卜条,而且是定量,吃不饱,但能聚在一起吃住,还是感到新奇感到快活。但这样的集体生活只维持了几个月,放了寒假过了年,第二年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而在**********后被没收的自留地和蔬菜地,在饥荒空前严重,每人每天口粮不足三两的1960年秋天,又重新发放给社员,可是晚了,想让自留地解决社员的燃眉之急,起码得一年之后,可漫长的1961年怎么打发?现在想想,如果1958年**********后没有取消自留地和蔬菜地的指示,1960年和1961年也许饿不死人。
在所有的新生事物中,好像水库工地上的小车化还普及了一阵,用小车推土确实比肩挑人抬要轻松得多。当时有一首歌这样唱道:一辆哎小车吱吱叫,推起来好象水上漂,我的乖乖龙的咚,我的乖乖龙的咚,推起来好象水上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