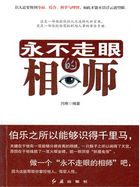廿澜不再理她,将视线扫向墙角桌下等各个角落里,寻思着这地方会不会有蛇和老鼠,下一刻手臂忽然被拉住。
“你干什么?”廿澜不耐。
苦丫头却并不回答她,径自拉着廿澜走向稻草堆,然后把她推dao坐下去,自己则重新走回桌子旁拿了一个包子过来,小心地掰成两半,拜完后微微举起放到眼前研究了半天,似是在看掰的大小是否满意,然后将稍稍大些的那一半递给廿澜。
廿澜本不屑吃这些,在蒙城时她曾被阿轮带着出宫吃过这东西,当时阿轮神神秘秘地,她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却原来比那烤熟的羊腿还如!
此刻,被苦丫头自己的那双亮亮的双眼盯着,廿澜竟不由自主地伸手接了。
苦丫头笑起来,“姐姐,是不是还有一点热?我是一路跑回来的呢!”说完小心翼翼地咬了口自己那一半,脸上现出满意的神情,似乎手中的包子已是天下最美味的东西。
廿澜被苦丫头满意的神情所蛊惑,也咬了一口,不知是她饿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包子似乎真的好吃了许多,于是几口吃完,见苦丫头手上那半个才只下去一个小边,径直站起来走向屋子里那张唯一的破桌子把另外一个包子也吃光了。
廿澜拍拍胸脯,还是有些饿,于是拿起旁边那张形状奇怪的食物研究。
“姐姐,这张饼是我们今天一天的食物,”苦丫头在她身后阻止道。
廿澜见苦丫头望向自己的眼中满是不舍,似乎自己如果吃了这个东西她就会哭出来的一样,终于讪讪地把那张饼放回去,然后走回稻草堆重新坐下,百无聊赖。
晚上,廿澜躺在草上叹气,觉得自己已经无聊得快要发霉了,今天一天她几乎什么也没做,除去吃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没吃饱外,就一直在帮苦丫头拔草。
没错,就是拔草!
苦丫头说,她要再做一张床出来,苦丫头把自己身下的稻草窝称之为床。
翻了个身,廿澜心想确实需要再做一个稻草屋窝,目前这个太小了,俩人睡太挤了些。
廿澜其实从来没有过与人睡在一起的习惯,从前在苍朗山她有自己的巢穴,后来到北翰虽然曾经与辨瓷、訇儿等人同过账,但也不曾挤在一起啊。
苦丫头似乎已经睡去,廿澜又翻了个身,终于忍不住坐了起来,望着远处漆黑的夜。
她到底在做些什么?
如此安静的夜里,实在太容易让人胡思乱想,廿澜忍不住又想起訇儿那张脸,这不是她第一次想起他,尽管分别还不到两天。
“娘,娘亲,”苦丫头在睡梦中呓语,朝着廿澜的方向翻了个身,简直把廿澜抱在怀里。
廿澜皱眉,有些火气地伸出手想要推开,动作缓了一缓,落下去时却轻柔了许多。
苦丫头睁眼,双眼中似有水雾,半晌道“姐姐?”
“你挤到我了,”廿澜道。
“哦,”苦丫头身子往旁边挪了挪。
静谧的黑暗中,两人一时无话,最后,还是苦丫头率先开口。
“姐姐,你有娘亲么?”
廿澜想起母主,按照人类的理念母主便是她的娘亲,于是点了点头,半天见苦丫头没有反应,才想起在这样一抹黑的夜晚她是看不见自己点头的,于是道“有的。”
“真好,”苦丫头的语气里满是羡慕,“姐姐你有娘亲,真好!”
“你……”廿澜想问苦丫头的娘亲去了哪里,话到了嘴边却卡在喉咙里说出不来,忽地有些伤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似乎从昨天出来后情绪就很容易受到触动。
均匀的呼吸声传来,苦丫头再次睡去,只剩廿澜一个人在黑暗中瞪着越发清明的双眼。
“既然睡不着就出去走走吧,”想到这里廿澜轻轻将身子挪开来,缓慢走向门边。
訇儿很烦。
廿澜自从昨晚和自己闹了别扭离开后就再也没回来,不是没想过要出去找,事实上他昨晚一整个晚上都在找她,可是廿澜就像蒸发了一样,任他找遍整个平城却连她身上的一根鸟毛也没有看寻到。
今天一大早天青就匆匆忙忙地赶来,说是昨晚廿澜被劫持了,訇儿本是将信将疑的,毕竟凭廿澜的本事人类要劫持她是不可能的,可是天青又说自己是带廿澜喝了酒的,没想到她酒量竟那么差,才几碗就醉了。
“她应该是没事的吧?”訇儿在心中自我安慰道。
“哎,不就是个丫头么?”尚云一把捞过訇儿肩膀使劲拍了两下,嘻嘻笑道“瞧你烦成那个样,这平城实在边远,等攻下个大点的城池,比你那小丫头漂亮的女人保准要多少有多少!”尚云说完,伸手牵过坐在身侧的女人细白的手,在自己掌心中把玩揉捏。
“爷,是在嫌弃奴家相貌粗陋吗?”那女人不乐意了,嘟着水艳鲜红的嘴唇撒起娇来。
訇儿看向已经有了几分醉意的尚云,眉头皱起,并不说话,只是将面前的酒碗端起来一饮而尽。
坐在訇儿身边的另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见了,赶紧给他酒碗中加满酒,倒完酒眼神妩媚地瞟了他一眼,訇儿却似完全没看到一样,径自在想自己的心事。
“你呀你,真是一点乐趣也无,就拿上次打赌来说,明明给你备好了美女,偏偏不要,”尚云见他如此,无奈道。
两人在蒙城时,曾就王和、张寿背后主人是谁的问题打过一次赌,结果是訇儿赢了,尚云原本提议的赌注是美女,但訇儿死活不要,只要求此次出征请尚云多多关照自己云云,当时大王刚好完颁布诏书,訇儿和尚云都在出征之列,于是尚云也便欢欢喜喜地答应下来。
严格说来,这已不是尚云第一次随军,只是前几次都有兀予启盛在旁罢了。
从青楼出来已过了子时,两人身上都没有穿铠甲,被夜风一吹酒便醒了几分,骑马走在大街上更觉得寒冷,訇儿忽然想起廿澜走的时候只穿走了一身铠甲,于是抬头看看天色,不会是要下雨吧,有鸟类当空飞过,看身形似是不小,速度很快,一眨眼就已经不见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