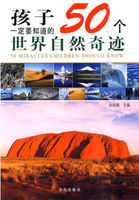此后六年,她的生命是静止的,躺在一口无盖的冰棺里,安静地沉睡着,不受任何外物的打扰。
也许是命不该绝,断肠崖下,一个深达几千尺的雪谷,蓬松无害的雪浪承载万物,仿佛一个温暖的怀抱深深拥住了她,使得她侥幸不死。
没有了无聊的羁绊,她把自己想象成一缕无形无质的清风,在这雪谷广漠而又封闭的天地间,以十六岁的美丽容颜,从容飘荡了六年。
那六年是寂寞的,可也蕴藏着淡淡的欣喜,因为她偶尔,能听到有人在自己身边下棋的声音,黑白棋子落在棋盘上的珠玉之声,成了平静无澜的湖泊中,最后一丝涟漪。
渐渐地,她发现自己甚至有些期待,期待每天的某个时辰,那个对弈的声音准时响起。以至于,期待成了习惯。
有时候,还会听到一个人在自己耳边轻轻说话的声音,每当她想要认真听清的时候,那个声音就突然一句听不清了,仿佛一种无法破解的魔障。
有时候,在她连灵魂都累了的时候,就会有人将她的身体轻轻扶起,把一种不知名的东西喂到她嘴里,而且是嘴对嘴的喂。
那种东西清凉,沿着咽喉缓缓流淌的时候,胸肺间忽然会感到无比的温暖,藉着这种温暖的力量,她又可以多支持一日。
她感觉到那个人柔软的唇磕碰到自己唇上,带丝霸气地叩开她的唇齿,将甘苦的药液送到自己嘴里,可是离开的时候,却没有多加一丝留恋,仿佛每日喂药的这个过程,只是在完成一项乏善可陈的任务。
每当在这个时候,她就会异常惊慌,努力想要醒过来,努力想要唤醒那个沉睡的自己,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属于她的时间停止了,她已经无能为力。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寂寞清冷,却又带着那令人喜欢而又揪心的淡淡痕迹。
前尘往事,似乎就这样远了。就在她以为自己已经忘记,潜意识里甚至打算就这样安宁地过一辈子时,忽然有一天,听到两个人激烈争吵的声音。
其中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格外尖利,而另一个声音却仍是迷糊而虚弱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寂寥无声。
“你为她受的罪已经够多了!六年了,整整六年!她自私地一觉睡了六年,每天靠着还魂汤维持生命,至今还不肯醒来,这一辈子你还指望她会突然醒过来吗?!”
“在她一天比一天恢复的时候,就是你一天比一天衰弱的时候,再这样下去你会油尽灯枯,你会死在她的前头!你死了之后,还妄想有人会为了她去找还魂汤吗?”
“无论你为她付出多少,她会知道吗?她会感激吗?”
“是不是她一辈子不醒来,你就一辈子都不娶亲生子了?就算外边烽火连天,天要塌了地要陷了,你也照例不误每天跑到这个鬼地方来,一守就是大半天!我原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这一根筋的毛病,简直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你要是还打算守着这具冰尸过活的话,以后就都别来见我!我没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儿子!”
就在这时,一个慵懒的声音响了起来,带着些许无奈悲伤地:“别说了,母妃,这是我欠她的。”
而她,也终于听清了这个声音!这个守候了自己六年的人……她攀着冰棺的外沿坐了起来,缓缓地,目光落到不远处:在一间冰石砌成的高大房间里,冰桌,冰椅,冰棺,寥寥几物,这样奇怪的组合。
冰桌一侧,坐着一个白衣华袂、广袖长襟的年轻男子。他的身前搁置着一副棋盘,耳边正在遭受着他母亲暴风雨般的洗礼,可是他的神情却安静落寞,一个人默默地对弈着,左右手各执一子,做着只有棋局高手才可能做到的事。
摊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死局,可是,他却没有丝毫放弃的意思。
“我相信她总有一天会醒过来的,莫非……她竟真的忍心看我白死么?”他淡淡地对僵立在一边的人说道,却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任何一丝异样。
相比六年前,他给人的感觉更加沉静了,更像个饱经磨砺的男人,给人一种安定的感觉。
“是的,我儿心诚,必能感动天地。”做母亲的已经热泪盈眶。
陡然听到自己母妃一改初衷的话,金靖夕举在半空的棋子,倏然滞住。顺着太妃娘娘的目光,他颇为讶异地回头一看,这才发现,那沉睡了足足六年的女子,已经不知何时醒过来了,正扶着冰棺娴静美好地站立着,望着他微微一笑。
六年后醒来,她的容颜还是六年前的那副样子,没有丝毫改变。
一个十六岁的美丽少女。只是跳崖之际那袭染血红衣已经在入棺之际换过了,穿着雪白短襦,浅绿色曳地长裙,就这样,清清溶溶地出现在他面前。
手中的棋子,蓦然惊落棋盘,琳琅作响。
“你醒了?”金靖夕一如既往淡如水的问候语。
“我醒了。”她仍是这样微笑着答,宛如面对相识多年的老朋友。
“那太好了。”他也笑了,焕然美好,宛如仙临。——沧海桑田,原来我只待这一次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