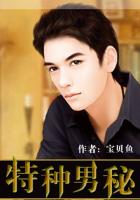这样冷,冷的空气,冷的肺腑,真的快让他窒息。
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奔波,在即将抵达第九座营垒的时候,金靖夕的身体,俨然已经处于崩溃的前缘状态,可他居然没有任何暂缓进程的意思,反而自虐般一刻也不肯停下歇息,一路上就靠着不断吃一种御寒的药丸,暂缓自己的病情。
可是,借助药物压制是多么危险的事,他自己不会不知道。
治标不治本,一旦爆发,那种从内而外爆发的伤害就会成百上千倍地反噬回来。
他每一次面不改色地把那种冰雪色的药丸一把一把地吃下去,旁边的烟水寒看了就毛骨悚然:为什么,这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能把自己不当一回事呢?
“金靖夕!老子对你有意见!!你要是不想活了就赶紧挥剑自刎,随便找棵歪脖子柳树拴了上吊也行!不要老是这副样子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看到你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别人就会觉得我们这些做属下的很无能,——老子身为全民崇拜的对象,绝不可能跟‘无能’两个字挂上钩的!你用前半生颠覆了我的信仰还不够,现在还妄图用这种方式来侮辱我的身家清白吗?!……”
烟水寒发出几百次警告之后,见对方依然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他阴云密布了一整天的脸色,终于再也忍不住电闪雷鸣起来。
他在烈烈风沙里,像个贞洁烈妇一样,对着金靖夕来了一阵暴风骤雨般的口水洗礼。
“你不停下来是吧?那好,我来帮你一把!——与其让王妃将来守寡,还不如现在就给她个痛快呢!”见对方还是没什么反应,烟水寒不由得怒火中烧,一个箭步冲到湘纪的马车前面,迅猛地一剑劈出,一道绚丽的蓝光沿着马车的轮轴处精准无误地划落,一个前轮骨碌碌地滚了下来。
“放肆!”就在车子倾斜欲倒时,金靖夕一声怒叱,已经从马上一跃而起,疾风般掠上车去,在危难关头将王妃从里面抢了出来。
然后,在“劈劈啪啪”的脆响中,那辆百经风沙蹂躏的马车忽然四分五裂了,最后像个炸裂而开的板栗壳一样,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部件,一片一片地如花摊开在沙地里,眼看已经再也无法使用了。
饶是明熙王脾气再好,此情此景下,脸色还是变得很难看。他死死地板着一张脸,扛着万事不知的王妃走向第九座营垒,路过烟水寒的身边时,恨恨地撂下一句话:“……这顿板子,爷先给你扎实记下了!”
不过,他到底决定停下来休息了,总算没有辜负烟水寒一番“美意”。
“只要你还有命活着回城,别说一顿板子,就算你要了我的命,我也无怨无悔!烟水寒堂堂七尺男儿,脑袋掉了不过碗口大个疤,谁怕?”他在后面觑着金靖夕的背影,大笑了好一阵,笑容明亮无比。
***
那种从骨髓里生生溢出的、血液如同被寒冰冻结的痛苦,使得金靖夕疑心自己只要一睡过去,就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每当在这种时候,便是他最脆弱、也是最警觉的时候,外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他十二分的警惕;成王者惯有的戒心作怪,彼时就算自己的亲兵,他也绝不容许他们靠近半分。
他一开始以为自己能挨过这段时间不会病发,所以这一次徐瑞星没带在身边,不然的话,此际那位老人家就该对着他大吼大叫了。
——徐瑞星身为一个品德恶劣、医德却有口皆碑之人,最恨拿命不当命的家伙,而金靖夕的所做所为,又常常挑战他的认知极限。
他倚榻坐在湘纪身边,看着对方如莲花般安静美好的睡颜,平静之余,不由得微微苦笑:也许,过不了多久,真的就会成为一个寡妇呢。
说起来还真是任性啊,不想醒来的时候,便一直这样沉睡着,心安理得。
——假如一个人能够一直这样心安理得地避世下去,亦不乏为一种幸福吧。可惜像这样的念头,于他而言,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他的命运,是即便面对满壁闪烁刀刃,也要勇往直前,因为知道凡是后退一步,踩到的便都是尸骨,就是死路一条。
“会不会……恨我呢?”想到要她嫁给一个将死之人,他忽然没来由地愧疚起来,瘦削纤长的手指抚上她的脸,由于病痛的发作而止不住地颤抖着。
——那就恨吧。他捂着嘴剧烈地咳嗽着,摊开的手心里,是一滩暗红的血。金靖夕看着这团刺目的红色,以一种不可理喻的蔑视态度,蓦然冷笑起来。
命运是个什么东西,可是在这一刻,他却宁可相信所谓的命运,是命运将她送到自己身边,使得他在心力交瘁之际,能像这样安静地看着她,哪怕就这样死去,也已经很是奢侈了。
“公子!”就在这时,忽听霍布田急匆匆地在帐外禀报,“连大小姐她人已经到了。”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惊喜。
随着他的话音落地,一个软调清腔响起:“连殇不请自入了。”
当那个女子毫不避嫌地拂帘而入时,仿佛带来一股如阳光般和煦的力量,使得这个室内忽然暖了暖。
不同于西海女子的装束,她穿着月白色短襦,黑色及地长裙,俨然一副中原女子的打扮,而且那种莫名沉静的气质,也跟中原那些一门不迈、二门不出的大家闺秀相类。
这让金靖夕不由得感到错愕,只因鬼医连殇,又称杀手神医,是个毁誉参半的矛盾人物。一方面,此女医术绝世,救死扶伤无数;另一方面,她要求自己救起的那人、或者由别人代劳,必须替她杀一人,至于杀什么人则由她而定。
假如有人因此食言,那么她就算已经救起了那人,也会在不久之后,自行取了对方性命。
她的武功,更是到了神鬼莫测的地步。
这样一个诡谲狠辣的女子,竟然如此年轻面善,怎能不叫人惊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