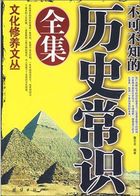他摇头,说不好。
那天,冉苏拍了拍他僵硬的脊梁骨,轻轻将他搂进怀里就像小时候一样。
“宝宝,怎么活都不要紧,只要你觉得值得。”
他“恩”了声,几不可闻,嘶哑低沉。
婚礼当天,她一身洁白,捧着花束微笑落落大方。
那个两个小小的花童挤了进来,拿着一支鲜艳欲滴血红的玫瑰,一幅包装白纸的画像,艰难的拖着几步,然后那个小女孩笑着说:“姑姑,刚刚有个哥哥让我们给你的。”
她扯开了那一幅画的包装,赫然是她,那个意大利的晚上,旖旎灼热,她隐约记得他呢喃轻哄:“菲瑶,我们不怕。”
那一支玫瑰有刺,她攥起,微戳疼了指尖。
鲜红的颜色,永恒不俗的花语。
“他……那个哥哥什么都没说对不对?”
她眼角湿润,嗓音沙哑。
女孩点点头,笑着跑开玩耍。
他不会说,他怎么会说,她曾经问他:当那些发生,你怎么还能跟我说你是爱我的。
他真的不再说了,都不说了,只有这一支玫瑰能给她。
许久前,她让他给自己画一幅画,他的自画像,可他画的却是她,意大利那个晚上,他守着她,给她画了画……
她跪在场会角落,隐忍哭泣,无声无息。
那夜,他开着银白色的跑车停驻在她的新房门口,他不知道喧闹的引擎声有没有引起她的注意。他只是想在淋一场雨,想着那个晚上,她在那座房子,也等了自己一个晚上,淋了一场雨。
等那扇窗灯光隐约熄灭,他胸口蓦然抽疼,紧得像一个缺口再也填不满,只能任那块最脆弱的肉喊着疼剧烈紧缩。
那一晚,还是下雨了,黑云压抑,树叶飘零,雨滴硕大,清清冷冷的渗进他的衣襟,胸口,凉得比以往更冷。
恍恍惚惚,他眯着浅淡俊朗的眼,响起她轻声问他:“尉至,你知道那个晚上,下雨了吗?你不知道,你一定不知道。”
今夜,没有人会再给他送伞,也没有人再来问他这个问题。
他只是仰着头,感觉到眼泪回流,冰凉刺骨,分不清眼泪和雨水。
他忍着闷疼,很想问:“叶菲瑶,你知道今晚下雨了吗?”
你不知道,一定不知道。
可从今天起,我明白,以后的雨注定只有我一个人受着。
父亲常对冉晟睿说:“儿子,女人可以有很多,最爱只会有一个。”
冉晟睿的人生是一场单薄的故事,负了一个深爱的女人,然后,废了余下的半生。
人的一生总会有几个场景忘不了,他想,是真的,直到死的那天,那些绚丽又悲凉的画面还是让他哀恸断了最后一口气。
冉苏:“自我长大有意识起,每次,我只看到了她的眼泪,笑容从来是那么的勉强,我有时想,这样的笑容曾经会不会也灿烂过,只是后来遗失在了那个男人快活的世界里。”
冉晟睿的父亲戎马一生。
冉父之前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习染既久,难免沾上奢侈、挥霍无度,奢侈荣华,平日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时男女欢场也平常不过,有些陋习也不知不觉遗留给了自己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