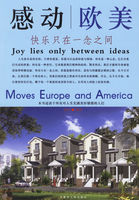就在李霓裳她们由红枫城的北城门离开之际,几股势力便由南城门,先后涌至红枫城,身负重责的暗探,使尽手段打探李氏姐妹的下落,其中还有一心想置李氏两姐妹于死地之人的死士。
马车里,李羽衣看着小铜镜中,很平凡的一张女孩脸,她很不解的开口道:“姐姐,为什么不易容成丑八怪,如果丑到极至,肯定没人愿意看咱们,这样且不是更安全。”
“傻丫头,如果真丑到极至,咱们走到那里都会引来议论及注视,先不管会承受怎样的冷潮热讽,单单那些议论,很有可能是暴露我们行踪的最大隐患,相反这种平凡之姿,走到那里都不会引起注意,反倒更安全。”李霓裳嫣然笑道,这些都是多年前多情公子教的,对她却是受用一生。
“即是这样,姐姐何不为连大哥也做个易容面具。”李羽衣闻言,觉得很有道理,她仔细盯着连瑾阳看了好一会后,便开口疑惑道。
“羽衣姑娘,何故我也要易容?”这下轮到连瑾阳不懂了,他堂堂男子,没什么需要隐藏的。
“连大哥,现在我和姐姐都是平庸之资,而你本就风姿卓越,我们的平庸之姿再做陪衬,越发显出你的不凡来。姐姐,我说得对不对。”李羽衣实话道,但询问李霓裳的尾句,却是她故意加上去的。
嗔怪的瞪了羽衣一眼,李霓裳神情有些尴尬的开口道:“羽衣的担忧不无道理,如果连大哥不反对的话,我现就着手为你做一个面具。”
“公子,两位姑娘,请容我说一句,其实公子就这样挺好的,毕竟是玉城二少,大少派出的人,再怎么样,也不会怀疑二少身边的人,如果二少易容将身份藏起来的话,反倒让大少的人起疑心了。”一直沉默的碧落,适时的开口道。
三人闻言,先是微讶,然后似明白了碧落真正的意思,因此便会心的一笑。
晌午的时候,马车终于赶至一个小的集镇,一行人找了间还算雅净的酒楼,要了个包间,连瑾阳便带着李氏姐妹先去包间了。
而碧落则匆匆的转身出了酒店,也不知道又忙着去置办什么东西。
“霓姑娘,我看你的气色不是很好,要不下午我们就在镇上寻一处客栈落脚,明天再行赶路吧!”
一路上,连瑾阳始终是魂不守舍的,李霓裳的影子到那儿,他的眼睛就跟到那,那怕是与李羽衣和碧落说话,他都会突如其来的瞥李霓裳一眼,一颗心全然都放在了她的身上,眼里、心里再也容不下其它。
“我没事,用过午膳,咱们还是继续赶路吧!”李霓裳想也未多想,径自的拒绝道,并不是她不想承连瑾阳的好意,只是相较于被姚晟他们追上的危险,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
“姐姐,你的脸色真的很苍白,我看你还是听连大哥的安排吧!”李羽衣瞧着气氛不对,急急的开口帮附道。这样做一是不想连瑾阳太过尴尬,二是姐姐易容过的脸依旧很苍白。
“可是……”
李霓裳本想解释她着急赶路的原因,美眸触及拼命对自己使眼色的羽衣,她便生生咽下想说的话,而是讪讪的改口道:“那好吧!今天暂且在这小镇上落脚。”
静等碧落回来,便叫了几样清淡菜式,几人围桌而坐,用罢午膳后,又寻了间干净的客栈落脚。其实连瑾阳曾提过帮李霓裳疗伤,但李霓裳以连瑾阳是唯一的高手,大家的安全都系在他一人身上为理由拒绝了,其实她是不想欠他过多,因此能自己承受的,她皆选择独自承受。
坐在干净清雅的客房里,李霓裳失神的把玩着连瑾阳昨夜给的小药瓶。李羽衣将包裹放置好后,转身便见姐姐失神的拿着连大哥的药瓶发呆,无奈的笑了笑,行至桌旁,并挨着姐姐坐下道:“姐姐,这不是昨晚连大哥给你的药瓶吗?你怎么了,是不是这药吃着没有效果。”
“不是,这药是很珍贵的疗伤奇药,昨晚吃了一粒,身上的伤痛已减轻不少。”李霓裳美眸恍了恍,这才回神浅笑道。
“即然这药好!那令姐姐失神的应该不是这药,而是赠这药的人。”李羽衣美眸灵动微转,她轻声且好奇的试探道。
客房门外,连瑾阳正欲抬手敲门,便听见门内李二姑娘的话,因此抬起的手,竟鬼使神差的又轻轻垂落于身侧,只因他很想听听李霓裳是怎么说的,不可否认,他自第一次见她时,便被她深深的吸引,怕自己的唐突冲撞了佳人,那份感情,他一直极力的压制着。
“你别多想,我只是觉得欠连公子太多,毕竟他与我们非亲非故,却肯如此仗义的护送我们去多情山庄,这份恩情真不知道该如何偿还。”
李霓裳见羽衣一语说中自己的心事,她神情很不自然的移开与羽衣对视的眸子,然后违心的随便找了个借口道。
“姐姐,在我面前,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连大哥做了这么多,都是因为他喜欢你,如果只是不赞成自己大哥的做法,他完全可以将我们姐妹救出后,便雇人送我们去多情山庄,何需他亲自护送。”李羽衣有些急切的开口道,虽然与连瑾阳相识时间不长,但她坚信自己没有看错,连瑾阳喜欢姐姐,而姐姐对连瑾阳也是有情意的,只是姐姐不愿意承认罢了。
“羽衣,不要再说了,我和连公子是不可能的,他是玉城二少,身份显赫,将来要娶的必是门当户对的大家千金,况且我们还有家仇未报,怎么可以沉溺儿女情长之中呢?”李霓裳柳眉一紧,她语气抽离的说道,虽然这些都是借口,却也是事实,灭门之仇,不共戴天,而自古大户人家,都讲究门当户对,所以她宁愿压制着这才开始的感情,也不愿意落得最后肝肠寸断。
门外的连瑾阳闻言,即喜又忧,喜的是李霓裳并不是对他没有一丝情意,忧的是她太理性,她坚持着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二少,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