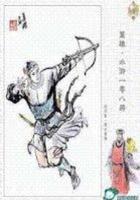鬼宗却比我十多日走前异样许多。
因多留个心眼,原是在阮菱同魔少面前遁形,遁到了离兮山脚,想亲瞧一瞧,那时在云上同魔少看到的血红脉络,是个什么东西。
念字起诀,便能够看到凡人无法看到的景象。
其实结界这种东西,一旦被破,结界者定会有所察觉,但魔少与我,甚至还有其他人都破过这层结界,鬼宗诸人不可能没有反应,之所以没动作,大概,已没将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了。
整个离兮山,已然是座溢血之山。漫天飞雪,飞的也是浅红色细雪。
可叹我先时,竟也被这样的障眼之法蒙蔽。
也能是,我现下能瞧得这般清晰,借的是血蝠的妖力。我能用的多一分,它便也噬我噬的,多一分。
凌凌似血脉之流,在脚下蜿蜒绵长,空炁里嗅的,满是血腥甜炽之味,漫天红芒,映着凄白天光异常刺目,若然我不是从小被血养着,今次见着这样的景象,定要晕上个三五次不省人事才行。
但还是瞧得触目惊心,遂大致瞧了瞧,早早捏诀将一切变了回来。
我若不加快动作,恐将这山下的城民,不日也会被血覆。
孟夏十七,离我出嫁之时,还有两日。
蚩晏再次表现的病入膏肓,似乎连我大婚之日都不能如常送我一程;鬼宗各个有些名望的长老,也全部换做傀儡;宗中子弟冷清,比如过两日就是春节大家都提前休了春假回家走亲戚——但其实大约他们都做了豢池的祭品。而我想与之说说话的葵苍,亦是副疲惫模样,唯一瞧着正常些的,只剩银缕与颜曦。
银缕是我的贴身婢女,我未出嫁前,还不能有半点闪失,颜曦贵为少宗主夫人,又是召唤血蝠的关键,自然也不能不正常。
如此一来,鬼宗倒是改名为大宣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才算正常。
从前颜曦喜欢有意无意贴近我,自与葵苍成亲,对我颇冷淡了。大宣时前有一款琼浆卖的甚好,广告语是‘晶晶亮、透心凉,’正正妥帖的形容了她今时如何待我。
但她不来贴我,我却要去贴一贴她。
她与葵苍处的院子,还是浓墨般的玄色,那一顺凌凌的梅树,也开得依好。明明是,玉梅千枝复万枝,有花堪折直须折;偏偏做,青鸦寒啼霜晓天,相见时难别亦难,如今是座空房。
寻了半晌,在鬼宗大殿后侧一处万年不结果子的杏林里找到她。
彼时她穿着樱红的裙装,薄纱质地,在那一抹及目的白与灰里显得又醒目又清冷,就像一朵敛蓄的冷梅,将将绽放,却又未绽。
紧了紧身上厚重的浅紫斗篷,距她丈余时,长声道了句:“嫂嫂——”
她并未回头。
再道了声,她方侧过头,冷言道:“什么事?”
我笑着朝她走近,因她是坐在林子里,我也只好不惧严寒的摆出要坐下的姿势,然身子甫一弯下,斗篷还没有掀起来,她已抬手将我接住,道了句:“站着说话。”
却见她待我也不是那么冷情。
可我该坐,还是坐下了,因这世上的事,不是所有旁人给你的杆子,你都要顺着往上爬,很多时候,爬的越高,摔得越惨,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要接接地气的好。
纵然,这地上,冷得很。
坐了半会,晓得她不会先开口,从怀中掏出一枚玉簪,只再微笑的:“前几日去城里,瞧着这只簪子颇有眼缘,一只买来送了姐姐,一只送予嫂嫂,还希望嫂嫂,不要嫌弃。”
她侧头朝我看了一看,我则顺势在她发髻上比试了一试,簪子的确是个好簪子,配阮菱配的出清泠,配她,却配出些姣艳。
她的目光动了一动,片刻,接过簪子,道了句:“谢了——”
又未及我开口,再道:“你有什么便说,不必讨好我,更不必,绕这么多圈子。”
我笑了笑:“送你簪子,不是想着讨好你,我是个直性子的人,也不喜欢跟人绕圈子,”瞧着她面上的绯红,若然不是这胭脂,她脸色并不好看,相由心生,一人的心不好过,面上又岂能好过,道:“就是觉得,簪子配你,所以买了。”
她似信非信的瞥了我一眼。
我道:“这世上,不是所有人,做事之前都要衡量一下与之自己的利益,我真心待你做嫂嫂,你若真心待我做妹妹,自然不会怀疑我会拿只簪子,害你——”
她的眸光蓦地换做凌然。
我笑叹道:“那夜你晓得我在门外,那些话,一半说给他听,一半却是,说给我听的,对不对?”
她没做声。
我道:“论年岁,你虽比哥哥小些,论灵力,却不在哥哥之下。哥哥那时并未分神,而你一早算准我会过去,所以觉察到我与东莱什么时辰立在门外,不是难事。”
从前我的确不知她的能耐,但自明白她身携双灵,大概那能耐,也低不到哪里去。
果见她目光涣了一涣,半晌,只道:“我只晓得你在外面,至于东莱,并未感知的到。”
我却微微吃了一惊。照理说我虽与东莱的修为相差甚远,但她感知我与东莱的本质,却不会有太大差别。这就比如你能瞧见远远搁了一只桃子,却瞧不见搁在桃子旁边的李子,逻辑上说不通,然今时并不是讨论能看见桃子还是李子,因讨论起来就会牵扯各国定律,着实费脑,即便我们可以从另一面想想看假如看桃的人是个独眼龙,但这样一来结论只会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朝着更加寻不到边际的方向发展了。
显然现下我得制止同颜曦谈话的方向那样发展。
轻咳了咳,道:“你说那些话给我听,就是想让我知道,葵苍与你的交易,便是为了我,对么?”
她再次保持沉默。
我道:“我的确现已晓得,葵苍他之所以娶你,乃是为了救我——”
她冷笑出来:“不是救你,而是将你彻底送上死路——”
我亦笑了笑,淡然看着她:“是的。”
她的笑容愈浓:“依照我哥那般性子,既然晓得真相,也一定会告诉你。”
我点了点头。
她笑意渐淡:“原是这世上,被蒙在鼓里的,只是他一人。”
我平淡的:“你与魔君,还有蚩晏,处心积虑谋划这样一件事,蚩晏他利用的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父子之情虽甚,总有一日淡去,你骗的,却是要与自己共度长生的夫君,夫君信你,你本还有让他钟意的时候,他不信你,你这一生,既是守他到枯死,也是徒然。”
她咬着唇身子狠狠颤了一下,半晌,才放开来:“即便如此,那又怎样,我也想一直待你如自己嫡亲的妹妹,但你终归——逃不了一死。”
我笑出来,看了她一眼,面上有强装的倔强,道:“是么?那你觉得,我可怜么?”不待她答话,再道:“看上去,好像是挺可怜的——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唯一对自己好的姐姐,入了修真之门也一心只为修道,被喜欢的人一剑刺死,以为复生了,便可以重新开始,开始的却不过,是另一段死到临头的绝路——”
她复冷然的:“你哪里可怜,你——”
我截断她的话头:“是,我其实一点都不可怜,真正可怜的,是葵苍——”
她的身影没甚预兆的斜了斜。
我凉凉道:“哥哥可怜,是因着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肯真正把他放在心上,放在第一位的,好好珍藏。生父利用他,妻子骗他,他最喜欢的人,喜欢的也不是他,明明是那样好的一个人,却什么,都没有。”
瞧着她面色终于苍白,徐徐的:“你可晓得,我今日来的,目的?”
她目光一闪一闪,嘴角的动作又阴狠又固执,显然不愿承认我方才的话,若说葵苍那般不幸,便彻底颠覆了她一直以来遵循的信念——得到便是好的。
这一点,倒与陆安不谋而合。
她道:“你什么都不必说,若想求我饶你一命,也只怕晚了——”
我笑道:“我若真的怕死,要求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你——”瞧她似仍自负,叹了叹道:“哪怕我晓得你有双魔灵,你是这世上唯一能够停止召唤血蝠的人——”
她总算愕然的:“你都——连这些,也晓得了?”
我笑点头:“恐怕你们以为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也知了十之八九,”再郑重看她:“譬如,我就晓得,这世间能让血蝠不再出来危害人的,就只剩下你我——不是你死,便是我死。”
不晓得是林间忽然有风,还是她自己后怕,我眼瞧着,她哆嗦了一下。
这种哆嗦,不是怕死,若她怕死,当初也不会拿自己的魔灵开玩笑,而是,假想自己一旦要离开那个人,心中便有难忍的忧痛。
我现今就日日被这种忧痛缠绕。
半晌,喉头里暗哑,朝我道:“你想怎么样?”
我默了一瞬,伸手握上她的手,她先始一惊,但我握着没有放手,她也未挣脱,后道:“我想你同我的哥哥真心相处,想你为他生许多孩子,想你们长长久久活下去。我亏欠他的,不能来还,所以想你替我,好好照顾他。”
她楞了半晌,没说话。
我续道:“哥哥需要有人真心待他,而不是各种交易虞诈——”笑弯着脑袋朝她脸上看去,一边摇了摇她的手:“我晓得你的愿望,就是同他做个普通夫妻,惹他生气的那些事就不要做了,同他开心的过日子,好不好?”
她眼神飘渺盯着我,咬牙却定定道了两个字:“宛宛——”
我道:“我明白——”
她再未吭声,反手却将我握了我,点点头。
我笑出来:“这样便皆大欢喜了——”瞧着她一时还不大适应,眼里亦流露出些惋惜,自嘲的:“反正我本就是多活了这么些年,多了个哥哥,还多了个嫂嫂,也算赚到了。”
而她默了片刻,松手又淡淡的:“你方才说晓得自己死期,又不愿血蝠复生,是要,自己了结吗?”
我没答她,只问:“月末便是召唤之阵成形的时候罢?”
她没甚意外的应了一声。
我又道:“哥哥部署一向严明,召唤之阵又须五颗心集齐才能发挥作用,是以那剩下的两颗,恐怕也就早有下落了?”
她再应了声。
我续道:“而且还是我们身边熟识的人?”
她却只看我,不说话。
那便是了,若没有这样的把握,葵苍是不能任我又认姐姐又成亲的。从前我以为他轻易应了东莱的求亲,一方面为着保我性命,更重要的,乃是因着东莱那颗心,但后来察觉并无关联,而涂宥与几位长老又死的蹊跷,多半是,他们其中有哪两个,有着那样的心脏。
也安静了片刻,片刻后,站起来拍拍身上的落雪,朝她伸手:“太冷了我要回去,你一起么?”
她并未伸手,摇了摇头。
我笑了笑,了然的朝她挥了挥手,转身离去。
步子迈了几个来回,身后传来她凛凛的声音,夹在风雪里,好像有些感伤,又像是风雪将那声音吹的变了质,又哑又散:“宛宛,我们都有各自想要的东西,各自保护的人,很多时候不是谁死,就能解决一切的——”
顿了顿,抬头,大雪深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