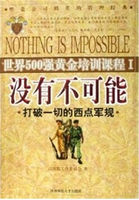回头讲,本城主将吴廷礼派人去黔东打探消息回来证实额勒登保并非虚言。的确,吴天盘独力难支,只带的一百人冲出重围,在一路拦截下,最后只剩他一个人跳进了青龙潭。这就更是雪上加霜,也将重担加在他吴廷礼肩上。
他是守城主将,又是吴巴月侄儿,责无旁贷,当全城苗兵在悲痛中推举他继任吴王时,他不避艰险,挺身而出,接下吴王大旗。
只是此时的苗军今非昔比,就像一个损坛子,虽未破碎,但裂缝已现。不到三天,先有吴廷举和杨进元两将军因通敌被处斩。接着,开国将军石三保又邀护国将军石柳邓另立山头,说:“吴廷礼、吴廷义兄弟二人不尊重我们这些老将,我要回老家去重新组织义军,你呢?”只是石柳邓不肯,说:“我们黔东几乎全部遇难,我就在这里拼了这条老命。”石三保就只身离去并留话说:“那你就留下吧,我先去,等搞起势后再与你联系。”
至于那些离队的兵丁更是不计其数,本城不战自溃。吴廷礼只得率领剩余的苗军向屏云撤退,同时命令其他各部全部向屏云靠拢。
吴廷礼到达屏云当日就做了铺排,前面由石三豹带五千人在九道弯守第一关,由石柳邓带五千人在西门山和强湖一带摆成第二道防线,石乜妹带所余女兵守屏云寨总坛。
背后,由吴双乔守抱木营,是为第一关,吴双保守黄石寨第二关,吴廷义和龙阿刚各带一万人守两侧山岭。
苗军一收缩,官军各路兵马跟着推进,将他们压缩在长不足五十里,宽不到十里的山沟里,可谓山穷水尽。
各方告急的人日夜不断,让吴廷礼茶饭不思,身不沾席,加之天气寒冷,他突发莫名之病,不到一天,含恨而死。
此刻为难之际,吴廷义知难而进,掩埋了哥哥后接过吴王大旗。而这时,前面第一关将士几乎全部阵亡,只剩几个侍卫扛着昏迷不醒的石三豹回到大营。他看过后慷慨道:“现在到拼命的时候了,杀一个得本,杀两个就赚了,苗家好儿郎们,今天好生吃饱,好生困好,明儿跟我一起上阵拼命。”
第二天早饭后,吴廷义带五百兵丁打着吴王大旗来到第二道关口。石柳邓大惊道:“吴王怎么亲自上来了?你还是坐镇大营才好。”吴廷义笑道:“别宽我心了,我们最后的时刻到了,我们这五千人怕很难顶过今天,但大丈夫死也要死在前面,怎么能死在后面。”石柳邓跟着大笑道:“好!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苗家的骨头是泥巴的还是岩头的。”
话音未落,官军守备王泰使一方天画戟,率一千人冲关。吴廷义便举起关公刀迎上前。王泰也不打话,喝一声:“来得好!”手起一戟当胸刺来。吴廷义侧身让过,顺势一刀,将其劈倒在地。旁边满人侍卫长赛灵一手持盾牌,一手握刀斜刺里冲来。吴廷义来不及举刀,只得横砍过去,扫中他小腿。塞灵一时不知这是什么刀法,尚未交手就倒了,眼睁睁看着又一刀砍来,脑袋糊里糊涂就搬了家。
石柳邓也老当益壮,挥舞两把大板刀,连砍官军部将百福和伦布春,余下官军抵敌不过只得撤退。
同时,额勒登保带着将军阿哈保,总兵朱射斗,副将那丹珠,率大部人马在吴陇登带领下从两侧山坳攻入了关口后面。守山苗兵被逼下山来,正在田间,地头,沙滩,河中与官军做最后的拼杀,这时,整个强湖和西门山都成了战场,一片混战。
吴廷义听到关口后杀声震天,急忙往后杀过来,杀至半途,手下不足四百人,却看见额勒登保正站在交叉路口观战,便挥刀向他冲去。临近,却被杨河顺挺抢拦住,说:“吴将军,你们怎么还要打?”吴廷义懒得搭理,奋力一刀砍来,可他岂是对手?刀被抢一拨,只震得两手发麻,复一枪快如闪电刺入咽喉,倒地身亡,时年三十二岁。
石柳邓自知不是杨河顺对手,不愿自取其辱,大喝一声:“老子二十年后再与你们搞!”然后挥刀自刎倒地。
额勒登保喊话:“投降可免一死!”苗兵齐吼:“投降个卵!我王吴巴月、吴廷礼、吴廷义都能死,我为哪样独活?死也要咬你一口。”额勒登保手一挥,卫队乱箭齐发。这四百苗兵与吴王旗一起倒下。杨河顺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便说:“额大人,现在就剩屏云弹丸之地,可派人劝降。”额勒登保:“不,现在是要他们找我们,不是我们找他们。你别多想了。好好休息,明日拿下他们老巢。”说完命令全体将士安营扎寨。
第二日,太阳照常升起,河里的血水早已流去,水还是那么清澈,鱼虾依然悠闲游荡,只有焚烧尸体的浓烟还在滚滚升腾。额勒登保命将士们列成阵势,不过就是在河滩、地角、田头、就地势站队,并无章法。
本来,自进山以来听从杨河顺建言,作战都用步兵,并无骑兵和炮队配合,但此时考虑是进攻吴巴月老巢,必有一场恶战,且这里地势开阔,就布置了三十门大炮,五百骑兵,以确保一锤定音。
一切就绪,副帅姜晟提一柄开山大斧全身披挂,率两千步标上寨栅门口搦战。随着三通鼓响,寨门大开,一群花枝招展女兵手舞足蹈而出。她们每人左手握一把打开的红纸伞扛在肩上,右手拿一方花手帕挥舞,脚蹬花鞋,一跳一舞,倒也整齐划一。
领头是石氏,她穿上盛装后又恢复了当年风姿,要不是鬓角露出白发,还以为是荷女回来了。她后面就是石乜妹和五百女兵。她们走出寨门后站成梅花队形舞蹈而前,远远看去,就像一朵朵鲜花缓缓向官军靠近。
这是什么阵法?姜晟和将士们看得目瞪口呆,好汉不杀无名之辈,何况是这些手无寸铁的姑娘们,个个都是十七八岁的花朵。姜晟正迟疑,有的将士也跟着跳起舞来了,如痴若狂,他急忙号令撤退,连同那些疯跳将士一齐拖回本阵。
额勒登保问:“为何不战而退?”姜晟尴尬地答:“实下不了手!都是些花儿朵儿妹娃子不说,还手无寸铁。”额勒登保皱眉道:“这是战场!退者生,挡者死!传本帅令,叫她们立刻退出,否则格杀勿论!”姜晟立刻前去喊话:“大帅有令,立刻退回去,否则格杀勿论!”喊完自回本阵。
女兵们并不搭理,依然带着灿烂的笑容且走且舞,放佛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赶边边场。额勒登保怒道:“放箭!”弓箭手乱箭齐发。前面女兵立刻身如刺猬,可没一个倒下,依然舞蹈而前。额勒登保大惊,问:“怪了!他们难道都是刀枪不入的?炮队准备!”杨河顺制止道:“不能放炮!他们可都是手无寸铁啊!放箭已经过分,怎么还能放炮?这不是征讨,这是屠杀。”额勒登保:“你别忘了,这次的旨意就是征剿,不是征讨。”杨河顺:“圣上一怒之下难免用词严厉,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临机而断,就算要剿,也够了,看不见一个男兵出战,只剩这些女兵了。”额勒登保:“可她们刀枪不入。”杨河顺摇头道:“哪能有这么多刀枪不入的!这些中箭者应该没命了,只是苗人善能赶尸,僵尸都要赶着走,何况这些鲜活的生命!”额勒登保着急道:“那你可知道解法?”杨河顺摇头道:“尚不探得。”额勒登保:“就是了,每次我都言听计从听你的,这次听我的,圣上怪罪,由本帅担着。”杨河顺无言以对。额勒登保喊一声:“放炮!”三十门大炮立刻吐出无情的火舌。
一时间,女兵们被炸得血肉横飞,有的没了头,有的肠子流了一地,有的手脚都离开了身子还在抽搐。她们并不怕死,但受不住这血腥,或吐或呕,各架着没倒下的人撤回寨子,大关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