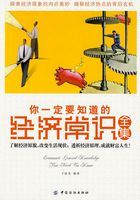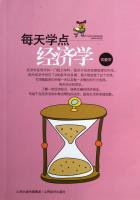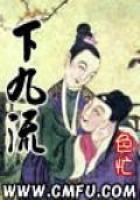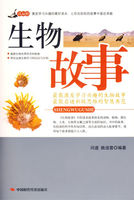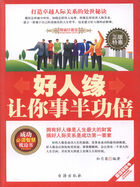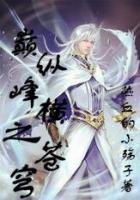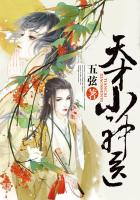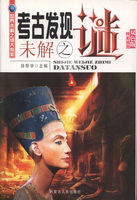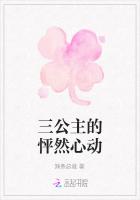奢侈消费对每个人都有必要,对于物质消费的常态来说,精神消费就是奢侈消费。对于消费依赖市场交易的常规来说,慷慨友情就是奢侈消费。对于旅游依赖参团的常规来说,“驴友”就是奢侈消费。对于攀比面子、炫耀身份的消费来说,创造性的个性消费就是奢侈消费。你以为皇室贵族都是奢侈消费?不,骑马打猎、游泳钓鱼之类,都是亲历亲为的个性消费、体验消费。以我自己的感受,特能理解年逾八旬的伊丽莎白女王自己开车、丘吉尔自己砌砖墙的乐趣。因而,特不能理解慈禧走路双手要搭在太监手上,或领导人要警卫给提鞋的享受。在我看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是享受,而是病入膏肓者的无奈。
在西方,不要说年轻人不用保姆,老年人只要能动,也绝不要人帮忙。不信,你去搀扶一位老人试试,弄不好会遭一顿抢白。我觉得动辄用保姆需要反思,至少需要把享受人伺候的惬意与失去劳作的乐趣一起拿上天平称一称,看哪个划算。西方人觉得还是自己修房子、洗车、侍弄花园划算。省钱还在其次,从劳作中体验生活才是享受。
因而,缺乏创造体验的低能消费者,必然热衷于面子消费与模仿消费。低能的、被动的、笨拙的、懦弱的消费,使消费者退化成了低能的、被动的、笨拙的、懦弱的经济人。
“面子消费”发达,“里子消费”缩瘪担心被认为是穷人,希望被认为是富人--炫耀性消费的这两个动机,恰恰代表了穷汉乍富阶段谄富欺贫的道德变脸过程。
--杨连宁
1只网球拍加1个网球多少钱?答案是110元。那球拍比球贵出多少元呢?答案是100元。如果我接着问:1个网球多少元?你会不假思索地回答:10元。你答对了吗?不对!为什么?因为离开了球拍,球可以标价10元,但独立价值不值10元。不仅球离开了球拍不值10元,离开能够打网球的场地,球拍加球也不值110元。为什么?因为球拍与球的边际效用在球场,没有场地可供人打球,球拍和球没有销路,其市价也不得不大打折扣。
附近根本没有球场的商店里,按值计价,这对球拍与球打了对折,55元,但它仍会躺在柜台里睡大觉,直至店主退货后不再进货。朋友曾送我一袋价格不菲的高尔夫球杆,但物不尽用--我没有时间去练球、打球,也不愿往高尔夫上花冤枉钱。于是,整袋球杆的效用就无从兑现。不仅物有不值,还浪费了钱。名牌运动服装在国内的畅销也是物不尽用。运动衣多,但运动场地少,买了运动服,也会很少去运动。
说到理性消费,不妨套用一下苏格拉底的名言,把“未经理性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变成“未经理性省察的消费,是不值得花钱的”。再套用一下刘禹锡的名句,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变成“钱不在多,会花就行;物不在多,尽用就行”。
******有本书,叫《中国人为什么勤劳但不富有?》。我对这个命题的回答是,不惜血本娶媳妇是个原因,倾家荡产建房子、买房子是个原因,攀比消费、炫耀消费是个原因,甚至吃喝嫖赌也是个原因。但这类病态消费行为的背后,还有更为本质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不大懂得更经济、更理性地理财,也即我一直说的“不注重盘算成本”。
对于中国人来说,京戏、国画之类文化审美行为,可以虚构;道德、文章之类政治作秀行为,也可以虚饰。但唯独市场交易行为,需要人的理性算计,来不得一星半点的虚妄。为什么?因为投资与消费的每一分钱都构成为成本,需要剔除一切浮夸、虚荣,才能避免投资折损或消费空耗。
高度雷同的消费方式,是因为除了攀比别人,自己也不会消费。也就是说,我们缺乏创造性消费与个性消费。不止是千家万户的电视机前,一大两小的三个沙发都摆成了个槽型,也不止是伙着晨练、伙着吃饭、伙着出游、伙着购物、伙着炒股,而且还攀比着花钱。消费的攀比,是买房要多、买车要大、买金要多、买钻要大,甚至憧憬价值连城的仿古瓷碗也要比别人多买几个。
多多益善,往往是经营者设给消费者的消费陷阱。譬如打印机便宜卖给你,然后靠昂贵的墨盒等耗材赚钱。超市里,你常见老人推着的购物车里,稀疏的货品连个车底都盖不住。为什么显得扎眼?因为超市提供的大容量购物车,给你提供了一个心理暗示:你要多多益善,装满车子,满足自己的占有欲。所有商店、餐馆的落地玻璃窗,也提供了类似的心理暗示:琳琅满目,珍馐奇馔,全都任你享用,你岂能无动于衷?
屡见不鲜的攀比消费,说到底还是没有个性、没有创造力的雷同消费。譬如,他不攀比别人徒步登山远足,却攀比别人旅行时携带了笔记本电脑。他不攀比别人开车出去餐风露宿,却攀比别人车上装有卫星导航。
“面子消费”发达,“里子消费”往往缩瘪。比如,在外吃得铺张,在家就吃泡面。我身边更多同胞,可能出门身上光鲜,但家里却邋遢得够戗。谁都知道,国内的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很不成熟,充满着攀比与炫耀。究其根源,可以归结为米塞斯所说的“傅立叶变态心理综合征”。地球人都患有此症,不唯中国人所独有。什么叫“傅立叶变态心理综合征”?中国人自己的解读比米塞斯本人的解读都要到位--以偏见与嫉妒看待人际差异,就是“气人有,笑人无”的“红眼病”。
1992年我下海经商,看到海南的大款亲自开车,下车时手握半块“砖头”,很是凶猛。我也一心想弄那种大哥大握握,结果,花了65000元买了一个,但是要配BP机才能用。怎么一回事?原来,那“砖头”只能打出不能打进。谁“call”我,我才抡起“砖头”打他。
今天街头拾荒人用的手机比那种“砖头”功能强大,而且更小巧便捷了,但市价比当年的BP机还便宜。手机的普及,代表了信息交流的及时与便利,也折射出我当年攀比消费、炫耀消费的幼稚与滑稽。
堵车,已成为国内无药可疗的城市顽症。而且,凡不是最新设计的小区,车位全都不足,致使居住区内车满为患,挤占了人的生存空间。小区内路边、过道、草地、花园,到处见缝插针,塞满了轿车。怎么办?上海的许多小区以月薪千元增雇车管员,每天“倒!倒!倒!好!好!好!”地不住地喊。购车人暴增,豪车也暴增。
买车只为面子、不为代步必需的人,不在少数吧?许多私家车每周停5天,白缴着停车费,只有节假日才有暇出动。不常开车,也就总也开不够起码3000公里的练车里程。
偶尔出动几次,免不了手生。你常见他们忐忑不安地开出去,刮蹭后一腔懊悔地开回来--多花了钱不说,还败坏了外出的心情。
我常见小白领装“成功人士”:把比亚迪小车的窗玻璃摇下来,把手机耳线挂在朝外的耳朵上开车--一副日理万机的老板样子。大众的老总不谙汽车在国内是攀比消费、炫耀消费,他曾百思不得其解地纳闷:怎么性价比最高、在各国销量最好的POLO,在中国却不畅销?他不懂得,中国人买车要买车壳的长、宽、高,而POLO车壳太小,不够摆阔。
按理说,私家车应该有个性。但许多家庭热衷于把它买成黑色的官轿子。深谙中国人把轿车当官轿子的日本车商,早就在3Y发动机上加装又长、又宽、又高的车壳,或把工具车改成面包车了。本田8代雅阁,有欧洲版、美洲版和中国版。在地广人稀的欧洲、美洲,车型都小。唯独在人多路窄的中国,车型最长、最宽、最高。为什么?因为中国消费者喜欢。
手机与笔记本电脑在发达国家比国内更普及,但大家会不显山不露水地携带。打手机会避开一边,压低声音。而在国内,人们打手机常常高声笑骂,旁若无人。国外用电脑喜欢用台式机,没有携带需求,不用笔记本。而且,没有要事处理,不会在公共场所使用笔记本。而在国内,选择笔记本胜于选择台式机,对于许多人来说,买笔记本不是为了携带便利,而是为了与人攀比,或人前炫耀。病态消费,就是多花钱、花大钱满足人的病态需求。譬如赌,譬如毒。性价比上,病态消费是成本昂贵、价超物值的。需求的病态,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效用的满足,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消费之外,在于人对虚妄价值的奢求。国内流行的身份消费与职务消费,就是消费的虚耗,就是泡沫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