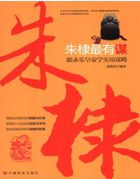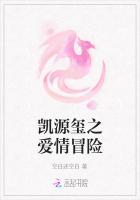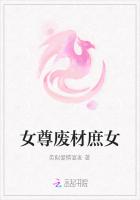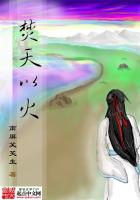一“格物”与“诚意”一一曾国藩的治学目的
在中国传统的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体系之内,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为了猎取功名,人们从孩提时起就被这种考试制度钳制了身心,从而也使一般士子学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做学问就是隔绝尘世,关起门来读书。因此,书本之外无学问、书本之外无世界的观念颇为普遍。什么政治好坏、国家兴亡等等问题都无须过问,也不想去过问。从而也就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倾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士子们对于做学问的真正而远大的目的并不清楚,并不明了。这种情形,在清朝更为突出。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清政府对学术的禁锢,以及对读书人的摧残所致。
当明朝未亡时,士气本来极盛,东林党的士大夫已有让贪官污吏侧目而视的声势;明亡时,在江南号召民兵抵抗清军的,如金声、陈子龙、吴应箕等也无一不是士大夫;即使到了明亡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也以讲求经世之学为当世大师,以复兴明室为其职志。满人入主中原后,为遏止这种士风的蔓延,采取了种种高压措施予以摧残。其摧残的手段大略有如下几种。
一是摧抑绅权。明末绅权颇张,尤以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为甚。
东林党之所以能使朝贵侧目之原因在此,金声等之所以能号召民兵抗清之原因也在此。而且,继东林党而起的复社、几社等实为号召民兵抗清的基本组织。其他各地士大夫也多以绅士资格与闻地方事务,甚至包办钱粮捐输等。这是使清政府对于士大夫感到局蹐不安的重要原因所在。所以在全国统一,大局初定后,清政府便着手实行取缔绅权的措施。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因各地拖欠钱粮,清廷便借机指斥乡绅、土豪及举贡生员的包揽;又于清顺治十七年上谕禁止江南等地士大夫结社订盟、把持公事;十八年更借江南巡抚朱国治清造欠粮册奏销之机,将所列江南士绅一万三千余人治以抗粮之罪,尽行褫革,并发交本处枷责鞭打,甚至如探花叶方蔼所欠只一厘,折合制钱一文,也被黜革,致使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歌谣。接着,清政府又颁布了士大夫不得有所建白的法律,强制各地执行。这一系列对士大夫的残酷摧残,使得一般读书人不得不日渐与世事隔绝,埋头钻入故纸堆中讨寻生活的路数。
二是文字狱之兴。封建士大夫虽被迫向故纸堆中讨生活,但清政府还是对他们放心不下,于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发生了连续不断的文字狱。自1662年即康熙元年庄廷挑的“《明史》狱”始,至1778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的“《一柱楼诗》狱”止,前后一百二十余年间,文字之狱,大小数十起。清政府对士大夫们所定的罪名大都是牵强附会,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明史》狱”和戴名世的“《南山集》狱”,只因叙述明末史事,有所谓悖逆语便触犯清廷。
明熹宗时,宰相朱国桢着有《明史》几百卷,动刻了一部分,名为《史概》。其未刻的还不少,都秘藏于家,后朱家因战乱转徙他处。后有庄姓富家赁居朱家的房子,庄家公子庄廷钱发现其未刻之《明史》稿,占为己有,又招集一时知名文人,以己意增减有关内容。书成后,定名为《明书》,未刻而庄廷钱去世。他的父亲因他死时留下遗嘱,乃组织人力将该书刊刻于世。县令吴之荣借此书向庄家索贿不成,遂于1662年赴北京,告发庄氏私撰《明史》,且其中有攻击清朝的语句,还使用南明的年号。清政府于是穷治此案,将庄廷钱尸体戮刑,庄家十八人都论死,知名士子参与其纂改者乃至刻工、书贾等问死罪者七十余人,因此案牵连而遭抓捕者男女共二千余人淤。
安徽桐城人戴名世所着《南山集》中有篇《孑遗录》,大多采用了同县方孝标所着《滇黔纪闻》的记述。康熙五十年(1了11年)被左都御史赵申乔所弹劾。清政府认定其语多悖逆,定戴名世凌迟,已死之方孝标被戮尸,曾为《南山集》作序之方苞、尤云鸮等都同时获罪。
此外,吕留良、陆生栴只因论史时发表其政治主张而触忌;汪景祺、胡中藻、徐述夔、殷宝山只因文字上偶有一二语被附会为叛逆而触忌;查嗣庭仅仅因做考官时出了一个题目便被附会为叛逆而论罪;尹嘉铨编《名臣言行录》,列入清代名臣,也被指为朋党而获罪;谢济世因注解《大学》不遵程、朱,被以为心怀怨望而论罪;王锡侯因将《康熙字典》缩编为《字贯》一书以便查阅而获罪;乃至如彭家屏因家藏《明末野史》等书,也被办个斩罪。
总之,从上述数十起大小不一的文字狱所谓的起因来看,除吕留良主张明辨夷夏大防,尚可以说是为消弭地域猜忌起见而发外,其他实多是牵强附会,有意罗织罪名而已。于是,在清政府这种有意的摧折之下,封建士大夫们即便是在故纸堆中讨寻生活,也是终日被缚紧了手足,不敢有任何越轨的行动。
三是科举的流弊。清初士大夫风气的麻木,除了上述两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科举的残害。科举制度原是历代君主“赚尽英雄头白”的长策,清代也沿而袭用,并变本加厉。其目的无非是一面用功名的虚荣来麻醉学人士子,一面以严试文的程式,来消磨学人士子的性灵。至于达到此种目的的方法,前者便是进士授官制,后者便是八股文程式之加严。
清代的科举制度有常选和特科两种类型。常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逢子午卯酉年的秋季,由政府派遣主考官,前往各省,考核各府县儒学中肄业的生员,叫做乡试。其中试者即脱学籍,称为举人。第二年即丑未辰戍年的春季,又合全国的举人会试于北京的礼部,其中试者称为进士。随后更由皇帝试进士于太和殿,叫做殿试。殿试中试者,分一、二、三甲。第一甲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均赐进士及第,状元立即授职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均授翰林院编修;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第二甲和第三甲人员更以朝考定优劣,除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者外,分别授以部属或外官(即地方官)。这就是清代的进士授官制。凡由进士授官者叫做正途出身,极被政府和社会所倚重。此种制度之特点,在其对于只供文学侍从的翰林院中诸官特别看重,治事的部属次之,临民的外官更次之。其轻重倒置如此,无非是为了鼓励士人专心于雕虫小技,而不去讲求有用之学罢了。
特科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是很特别,因而没有固定的次数。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有顺治二年(1645年)的诏举山林隐逸,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诏举博学鸿儒,乾隆元年(1736年)的博学鸿词科,乾隆十六年的诏举经明行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经济特科,以及雍正以后历帝即位时的孝廉方正科。此种特科都是由京外官吏保举而后召试的,其中尤以博学鸿儒及博学鸿词科最为隆重。其中试者也一概赐以进士出身,授以翰林院诸官以宠之。康熙年间诏举博学鸿儒时,被保举的多是被迫来应试的士子,当时如黄宗羲、顾炎武或托病,或誓死“避之若将浼”曰至乾隆初举行博学鸿词科时,已经出仕的人都争先恐后来应试。这是因为对于前者士人还能认识到这是一种政策,后者被却认为是做官的“终南捷径”了。
清代科举考试用的文体也沿用明代的八股文,其格式似乎比明代的限制更为严格。乾隆曾谕旨厘正文体,不许有艰深俳俪之作,命方苞选录所谓清真雅正的《四书》文(即八股)以为程式,以为模范,并限定每文以七百字为标准。于是,所谓程式者,便成为束缚士人的桎梏。其施行此种桎梏政策的方法,仍不外用“代圣贤立言”一语为借口,而益严其限制。惟其代圣贤立言,所以《四书》、《五经》以后书中之典实语句不能入文,士人只好束书不读,以免无意中羼入;惟其代圣贤立言,所以为文不许涉入题目的下文,有犯者谓之不轨,作违式论处,士人只好就题中的字义铺张,说些有头无尾的话罢了。因此,当时的所谓程式者,只是用以限制士人,不许其读书,不许其说有意义的话,又不许其用辞藻。此等缚手缚脚的程式,遂令士人单单学习八股文一样,往往童而习之,皓首仍不能工,哪里还有余力去做他种学问,必至得了进士之后才可稍稍从事其他,但充其量也只能作作诗和古文辞,很少余暇涉猎世务。
很显然,有了上述第一种原因,士大夫对于时事不能去过问;有了第二种原因,士大夫对于时事不敢去过问;有了第三种原因,士大夫对于时事更不会去过问。所以,尽管清末内忧外患空前剧烈,但因士大夫从根本上已失去了过问时事的机能,自然只得一任清政府误国。即使有因科举而得到一官半职者,到了可以有所作为的地位时,也由于过问时事的机能已经失去,对于时代的需要也就无从认识,只得盲从于误国的途径了。
曾国藩生逢封建社会末世,他在青少年时代自然经历了一个寒窗苦读,闭门不问世事人情的阶段,之后终于科举成名,跻身于仕途的最高阶梯。值得注意的是,当他步入政治生涯,开始接触到社会的实际问题以后,便能逐渐认识到清代学风的空华、士风的麻木,一般士子学人的治学目的并不明确,大多不能学以致用,于现实社会无所作为。他明确指出:
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曰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
曾国藩在这里自然不同意那种把做学问看做只是终日读写学习的观点,认为重要的是首先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弟”功夫学到手,加以融会贯通。如果说这段话对于治学目的的阐述还不够全面的话,那么我们看他的另一段文字: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猎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猎奴作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曾国藩在这段话中说得很明白,读书固然是在做学问,但即使行止坐卧,也有学问体现其中,重要的是要把治学与处理世事人情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有所作为,才是有真学问。想要做到这种地步,曾国藩认为归结到底就是要解决“格物”和“诚意”的问题。“格物”就是指“致知之事也”;“诚意”就是指“力行之事也”。那么,“物”究竟是什么呢?他说:“即所谓本末之物也。”他认为居国家天下,则使人民各安其所,近悦远来,推而至于为农为圃、为工为商,各思慎其职而敬其事,这便是做学问。“格”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即物而穷其理”,就是事事都要究其所以然,都要切合实际,见其功效。
这就是曾国藩对治学目的的全面理解。他的这种观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和阐发,体现了“礼(理)学经世”的实学风格,与当时一般学人士子把学问看得很窄,把它与现实政治隔绝的观念是有所区别的。
然而,曾国藩为什么能在清朝文化专制的陈腐空气笼罩之下,对治学目的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套与众不同的见解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历史环境和条件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和制约所致。但集中起来说,主要的原因则是他对“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阐发。
儒家学者传统的对社会的抱负,表现在思想上就是“经世致用”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经常接受外来文化的挑战,但不论挑战多大,最终它总能以包容并兼的态度吸收新的成分,融合各种性质不同的因素而仍保持着儒家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的基本信念。然而,历史发展到19世纪40至50年代,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在从这时起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遭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外来文化的挑战,儒家文化也首次面临着一个无法应付的新局面。
曾国藩正是在这样一种新局势、新的文化背景下继承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经世致用”思想本来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传统精神。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社会虽然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但新的阶级力量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尚未建立起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则因中国长时间的闭关自守而被拒之门外,即使有时稍有所闻,也被斥为异端邪说而立即被统治者封杀。因此,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只能从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寻找思想武器,重新举起“经世致用”这面古老的旗帜并赋予其时代内涵。近代经世致用之学的开启者为两江总督湖南人陶澍,他的弟子林则徐、贺长龄、魏源等后来都成为了有影响的经世致用派代表人物。早在进京赴考之初,曾氏便仔细研读过由魏源协助、贺长龄主持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后来,他在“经世”方面的学问主要是得益于这部书淤。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曾国藩日益留心国事,不断认识到经世之学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曾国藩一直注意与湖湘学人保持联系,深受具有主宗宋学、经世致用、兼容百家、尚节强毅等学术品格的湖湘文化的浸染。不仅新宋学名家唐鉴和他有着密切的师生关系,而且李星沅、贺长龄等也是其学术前辈,汤鹏、邓显鹤等与他的关系则介于师友之间。所以,曾国藩在翰林院时便“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于。升任内阁学士之后,他更注意充实自己的经世才识,“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盂。以后,不管从政治军如何繁忙,他总是坚持研读经世派的着作,这在他留下的三大册日记中随时可以看到,如某日读魏源《海国图志》多少页,某日读徐继畲《瀛环志略》多少页。通过研讨考究,曾国藩明确认识到:“古人无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又说:“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因此,在曾国藩的眼里,经世之学也就是礼学。曾国藩这一思想在治学目的上也是融汇贯通的,因为“礼”的目的是经世,经世必借研究经典、发挥经典的意义才能获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