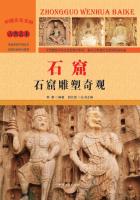两匹马在那条被马车碾出的马道上跑着碎步。心情一落千丈的阿里再看四周的景致早已没了刚才的亮丽,被马道边的深沟劈得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高原顿时多了一份苍凉与孤寂,太阳悬在头顶无情地挥洒着明晃晃的光线,更增添了他心里的焦躁。
忽然前边马道边出现的一双人影吸引了伊斯玛仪的注意:前边这两人不是本地人,你信不信?
阿里抬起头往前看去,只见道路上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在往前跌跌撞撞地走着,那个老人显然已经支持不住了,走着走着竟一头栽了下去。阿里没心思和伊斯玛仪猜谜打赌,双腿一夹马腹就来到了两人的跟前。他从马上跳下,拉着一条瘸腿跑到老人跟前俯下身去,急切地问了一句:怎么回事?
年轻人吃力地搀起老人,低着头答道:饿的,我们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年轻人一说话,阿里这才注意到原来是个女子,他看了看刚到跟前正要下马的伊斯玛仪,连忙喊了一声:别下来,赶快回去找阿依莎拿点吃的来,顺便捎点水来。
老人听到阿里的话睁开眼,目光呆痴地看了他一眼,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塞瓦布(谢谢)。
阿里一听愣了一下,他回头对伊斯玛仪说:你听到了?他醒过来了是穆斯林,快下来,把他扶到马上去。
正想往回赶的伊斯玛仪赶紧扯回马头,下马和阿里一起把老人扶到马上,阿里又把自己的马交给了那个女子:你骑我的马。
女子迟疑地:你们?
阿里赶紧上前出赛俩目:安塞俩目阿莱库木,我也是穆斯林,前边不远就到我们的家,先回家吃点东西再说别的。
女子像见到亲人一样眼里盈满了泪水,她哽咽着赶紧回答着阿里的问候:阿莱库木塞俩目。
将一老一少接进窑洞,阿依莎赶紧为他们端上一杯水,又拿过掺着菜叶的米面饼,阿里摇摇头:不行,他们已经饿成这样,不能一下子让他们吃这么硬的东西,还是先煮点稀饭吧。
院子里陆续来了几个人,都是来同阿里一起礼拜的佃户,他们站在阿里的院子里看到这一老一少,尽管还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又去往何处,但都对他们的处境唏嘘不已。
阿里每天都会在礼拜前给大家讲一点关于宗教的事情,有时是一个小故事,有时是一段经文或是圣训,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他就和大家说,我今天就不再讲卧尔兹(劝诫演讲)了,我们开始礼拜吧。
人们来到院子里,铺上一层用一绺绺长蔓草制成的草席,然后褪去鞋袜面向西方站好,阿里则站到人们的前面准备领拜,这时那一老一少一起出现到窑洞门口,女子搀扶着老者走上前来,在人们的身后铺下了两块拜毡。大家愣住了,阿里扭头看着他们做好准备,然后回头高声诵道:安拉乎艾克白勒儿。大家一起随着他抬手入拜。
礼完拜大伙散去了,阿里和女子把老者扶进窑洞坐定之后,阿里这才开口问道: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
老者慢慢舒了口气:从花剌子模的锡尔河边来。
阿里心里一惊:花剌子模?锡尔河?
老者深深地感叹着:是啊。
阿里朝老人跟前坐了坐,又是感叹又是好奇地问了一句:迢迢万里,你们爷俩儿是怎么过来的?
老者低下头去看着自己已经磨的露出脚趾的草鞋,不停地摇着头:走了三年,我都快走不动了。
伊斯玛仪听到这里,感慨地看着阿里: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老者慢慢抬起头,带着一脸茫然与无奈:我来找儿子的。
阿里点点头,他为这位老人的真情和执著感动着,顺口问道:你儿子?你儿子是谁?
老者看了看阿里,又看了看伊斯玛仪:阿穆尔丁。我叫纳贾尔·阿穆尔丁,我儿子被鞑子兵抓来东方,家里没人了,我来找他,两位好心的朵斯提(穆斯林兄弟),你们可曾听到过他的名字。
阿里和伊斯玛仪愣在那里,张着口不知说什么好了。只见老者又抬手指着身后的女子说:这孩子不是我的姑娘,我们是搭伴来的,她是找未婚夫的,她未婚夫和阿穆尔丁在一起。
伊斯玛仪一愣:在一起?那是谁?
纳贾尔老人刚要说话,那女子站在一旁抽泣了起来,泪水像一颗颗珠子流过面颊,那被戈壁大漠的风刀子划出了一道道伤口的脸上,流露的是一种极度的悲伤。纳贾尔老人回头安慰着女子:孩子,两位好心人不是别人,是我们的穆斯林,天下穆民是一家,我们就不再隐瞒了。
阿里看了看伊斯玛仪又看了看女子,他心里一惊慢慢地站起身,摆摆手不让老者说话,眼里慢慢地充盈起了泪珠。阿里顾不得女子的羞怯,一边流着泪一边打量着,从那女子被太阳烤黑了的脸上,他读出了一丝熟悉的讯息。阿里浑身打着抖,满眼的泪终于再也止不住了,他一把拉过阿依莎,嘴唇哆嗦着一指女子:她……是法图麦。
阿依莎一惊,她赶紧上前一把抓过女子的胳膊,急切地问:你真是法图麦?是真的?
女子听到有人叫出自己的名字,猛地站起身,由于激动身子趔趄了几下,她点点头,嘴里喃喃着:我找……札兰丁。
阿依莎又惊又喜,上前一把抱住了法图麦:你真的是法图麦?孩子你找到了,你看他是谁?
法图麦顺着阿依莎的手指,迷茫地看着阿里,半天摇摇头。阿里离开锡尔河草原已经十多年了,这之前他一直在撒马尔罕的礼拜寺念经,法图麦只在小时候见过他几面,她已经想不起当年阿里的影子了,看着眼前这个瘸腿的中年人,她说啥也想不到,这也是她的亲人。
阿里眼里的泪纵情地流着,他站在窑洞中间,用颤抖的声音和法图麦说:我是你的叔叔阿里呀。见法图麦还有些疑惑,他忙问了一句:孩子你爷爷———哲麦里叔叔还好吗?
法图麦瞪直眼睛又看了一下阿里,张口想说什么,可什么也没说出来。她一阵晕眩,瘫软在阿依莎的怀里。
直到傍晚,法图麦才爬起来,她央求阿依莎让她做一次大净:一路上,我们礼拜都是土净,是大能的主把我们引领到这里才找到你们的。我要洗个乌斯里(大净),然后礼虎伏坦(宵礼)。
阿依莎赶紧给她烧了一大锅热水,协助她完成了功课。
第二天一早的邦搭拜(晨礼),法图麦自己爬上了窑洞后面的沙坡,她找到一处干净的沙岗,面向西方立定,她的眼睛模糊了。
从这里望出去,四周被千万条沟壑切的七零八碎的斑驳草场,在背后射来的微光里静默着,枯黄中还有些黑黢黢的,像一个年迈的老人历经岁月的淘洗最后在额头留下的皱纹,被掏走的是精华,而留下的只有对于那些精华的回忆。不甘沉沦的下弦月挂在西天边的沙丘上,毫无生气地瞪着痴呆呆的大眼。迎面吹来的风干呼呼、热燥燥的,没有任何味道。贪睡的鸟雀还在梦里没有醒来,到处一片死寂,静得让人心里没底。
她从锡尔河草原出发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才来到这片黄土高原,一路艰辛在她心底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她曾想见到札兰丁一定把自己这一路的点点记忆说给他听听。他来时还有好多伴,至少他还是个男人,可自己除了纳贾尔老人再就是两匹牲口,后来连这不会说话的旅伴也没有了。纳贾尔老人肚子里的故事轮转着讲了几遍,再也讲不出什么新意来了,慢慢地又封进自己的心底去了,最后老人也舍不得讲故事的力气了,还要留着它多走几步路呢。
进入了铁木尔忏察隘口以后,路上就只有她和纳贾尔老人了。还好,他们没走多少弯路,进冬之前就到了黑水城。他们满心欢喜地见人就打听阿穆尔丁和札兰丁的下落,可所有的人都摇着脑袋。接下来的时间,爷俩儿几乎走遍了黄土高原的角角落落。有一次,纳贾尔老人在礼虎伏坦拜时竟哭出了声。那天,对着一轮新月,法图麦没掉眼泪,她知道自己离札兰丁越来越近,有时她似乎感觉得到札兰丁就在离她不远的某个角落,即便是后来高原上的驻屯兵都整队南下了,她也没放弃希望。现在,她终于闯进了札兰丁曾经的驻屯地,可札兰丁却被人家又驱赶着上了战场。
晚上,安排下纳贾尔,阿里陪着法图麦坐了好一会儿,将札兰丁放到他这里的那床狼皮褥子递到法图麦手里:札兰丁说你怕冷,要给你做一床狼皮褥子,他就是为了打狼才落到蒙古人手里的。
法图麦接过褥子,用手轻轻拂过毛茸茸的褥面,心里翻江倒海折腾了半夜。夜里,阿依莎又趴在她的耳边,给她讲了知道的札兰丁和阿里的点点滴滴,动情处阿依莎也不免唏嘘起来。
这会儿,站在这晨曦里审视着眼前的一切,法图麦忽然心疼起札兰丁来。同他相比,自己经历的一切还叫艰辛吗?这就是他曾经的流放地啊法图麦感叹着,阿里叔叔还说这里比蒙古高原强多了,她实在想象不出那里该是个什么样的人间地狱。这些年他们爷俩儿该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哇?
她站在沙丘上,眼前的一切在她的眼里不停地幻化着,她想起了淙淙流过的清冽甘甜的锡尔河,想起了锡尔河旁青青的草场,想起了家,想起了爷爷,想起了札兰丁……
一声梆子响传来,法图麦心里一惊,回头向坡下看去。
梆子是伊斯玛仪站在窑洞前敲响的。他敲了几下,拿着梆槌的手放到耳后,冲着面前的沟沟壑壑呼出了赞主声:安拉乎艾克白勒尔。
法图麦发现自己走神了,她赶紧摇了几下头收回思绪,虔诚地站直了身子,举意要为心中的一切美好完成今天的功课,然后抬起双手齐肩,跟着伊斯玛仪从心中发出一声赞叹:伟大的主哇。
她在心底默默地祈求着:主哇,我们已经被降生在这活的炼狱,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可我们时刻都在靠近你,我刚刚洗过乌斯里,趁这一刻洁净向您伸出双手,恳求你带领我们走出这荒漠的凄凉,带领我们走向纯净,接受我们来世做天堂的住民。容许你的仆人,还有札兰丁,看在我们伊玛尼(信仰)的坚贞,容许我们的乞求吧。阿米乃(求真主承领)!
礼完拜,法图麦慢慢地坐在那块沙丘上,后来她经常来这里,朝着家乡看一会儿,再朝着札兰丁远去的南方看一会儿。直到某一天,伊斯玛仪走来告诉她:札兰丁出征前就经常坐在这里朝着西边天空发呆。法图麦听了后眼里立马噙上了泪水,她想,他坐在这里也一定是想起了锡尔河,想起了锡尔河旁的草场,想起了家,想起了爷爷,想起了……
法图麦暗暗地下定决心,她曾经向爷爷保证过,她愿意重申自己的决心。在这远隔千山万水的黄土高原,法图麦向着心中的圣域,向着居于其中的爷爷一次次表述着自己的信心:
我一定要把他带回锡尔河草原去。
潼关之役进展的不是很顺利,让蒙古人很是头疼。拖雷思索了多日觐见窝阔台道:大金国迁都汴梁将近二十年了,全仗着潼关、黄河倚为天险,我军若从间道出宝鸡,绕过汉中,沿汉江进发,直达唐、邓二州,那时再攻取汴梁就不难了。窝阔台沉思良久:从前父汗遗命,曾令我等假道南宋下兵唐、邓,我先修书一封遣使往宋朝借道,如果他能应允那再好不过了,否则再用此计也不为迟。于是命属下绰布干为使去往大宋交涉。谁知绰布干到了沔州谒见统制张宣,两人一语不合竟被他杀死。窝阔台得信后很是震怒,命拖雷率轻骑三万径趋宝鸡,攻入大散关,又遣别将撤屋为筏,强渡嘉陵江攻入宋朝蜀地,拔取城寨共四百四十所。教训了宋军以后,蒙古人这才把账先记起来,转头会兵攻陷饶风关,飞渡汉江,向东攻击前进。
与此同时,窝阔台亲率中路军由白马渡过河取郑州后南下继续追击而由那颜斡惕赤斤统领的另一路大军也在济南渡过了黄河。至此,金朝的黄河防线全线瓦解了。
札兰丁的小队随大部队渡过汉江一路挺进,很快就进至禹山脚下。大金国守将完颜哈达、丰阿拉的大军却已早在禹山筑好了工事、摆好了阵势要以逸待劳聚歼这支远征的偏师。可此时军事上的半渡先机已失,狭路相逢就要看兵丁的英勇和将帅的谋略了。
札兰丁和属下随同大队纵马来到山下,正行进间,只听得一阵铜锣响亮,前面的大山上突然竖起大金的旗帜,金鼓隆隆,一阵流矢像飞蝗一样向着札兰丁他们迎面飞来,前面有人中箭,有几匹马见主人一头栽到地上,回头迎着大队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