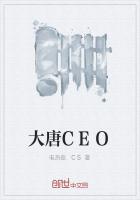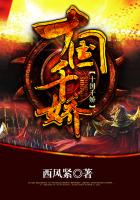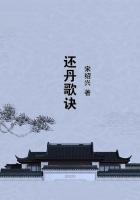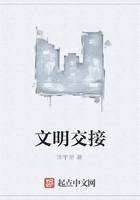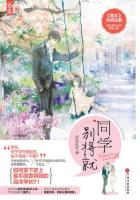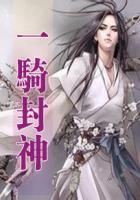他在知益州时,在成都府开府办公,按规定,各级地方官都要“庭参”,也即按礼拜见知州。拜见时,自己要宣唱自家官名姓名。即使是带着京官身份,但只要在州府差遣,就要“庭参”。有一个书生,是京中官署的干事,在成都府任录事参军,负有监督和官员档案管理的职责。他就不“庭参”,有司就责备他,他坚决说不。张咏知道后,也发火,叫人传话给他:“唯致仕,乃可免。”这是规定,除非你提前退休,可以免掉“庭参”,否则不能免。书生当即写了辞职报告,请求“致仕”,退休。报告后面还赋诗一首,末两句是:“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这个秋天不咋地,秋味淡淡的,像官场人情一般又寡又薄;满眼的山色也淡淡的,远远不如我回家的兴味浓厚。张咏也是有诗情的才子,一见之下,大为称赏,自己走下台阶来拉着这位倔强书生的手说:“部内有诗人如此而不知,咏之罪也!”咱这系统内有这么棒的诗人,而竟没有人知道,这是我张咏的过错啊!说罢,将辞职报告还给他,从此待他为上客。
还有一事。说张咏公事处理完毕后,退下,看到有个小吏在堂边昏睡,不禁心下一动,就叫醒他问:“你们家里有什么事了吗?”小吏很惶恐,答道:“我母亲病了很久了,我哥哥在外地做客不知,很久没有回来。”张咏派人去调查,小吏所言属实。第二天就派一个场务工人给他,帮他料理家务。张咏对人解释说:“我办公的地方,有人敢睡觉,一定是有隐情,忧闷,困极了才这样的。”
此事证明张咏对人情人心不乏感同身受的洞察力和同情心。
张咏是今属山东的濮州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在濮州被举为进士,当时州郡议论应该首推张咏,但张咏知道本郡有老儒名张覃,始终未能中举,就向州郡举荐了张覃,认为他应该首推。这是张咏能“让老”,年轻时,就有“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修养。
但他放出辣手来,也不含糊。这方面,他做得太过,有失正道。
辣手张咏
张咏年轻时学过击剑,为人慷慨,好出大言,乐为奇节。
有一年他到长安,在旅馆里,听到邻居一家夜半聚在一起哭泣,声音很悲酸,就去问怎么回事。主人忍不住告诉他:“我做官不自谨慎,常私用官钱。结果被家仆所挟持,想娶我家女儿。拒绝他吧,我们害怕惹祸上身;服从他吧,则女儿就要失身。日期就在近期,所以全家很悲哀,不知该怎么办。”张咏第二天到门边上等着,看到这个仆人出来,就对他说:“我跟你家主人说了,要借你到一亲旧家做点事。”仆人不很情愿,张咏用一种办法强迫他上路。到了城外一个悬崖边,下马,张咏数落他一番罪过,仆人还来不及答对,张咏挥剑将其砍落崖下。回来后,告诉邻居说:“你家那个仆人不会再来了,赶紧回家吧你们。以后要谨慎做事啊!”
这事与柳开在驿站中杀恶仆的事类似。
有可能是一件事分别安在俩人头上,也有可能当时恶仆较多,各有各的段子。此事考查起来,恶仆实恶,用这类黑色手段处理,虽然于法不合,但好歹也算是“原始正义”一把,故对张咏可以不必过多指责;但后面几件事,则透露了张咏“草菅人命”的一面,实难为他回护。
他知益州时,成都忽然有了民间流言,说有个东西叫“白头翁”,是兽是鸟,是人是怪,全不知;知道的是这个东西到了午后,就要吃人家的儿女。流言一起,州郡不安,甚至到了晚上,街上都没人敢再走路。有人主张请道士方士之类来作法“压胜”。但张咏不同意。他设法捉住了这个流言的制造者,当即将其正法,一城皆安。他对人说:“之所以有‘妖讹’兴起,是因为有灾害不祥之气作怪。妖有形,讹有声,流言就是讹言。终止讹言的办法,在于能够识别、判断它,而不在于所谓‘压胜’之类巫术。”
但这个“讹言”制造者,按法当诛吗?
史称张咏“刚方自任”,以严正、刚猛自诩自任。治理僚属往往威断。
他在做崇阳县令时,有一个小吏从仓库出来,鬓角边的头巾下有一个小钱露出。问他这钱哪儿来的。小吏瞒不过,告诉他是“库钱”。张咏命令给以杖刑。小吏倔强,回复道:“一钱何足道,即能杖我,宁能斩我耶?”张咏当即拿出笔来,写了一个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于是就给了这个小吏一个立即执行的死刑,而且是自己拿着剑,在台阶下将小吏杀掉。完事后,上表申述,自己作检讨。
知益州时,又有一小吏,因为某事触怒了他,一怒之下,他给这位小吏戴上了枷锁。小吏心不服,又发牢骚,顶撞这位“益州”的“省长”说:“哼,给我上枷容易,拿下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你不拿我的脑袋,我还就不脱这个枷锁了!”张咏对他的“悖逆”很恼火,当即说一句:“脱亦何难!”脱掉这个枷锁,又有什么难处!当即将他戴枷斩首,枷锁拿下来了。
凭好恶喜怒发落部下,且杀人,实属大恶。两个小吏都罪不当死。
他最令人发指的辣手,是一桩灭门案。
他还没有“释褐”时,曾经在汤阴一带游历。县令喜欢他,赠给他一束帛,一万钱。他就让驴子驮着,带着一个小僮回山东老家。有人跟他说:“从这里往北,有丘陵湖泽,人烟稀少,可以等有了同行的伴侣再走不迟。”张咏说:“天气凉了,家中有老亲,还没有给他们准备过冬的衣服,哪里敢再停留!”于是临时打制了一柄利剑上路了。
行走约三十里,天色已晚,在一个孤零零的小店投宿。店中只有一个老翁和俩儿子,看到他来,露出很高兴的样子。张咏生疑,后来就听到仨人悄声密语:“今夜有好买卖啦!”张咏当即心动,陡然而生一股恶念。于是睡觉前打了一捆柳枝有一抱粗,放在房间内。小店老翁来问:“弄这么个作甚?”张咏答:“明天天没有亮就要走,用它来举火照明。”张咏的意思是:你们这帮恶人,要动手,就早一点,别让我睡过头了!果然,午夜才过,老翁就让他的大儿子来叫:“鸡都叫了,秀才可以走啦!”张咏听到,装睡,不答腔。这大儿子就来推门。张咏预先用房间内家具顶住了左边那扇门,大儿子就推右边这扇。张咏先顶着右扇门,然后一松手,退立一旁,大儿子即踉跄而入。张咏抓着他的头发,将其刺死。随后将尸体拽进屋里。一会儿,小儿子又来,像刚才一样,也被张咏杀掉。等到他提着剑去找老翁,发现老翁正在烧火做饭挠痒痒。当下就将其斩杀。
然后,叫上小僮,牵驴,出门,纵火,北去。
走出二十里路,天才开始亮起来。渐渐有后来者说起:“前边有一个小店失火,全家都被烧死了。”
此事实难评说。但能下得如此辣手,也是朗朗乾坤下的一个忍人。
后来张咏也知道自己有这个恶习,于是对人说:
“张咏幸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人邪?”我张咏幸亏出生在大宋这个文明时代,可以读圣贤经典,用以自律;如果不是这样,我要是生活在五代那样的乱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这话可以看到,他对大宋有一种由衷的敬意、温情。所以他也曾对友人讲:“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为君王服务,廉节而不能说自己贫穷;勤敏而不能说自己劳苦;忠诚而不能说自己效力;公正而不能说自己能干;做到这样,就可以为君王社稷服务了。
这话说得不错,但他诛杀讹言制造者和倔强的小吏,将野店一家灭门,不能算“公”。
超脱于仁愚、贤不肖之上的智者
张咏治蜀有办法。治蜀,就离不了审案。审案,他有一句名言:
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党询之,则无不审矣。
要想了解君子的作为,就找他周围的君子来调查;要想知道小人的作为,就找他周围的小人来调查。各就其友朋党羽来调查,没有弄不清楚的案件。
他审理的案件中,有一个特别富有“春秋决狱”的性质。
说有一个民家子与姐夫有家财分配的纠纷。姐夫辩解说:“我岳父临终时,我这小舅子才三岁,所以由我来掌管岳父家的财产。岳父还留有遗书,说他日小舅子长大,要以十分之三给他,而我留十分之七。”
张咏看罢遗书后,长叹不已,还找来一壶酒向地上浇酹,然后对他说:
“你岳父真是一个智者啊!因为他的儿子太小,只有三岁,所以不得不托付给你。如果遗书中说十分之七不是给你,而是给儿子,这个儿子会早早死在你手里啦!”
于是判决:十分之七给民家子,十分之三给这位姐夫。
士庶闻听如此判案,都服气张咏判断明白。
理解这个故实,须勘透人性之“恶”;尤须勘透人性之“善”。按“春秋决狱”考量本案,岳丈有遗书,即为立约,修辞立其诚,各方当守信不移;但财产本来是岳丈家的,理应传子,即使按今天的法理考量,儿子也应该是第一继承人,故儿子应该至少得十分之七;女婿当初接受这个本末倒置的遗书,就是人性之贪,也违背了法理逻辑。本案张咏如此判决,事实上是回归了事件本身的逻辑。在善恶之外,张咏明智。
此类事,古今一体,大宋距今不远。
张咏,是那种超脱于仁愚、贤不肖之上的智者类型。宋人张舜民撰写的笔记小说《画墁录》说:“张乖崖浴为猿。”张咏洗澡的时候现原形,是一只猿。这故实说他原来是猴子变的。此说背后也含有世人对他不乏机智这一特点的调侃。
治蜀时,兵火之余,人情不安,各种“反侧”不断。宋师有不少人投降了“大蜀国”,投敌是死,造反也是死,难保没有人动这脑筋。这是特别容易出现“阴谋拥戴”的多事之秋。
有一天阅兵,军队刚刚出城,张咏从军队东北方向骑马走过。军人们忽然冲着他高喊“万岁”。张咏毫不犹豫,当即跳下马来,也冲着东北方向,三呼“万岁”。完事后,上马,揽辔继续缓缓而行。众人也不敢喧哗。这事就过去了。如果他问:“你们喊谁‘万岁’呢?”这事就大了。如果他逮捕带头喊“万岁”的,后面会有很多事说不清。任何一种处理方法都不如他这种“假痴不癫”,这一招几乎就是《三十六计》中“浑水摸鱼”“金蝉脱壳”“李代桃僵”“隔岸观火”“暗度陈仓”“釜底抽薪”“反客为主”“偷梁换柱”“无中生有”“声东击西”,最后“瞒天过海”的天才杂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