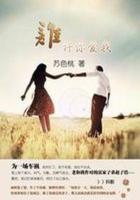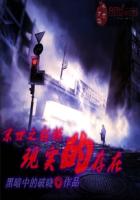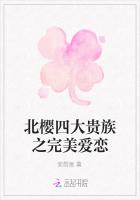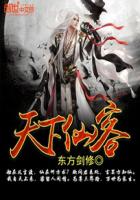卷首语
时间好像一条大河,把轻飘的、吹涨的东西顺流浮到我们手里,沉重的、结实的东西全部沉下去了。——弗兰西斯·培根[英国]
乡味儿
乡味儿之于我,就像一坛陈年老酒,不需大口喝,闻着就要醉了。
“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是乡味儿的暗涌,是我们感动莫名的暖流。“他乡遇故知”和“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霖”一起被人们誉为人生四大幸事。人在他乡,对乡味儿的渴盼是浓郁的。时光荏苒,我至今难忘十三年前的那个冬天,在北京漂泊的我,有一天,就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就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我竟然遇到了老乡。没有来由的,我们呼喊着彼此的名字,紧紧地握手,热情地拥抱。在我的记忆中,是那个惊喜的拥抱,温暖了我在异乡的整个冬天。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是乡味儿的积淀,是我们今生不灭的印记。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这穿越时空的语句,是在外游子心底的丝线,遥系着乡味儿的内核。拂去岁月的尘埃,我又记起了刻骨铭心的一幕。那是一个春节,我多年在外打工的堂兄回家过年。正月初一的早上,我们按惯例去给老族长拜年。堂兄也许是在外呆得太久了,和老族长说话时,没说家乡话。中午吃饭时,老族长再也无法容忍,夺过那个堂兄的饭碗,瞪着一双老眼说:“再这样说话,我就把你赶出家门”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了老族长的愤怒,理解了老族长颤抖的心。他其实是在痛心,什么都可以变,乡音乡味儿怎能丢?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将至,乡味儿对于在外打拼的人们,对于留守在家的人们,对于在城市的孤岛中挣扎的人们,就像一罐喷香的心灵鸡汤,可以滋补疲惫的身心,可以抵御袭人的寒冷。在万家团圆的时刻,如若不能相聚,那就打个电话,听听乡音,品品乡味儿吧。在浓得化不开的乡味儿中,这个春节不会冷。
(2007年2月14日《齐鲁晚报》)
心中那盆不灭的炭火
小时候,常常听大人们说:“过年的火,十五的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过年烧一盆炭火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每到除夕,吃过年夜饭,父亲总要把炭火烧得旺旺的。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春节联欢晚会;没有扑克、麻将,可以打发漫漫长夜;没有五彩斑斓的烟花,让大年夜绚丽多彩。一家人就那样团团围坐在蹿着火苗的火盆边,喝着茶,嗑着瓜子,吃着花生,品尝着平时吃不到的水果,聊聊家长里短,尽情地享受过年的欢乐。
不知为什么,那除了放鞭炮,再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除夕夜,我们竟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枯燥和寂寞;除了鞭炮声,就是一片漆黑的除夕夜,我们竟感到过年的时刻是那么神圣而温馨。一家人就那样守岁,守护一年的运气和财气,守望来年的平安和幸福,祈祷着来年的日子红红火火。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办公室里装上了空调,家里买了取暖器。除夕夜,若看烦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春节联欢晚会,可以打打麻将、摔摔扑克,也可以出去放一通艳丽的烟花。
随着时间推移,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烤炭火的除夕夜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然而,每年的除夕,我的心中始终有一盆不灭的炭火在燃烧,那红红的、轻轻跳跃的火苗驱走了刺骨的寒冷,照亮了前行的路途……
(2006年1月25日《大河报》)
照亮童年的纸灯笼
元宵节快到了,妻子说,我们该去给女儿买灯笼了。这时,我才想起,三年多来,我们都没给女儿买新灯笼了。
这几年,女儿年年元宵节玩的都还是三年前给她买的那个用电池的“鱼”形塑料灯笼。几年过去了,那个用电池的塑料灯笼摔不坏,烧不了。每年元宵节,女儿拿出来玩一会儿,就不太想玩了,不像我们小时候爱不释手。因此,那个塑料灯笼看起来居然还像新的,女儿也没有想要新灯笼的意思。
走在街头,商店门口挂起了各式灯笼。看着这些大多用塑料做成、靠电池发光的灯笼,我没有感到节日的欣喜和快乐,反而感到漠然。我再也不想给女儿买这些披着画皮的、没有温情的、变味儿的灯笼,我想给女儿买一个曾经照亮我童年的纸灯笼。
儿时的元宵节,灯笼制作工艺很简单。穷人家甚至无需到集上去买,用几根麻秸秆儿、竹篾做成类似兔子或圆球等的骨架,糊上几张白纸,然后用红笔或绿笔,写上字或描上图案,用木板做个蜡烛底座,一个纸灯笼就做成了。
最妙的就是玩灯笼了。吃罢团圆饭,小伙伴们先是用灯笼照遍各自家里每间屋子的每一个角落,以示驱走晦气。然后,就成群结队地走到村庄路口,排成长长的“龙”形,开始和邻近村庄的小朋友进行灯笼比赛。看哪个村庄的灯笼多,灯笼亮,灯笼美。有时,各自的领队还互相喊话,一比高低,那气势不亚于对山歌。兴奋的伙伴们,只玩得燃尽了爸爸妈妈分发的所有蜡烛,才在大人们的吆喝声中,不情愿地回家了。就是那一盏盏简陋的纸灯笼,照亮了我幸福的童年。
如今,城里每到元宵节时,都要搞灯展。设计新颖,造型美观的电灯笼,看上去很美,很豪华。可那些都是用来观赏而不是用来玩的,而且每盏灯的制作花费都是少则数百元,多则成千上万元的。灯笼越来越花里胡哨了,可玩灯笼的欢欣是越来越少了。
我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意义上元宵节玩灯笼的快乐,在现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已悄然远去了。我多么希望,当女儿看到我给她买了一盏曾照亮我童年的纸灯笼,向她讲述我童年的赛灯故事时,她不会认为那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2007年3月1日《大河报》)
陪酒
平时应酬较多,陪酒是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陪酒“生涯”中,让我记忆最深的还是上中学时的那次陪酒。
那年正月初三,我到舅舅家拜年,恰遇新表妹婿上门。我是陪新客喝酒的成员之一。
喝酒的重点对象自然集中在新客身上。酒过三巡,让我惊讶的是,我那一沾酒精就过敏的老表,竟然也喝得热火朝天。我正在纳闷,忽然看见老表的酒杯隐隐冒着热气。我忍不住大声说:“老表,我俩换着喝”众人一看,哈哈大笑,都明白了老表喝的原来是白开水老表羞得下了酒桌,溜进了厨房。多年以后,提起那事儿,老表还不住地埋怨:“你太认真了”参加工作以后,酒桌上的花样就更多了。官场上喝酒,常常是官大的喝得少,官小的喝得多。有的领导脖子一仰,看似一杯干尽,实则滴酒未进,喝酒功夫深也;有的领导豪爽地一饮而尽,喝的却全是矿泉水,让你杯中有酒也说不出也。
记得一次陪酒,我正欲举杯给领导敬酒,坐在我身旁、喝得微醉的同事小乙忽然踢了我一脚,附在我耳旁小声说:“领导喝的是……”我狠狠地瞪了小乙一眼,高高举起酒杯,和领导一饮而尽。然后,我拿起酒壶,起身去给领导斟酒。领导立马起身,端起酒杯,拍着我的肩膀连声夸奖:“小陈同志工作干得很不错”我装模作样地往领导杯子里倒酒,作斟满状。其实,领导一滴未喝。
我满是醉意地回身落座。
(2006年4月6日《大河报》)
酸菜
每当吃着大鱼大肉时,我总会想起上学时吃的酸菜。正是那酸得直冒口水的酸菜,伴着我度过了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上初中时,学校离家三四公里。由于住校,我就每星期回家带一次酸菜,通常是每次带上两三瓷缸,够一个星期吃。开始时很不习惯,但家境贫寒,也只能如此了。偶尔在食堂买一份荤菜,那便是“改善生活”了。瘦小的我吃着酸菜,竟也学习成绩优异,顺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
上了高中,学校离家更远了,有40多公里路程,只能一个多月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我不再用瓷缸装酸菜了,而是用一个大坛子,直到装够一个月吃为止。临走时,妈妈除帮我准备好一小袋米外,便是一大坛子她精心腌制的酸菜。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地到村口目送我上路,直到我翻过那座日落的西山……
在学校里,看到城里的同学穿得好、吃得好,一种自卑心理渐渐地使我变得内向了。每天除了紧张的学习之外,我便匆匆地来回于教室、寝室、食堂这三点一线之间。那时,除了每周一三五的中午在食堂买一份2角钱的素菜外,其余就用酸菜就饭了。买饭时,每当闻到从食堂里飘出来的一股股肉香,我便端着饭碗匆匆地回到寝室,偷偷地打开放在箱底的酸菜坛。冰冷的酸菜就着雪白的米饭,一口一口地往下咽。不知不觉,眼里竟噙满了泪花。
高中三年,有的同学在比吃比穿比玩中荒废了学业,而我却吃着酸菜,啃着书本,保持着优异的成绩。
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进了机关工作,就很少吃到酸菜了。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每次回老家,母亲就摆一大桌子大鱼大肉,我便问她:“家里还有酸菜吗?”母亲摇摇头笑着说:“酸菜你还没吃够吗?”
我好想再吃到妈妈精心腌制的酸菜……
(2003年8月17日《信阳日报》)
童年的爆米花
下午下班回家时,远远地就看见我家楼下围了很多人,排起了长长的队。
走近一看,原来是爆米花的。闻着那扑鼻而来的香气,我想起了童年的爆米花……
儿时,只要来了爆米花的,整个村庄就沸腾了。孩子们更是乐得像过年似的,缠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炸一点。于是,你家几碗米,我家几个鸡蛋,他家几毛钱,就能弄一小筐爆米花。那时爆米花是不用排队的,不是你让我先炸,就是我让你先炸,总是要互相谦让一番。小孩子也用不着一直眼巴巴地瞅着,只要谁家先炸出来,就可抓一把尝尝,解解馋。
大人们在拉呱,小孩们在嬉耍。随着一声声“呯”响,一锅锅热腾腾、香喷喷的爆米花新鲜出炉了,整个村庄都陶醉在爆米花浓郁的香气中。白嫩香甜的爆米花只诱得圆圆的月亮高高升起,连那清冷的月光也眼馋了。
炸完了爆米花,小孩子们匆匆吃完饭,就来到村口平整宽敞的空地上,开始玩老鹰捉小鸡、跳绳、踢毽子、斗鸡等等游戏了。谁赢了,奖励就是输者从家中偷出来的爆米花。
我们疯狂地玩呀,闹呀,直到月亮偏西,直到汗流浃背,直到大人们拿着棍子来撵着回家。
我深深地怀念童年的爆米花,怀念那爆米花般芳香的童年……
(2006年6月18日《信阳日报》)
耳根子
从小就知道耳朵是人的五官之一。可对于耳根子的重要性,却是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才对其有深刻的认识。
上小学时,要是回答不出老师提出的问题,或是做错了作业,老师惯用的伎俩就是揪耳根子。轻则揪得耳根子痒痒,重则揪得耳根子通红。虽不知为什么老师爱揪耳根子,却知道被老师揪耳根子之后,清醒许多,认真许多。记得有一次,班里几个调皮的学生,考试前不认真复习,惹怒了老师。老师一边一路揪将过去,一边痛心大声呵斥:“都什么时候了,还糊糊涂涂度春秋……”这一揪,还真管用,其它不说,连很多没被揪耳根子的学生,在作文里都常引用老师的“糊糊涂涂度春秋”这句“名言”,表示不再“糊糊涂涂度春秋”,而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在农村老家,村子里的乡亲喜爱串门。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农闲时节,大姑娘小媳妇们凑到一块儿,就会东家长西家短的聊个不休。聊的结果,常常是村东头传来婆婆说媳妇的不是,村西头传来媳妇说婆婆的难处。更有刀子口豆腐心的“长舌妇”,见面说一套,背后说一套,直说得东家鸡犬不宁,西家怒目相向。时间长了,才总结出经验教训,原来是由于耳根子软,听风就是雨,别人一说,就信以为真了。若耳根子硬,哪有那些无事瞎搅和的人的市场呢。
由于耳根子软而吃大亏的人是很多的。有一位亲戚,他的亲侄子苦心劝说他去南方投资,合伙做生意,说是既轻松,赚钱又快。禁不住诱惑的亲戚,赶到南方之后才发现,亲侄子原来是劝他搞传销,把他气得半死,恼怒而归。有一位对金融知识所知甚少的朋友,看着别人炒股大把赚钱,就兴冲冲杀入股海。恰逢印花税调整,股市大跌,赔得不轻,只呼哀哉。
任尔东西南北风,咬住青山不放松。从小处说,这是耳根子硬的表现;从大处说,这是信心和目标坚定的誓言。在各种欲望充斥的社会,保持耳根子既清醒且不软,向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就不至于活到最后还找不到北。
(2007年7月5日)
想起村口那棵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下班回家,女儿正在一遍一遍地吟诵着幼儿园老师刚教的这首唐诗。
看着女儿认真的模样,听着女儿稚嫩的童音,我想起了老家村口那棵柳,想起了站在柳树旁张望的母亲。
上高中时,学校离家六十多里地。我住校,每月只能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母亲都早早地在村口的柳树旁守候,有时等到夜幕降临,直到我带着空空的行囊回到家中。回到屋洗过脸,母亲会端上热腾腾的蛋炒饭,先填一下饿得发慌的肚子。看着我风卷残云般吃得那么香,母亲一脸的欣慰。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要去学校了。天还没亮,母亲就起来做饭,准备好我下个月要吃的咸菜。我默默地吃着饭,母亲一边帮我整理行李,一边唠唠叨叨地重复着一些关心的话语,直到好吃的东西塞满大包小包,直到心疼的话语灌满两只耳朵。
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送我到村口,站在那棵柳树旁目送我踏上返校之路。快要翻过村子西边的小山时,我回头一看,母亲仍然站在村口,偎着那棵柳树不停地张望。风乍起,丝丝柳条随风轻拂,青青的枝叶悠然曼舞,我心已酸,我泪已流。
在母亲的目光中,我渐行渐远。由不谙世事的孩子,到长大成人,完成学业,参加工作,为人夫为人父。然而,不管我走到哪里,不论我身处何方,我始终觉得,村口的那棵柳,就是我漫长人生的起点,母亲慈祥的目光,就是我今生不变的航线。
(2006年4月15日《信阳晚报》)
永远的书桌
也许是偏爱读书、写作的缘故,我对书桌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
小时候,家境贫寒。母亲房屋里那个用泥巴垒成的梳妆台便成了我写作业最好的地方。就是在那个用泥巴垒成的书桌上,我不断地汲取知识的养料,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小学、中学……
刚参加工作时,在我租住的房子里没有书桌。我从外面拾来些碎砖头,垒了两个墩子,中间放一块木板,便成了我的书桌。书桌很小,仅够铺上稿纸伏案写作。由于砖头没用水泥砌,砖头与砖头之间没有粘结,稍有不慎,两个墩子会左右摇晃。就是在那个左右摇晃的书桌上,我写成了一篇篇小说、散文、通讯……
我渴望拥有一个平静、安稳而整洁的书桌。这个愿望在我和妻走进婚姻的殿堂时终于实现了。妻好像知道我的心思,把买洗衣机、影碟机、热水器的钱全部用于布置我的书房了。不仅把最大的卧室给我做了书房,而且还配备了电脑、老板桌、老板椅、书柜,装上了“海尔”空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书桌也鸟枪换炮了。我却日益深刻地意识到,我的读书、写作是始终不能停止的,因为,母亲的慈祥在书桌上凝聚,妻子的关爱在书桌旁萦绕,我的梦幻从书桌上实现……
无论何时,我都会珍惜我心中永远的书桌,因为,那里是我生命的源泉,奋进的起点……
(2002年4月16日《信阳晚报》、8月25日《信阳日报》)
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