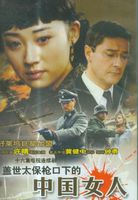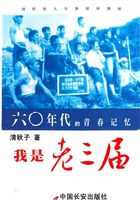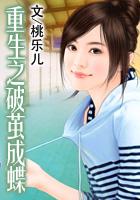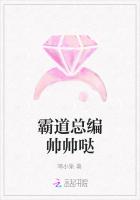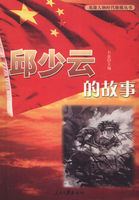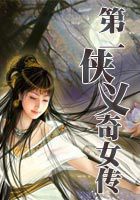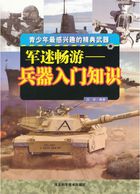与泰山对视
桑新华
第一次,这样整天地坐下来,静静地与泰山对视,是因陪朋友登山受阴雨所阻而形成的。
好友自远方来,路经此地,专为登临久仰而从未谋面的泰山而驻足。准备了半天,谁知一冬一春少雨雪,艰难孕育的好雨偏偏下在了今天。雨雾笼罩了整个世界,天湿了、地湿了,登山的热心全湿了,沉甸甸的、烦躁的。看看雨丝在微风中舞呀舞,不紧不慢,没完没了。无奈,我们在窗前坐下来,望着山,等……
泰山是一人瞩目的风景,居室楼是山怀里的颗颗纽扣,我的蜗居仅是纽扣上的一个小点,高挂楼顶,恰恰与大山形成极好的对视角度。只可惜整天疲于奔波,就像上得无法再紧的发条,人乏心更累,哪顾得上认认真真的看它一回。值此闲暇,以渐渐静下来的心,细细看风雨中的山,似酷夏午后慢慢品一杯绝好的“雨前”,品品诸般滋心润肺的味道。
山整个地浸在雨里,湿漉漉的装在我窗里。正对着的是层层叠叠后面的主峰,两翼延绵东西。草木峥嵘的繁华让寒冬脱去了,雨幕挡住了雀跃攀登观赏膜拜的人群,连同纷乱与嘈杂,只有细雨微风裹着无言的油墨,在山的脸颊上抹。挂上主峰的是雪,白皑皑的,落进附近起伏山包的是水,悄无声息地把土石树木濡湿浸黑,黑和白随意一叠,自然构成一幅茫茫大海上泊着艘洁白巨轮的写意。简单、清丽,透着初春酥雨特有的朦胧、柔和、静谧。所有细节被删去,令人心仪的景观珍宝和被人忽略的山岩顽石统统模糊成没有差别的一片,平日里闹得满山沸沸扬扬的历史卷帙和永远说不完的荣枯生灭故事,早已收藏进大山深处。山,头顶着天,脚踏着地,袒露出自自在在、从从容容的风骨,留一个空空灵灵、清清静静的境地,任我们审视。久久凝望它安然端踞的姿容,体验到一种肃穆的深邃,一种由静而弥漫升腾起的苍莽大气。古往今来,那么多人频频临访、苦苦思辨泰山伟大之所在,是否只在感受到了它守中持恒超然物外的从容宁静气质之后,才有了“稳如泰山”、“重如泰山”的结论?
我友也在全神贯注。突然头不回地问我:“山上有河吗?”有啊,直贯上下的中溪、通天河,穿行西麓的彩石河,还有……何止一条。不过它们随季节变化而消长,不像大山,始终如故地迎送无常的四季。雨季来了,任雨暴风狂、雷劈电击,山默默承受把创伤埋进心底,坦然地把丰水供给草木,送给河流。于是,河水翻腾飞溅,随势应变地跳跃奔流,水声回响在山城间。多彩的卵石趁机拥挤着、碰撞着,嘁嘁喳喳,热闹得令人眩目。雨季去了,山无言地忍受烤裂的曝晒,不惜输出脉管里的血支撑草木洒下一片绿荫。而河顿失滔滔,消落到流细声微,枯竭到河道自身迷失。此时此地,你怎能看得到呢?还记得我们学过的一句哲言吗:自然界的奇迹都在相对的静态中酝酿,宇宙的巨轮在无声中运转。动是宇宙的本能,静是自然的灵魂。静是运动之后的一种沉淀、恢复、修整、提升。静是一首诗,一种美,一种境界,具有超凡的影响力。泰山了悟了这一道理,从而获得了对事物对自己把握的力量,凝炼出任物变依然故我、宠辱不惊的庄重品格,无愧是自然界的仁者。
主峰西侧平坦的一段,那是天街,这座城市最北边的一条。其实山与城本来就一体,山与人始终共生共存、相亲相伴。城从南向北走到头便是山,由盘道接天街直到极顶,没途的各种营生与城里一样红火。这影响不了山的静,它形态静心更静,静到了人们一走进它,自觉不自觉地多一些持重和规矩。从山顶开始就有居民,一路下来到山脚,汇聚成人挨人的城池。山因有了居其中、行其中的人,除去许多拔地横空盖世凌人的孤苦和傲气;人因有了雄伟、闻名、可亲可靠的山,多了闯生活的自信、自豪和情趣。正因如此,山在泰城人心中更增加了分量,增加了敬仰的虔诚。外地人诚惶诚恐地前来对山顶礼膜拜,而对挑行李的山民气使颐指、不屑一顾,殊不知,在这里山与人不可分离,伟大与平凡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
泰山毕竟举世闻名,名山帝名城,铁定是全世界认准的旅游胜地。于是人流滚滚,八面来风。城变大了,景变美了,人心变高了。遗憾的是:南来北往的风吹来吹去,吹得心高起来的那些人少了些本分的清静、添了些浮躁的火气。腰缠万贯的老板与徒步爬山的老太太都有诸多不如意,做学问的和目不识丁的同样奔忙出无可言状的烦恼,为了什么、不为了什么都去争一争、嚷一嚷。只有泰山依旧无言,始终不语,默默地看着不肯安静片刻的人世,看着沉浮起落的大地,看着在欲望面前失去自控力、变得孩子似的那些人。那些人看做关系生前身后菪成败的大事情,山知道,和它怀里的树木流水一样,消长生灭,转瞬即逝。浮躁的追逐戏剧性的热闹,宁静的注重丰富真实的生命。两千八百年前,我们民族文化的先哲就断言: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经千年进化、世事历练,踏进现代文明门槛里的人们,怎就轻易忘记了?奢望过多失望必多,何苦自困自扰。
一种心态导致一个时代的风尚。
一旦静到泰山一般,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又有什么不能得到的。
举止西北望去,巨大的卧佛,仰枕傲徕峰,脚抵九女峰,一卧就是上亿年。它以佛的慧眼,看尽人间沧桑,任斗换星移、岁月嬗变、尘嚣汹涌,从不动容、不开口,出了嘈杂言行的浅薄而多余。一触目它那不被任何事物所惊扰、尊贵优雅的姿势和安详如满月的面容,顿觉国徽来一种化愚矫枉的巨大力量,自己平时的焦躁,渐渐化作一缕轻尘,飘然逝去,得以解脱的轻松漫遍全身。
夜来了,一切在如烟如雾的缭缈中隐退去了,清晰可见的只有闪烁在盘道和天街上,形似北斗的路灯,神秘地对我们眨眼睛:这真真实实富有灵性的对视,是一次人与自然、心灵与心灵的碰撞、交汇,是精神的净化,它正随着春雨溶进生命里。
与友相对。
我说:山,是我窗上的一幅巨画,有了它,高挂的斗室就是我灵魂的栖息地,永远。
她说:不虚此行。
烟雨佛寺
陈平原
吾乡潮州有座开元寺,顾名思义,是唐代开元年间敕建的。小时候听了一脑子关于开元寺和韩愈的传说,也隐隐约约记得那四大金刚的尊容。文化大革命毁佛驱僧时,我不在潮州,无缘目睹。只是在我插队的山村附近,有位被迫还俗的僧人,暇来与他“闲坐说玄宗”。那时开元寺已改为文化馆,既无佛像也无香火,大雄宝殿被用来办阶级斗争展览,各个配殿也都派上用场,我就曾在观音堂里参加过县里组织的乒乓球赛。八十年代重修开元寺,我恰好又出外念书,无法恭逢盛典。虽说此后每次回家乡,都不忘上开元寺走走,但已经没了儿时的那种神秘感与神圣感。坐在菩提树下,望着香火日盛的大雄宝殿,抹不掉当初荒凉的记忆,实在难以参悟。
明知文革中各寺庙的境界大同小异,但没有切身体验,游五台山或洛阳白马寺时,便更多注意佛像之庄严。俗话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还应该加一句:远去的寺庙会显灵。道理其实一样。只有“出凡”,才能“入圣”,对于太熟悉的和尚与太亲近的寺庙,很容易发现法衣底下的“世俗相”。常人不觉,转而寄希望于陌生的“远方”。我也喜欢远方的寺庙,与其说出于信仰,不如说是想借此了解此地的历史、文化与艺术。
有幸到日本来“游学”,感觉就像挂单的和尚一样,无拘无束到处游荡,但仍以佛寺为主。阅读古代及近世日本的最佳途径,除了博物馆,就是佛寺。日本的“国宝”和“文化财”多集中在寺院,其中雕刻占了九成,建筑占了六成。经历了明治初年的排佛毁释以及神道的迅速崛起,佛教在当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已经不起主导作用。即便如此,日本寺庙之多仍然令人叹为观止。据说单东京一地,大大小小的寺庙就有两千多座,我游览过的尚不足十分之一。
忽忆及唐人杜牧的《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历来注家多喜欢在“四百八十寺”上做文章,强调此诗主旨为讽诫朝廷之大建佛寺糜费钱财。我却对“烟雨”二字感兴趣,总觉得这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朦胧美。此次东游,更证实了我的直觉:寺庙的魅力离不开“烟雨”。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进寺庙自是不必考虑“阴晴圆缺”;可像我这样缺乏坚定信仰的人,往往需要外缘来接引,这时“烟雨”便起了很大作用。
烟雾缭绕的大雄宝殿,与微风细雨中的石塔,同样给人暂时脱离尘世的感觉。“烟”好烧而“雨”难求,因而,我更喜欢后者。
下雨了,如果记得带雨伞,我会顺路拜访寺庙,或者就在路边站一会,聆听断断续续随风飘来的念佛声。和尚所礼何佛所念何经与我无干,我只是欣赏这种“幽玄”的情调。此时路上行人稀少,寺庙益显凄清,大都会的喧嚣暂时隐去,心境格外澄明。远观佛寺,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平添几分神秘的意味,不若丽日中天时的“造作”。东京的寺庙大都为战后所重建,且因地皮昂贵而缩小规模或干脆改为楼房,外观上远不及奈良、京都的古寺有魅力。只有在虚无飘缈的烟雨状态下,可以忽略新寺庙造型上的缺陷,而专注于隐隐传来的梵钟。
当然,如果忘记带雨伞,或者雨如倾盆,那还是赶快回家好。
说村落
阎连科
村落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人们把村落、村庄、乡村等而视之,笼统解释为农民们聚居的地方。但若仔细辨认,村落、村庄、乡村似乎应该有些什么差别,比如说乡村必然是在偏僻的乡下,而村庄就有可能独立出现在繁闹的城市。许多大都市里至今还有村庄的存在,但那村庄里的主人却已不是农民了。然而,这些好像都不重要,人们都不会去刨根问底,重要的是农民聚居的地方和那个地方的人。
你走在山脉上,阳光斜斜地照着,山梁上除了嘎嘎不止的乌鸦就是徐徐晃动的树,这时候口也渴了,而回答你的是荒凉无垠的黄褐褐干裂的田地。恰就在这时你听到了井上辘轳的叽咕声,水淋淋的,明亮而又清丽,心中一震,转身看到一凹山腰上有几间、几十间草房,掩映在树木间,仿佛卧在树荫下疲累的牛——这个时候,你心里叫出了村落二字,开始对村落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
再或,你走在南方稻田的埂上,沉浸在一种诗意里,唐人的诗句、宋人的词句如春风一样掠过你的心头。放眼良田万亩,正为“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
的夸张感到贴切时,一阵乌云先自来了。于是,你惊了手脚,在田埂上跑得东倒西歪。也就这个当儿,从哪儿划出一条小船,先递你一张荷叶顶在头上,赶着雨水到来之前,把你载到了一丛草房的檐下。这个时刻,你心里哐咚一声,忽然更加明了村落的含义。
实际说,村落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就是农民居住的地方这一点。村落应该还有一种精神,一种温馨,一种微微的甘甜。村落是和城市相对应的存在,对于农民,它给予他们居住、生活的必需,而对于都市,它给予温暖和诗意。它既是一种物质存在,又是一种精神存在。我们可以从村落中找到农民、房舍、树木、耕牛和鸡羊,同时也应该找到农民自身生存的艰辛和对外人所付出的温馨。古文人怕是最能体味村落的含义的,无论是李、杜、白还是“八大家”,他们对村落的理解,都浓含了“愁滋味”。可轮到我们,却偏颇得很,不仅没有了对农民的“愁味儿”,连诗境也剩下不多了。单单地写出愁苦来,那不是村落,而是村落中的人,单单地写出温馨来,那也不是村落,那是村落表面的诗境。到了今天,村落剩下的就是一个符号,就是聚居农民的某个地方。所看到和理解的是新楼瓦舍,而农民那千古以来一成不变的生存形式和给别人的温馨、对自己的麻木和忍耐,却被人们从村落中删去了。
连我自己,做小说的时候,对于乡村的描绘,也是不断重复着抄袭别人的说法:
“站在山梁上望去,村落、沟壑、林地、河流清晰得如在眼前”,或说“模糊得如它们都沉在雾中”。而实际上,村落真正是个什么,沟壑的意义又是什么,河流在今天到底是什么样儿,我这个自认为是地道的农民的所谓作家,是果真地模糊得如它们都沉在雾中了。
我不敢说别人什么,而我自己,或多或少,总是感到一种内疚的。我们对村落意义的删节,并不单单是因为社会发展所致,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农民的背叛。只有在大都市住腻的当儿,我们才会想到村落,而想到的那个村落,除了田园的诗情,对农民的愁情是决然不会有的。这是当今社会中村落的悲哀,而对于村落以外的人,是什么也谈不上的,或幸或悲。
江南蓑衣
胡明刚
在故都的某个雪天里,突然想到老家江南的蓑衣来了。
满目彤云里,翻读一本江南的画册,心情一派宁静和畅。那连绵的苍翠山峦,那层层叠叠的梯田,那高低错落犹如穿着蓑衣的房舍,总给人以平和而安详。满谷烟云,缭绕着江南的烟花三月。三月的江南,春光迷漫,而乡村道上穿着蓑衣的赶着牛群的牧童,总把一管缠绵的委婉的笛声传入我的耳鼓。而穿着蓑衣在微雨中插秧的山地汉子,则把一篇耕作文章呈现在我的眼前了。
我很少听到歌唱江南蓑衣的歌曲,江南的乡野之歌似乎除了采茶桃花和篱笆修竹外,就没有别的了。而蓑衣却依然沉睡在古典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就在我的记忆中与我隔岸相望。这江南的景色一半是属于蓑衣的,这季节的一半还是属于蓑衣的。不光是春天,还有下雪的隆冬,独钓寒江的孤舟蓑笠翁,一直在我眼前描绘着悠远的江南山水。在风景中出没的穿蓑衣的人,不仅仅是牧童,而且还有渔人,他们都是志趣清雅的高人。一蓑风雨,一叶孤舟,一片兰桨,一弯明月,顺流而下,逐草而居,是多么潇洒逍遥啊。我常把穿蓑戴笠的人称之为隐士和佛陀,且看那蓑衣似乎张开诗歌或者哲学的虚玄的羽翼翩翔在空明中,如神灵一般幽黑而深邃。这是自由狂放的,是寒山中的极致,远峰、孤舟、烟雨和萧寺,只是绝妙的陪衬。江南的蓑衣飘扬在诗意中。一袭蓑衣穿行在时空,犹如达摩的一苇渡江,把无限的禅机融入空荡和苍茫之中。
江南蓑衣是平常的,一种极不起眼的家用物什,与镰刀、锄头和竹笠一起静默和谐地相处。在风雨中的劳作是艰辛的也是欢愉的,蓄满微凉的忧郁。当踏歌的农夫带着一身泥水,从田里山间归来,蓑衣和竹笠随即被挂在墙上,农夫歇息了,而它们则开始了默默的对话。蓑衣注定是蓑衣,竹笠注定是竹笠,似乎与主人一样无法逃避命运的摆布,无法摆脱生活的清寒。它们的主人一直向往看远方,但总无法走出这片山拗,他与他的老牛一起在这片小小的田地间一圈一圈地跋涉着,总超越不了这历史因袭的圆周率。雨中的蓑衣凝望着主人口鼻间升腾的气息,如雾般的慨叹着,幽幽地怀想着,难道主人真的没有幸福的愿望,没有丝毫改变命运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