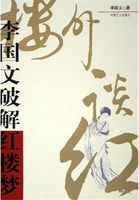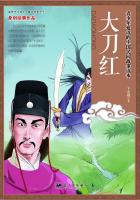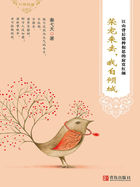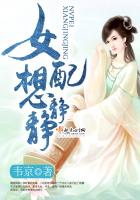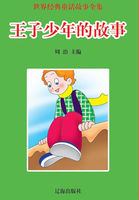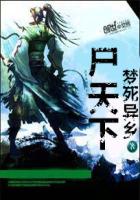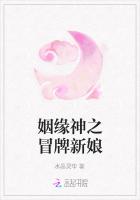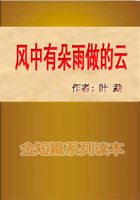如果止于爱和赞美,哨兵只是20世纪湖北众多乡土诗人中的一个。他写作的独特性在于:超越了赞美家乡赞美地方文化的一般模式,用以洪湖为叙述主体的地方志写作来展开他对个体生命和破碎生活的思考,既怀疑又审问,且将地方审美与人类审美贯连,从而成为了一个现代派诗人而非单纯体制批判的现实主义乡土诗人和单纯赞美的浪漫主义乡土诗人。
“即使严冬不散/我也不怕我将借用一盏渔火/依次照亮事物黑暗的秘密。”(《颂歌》)“照亮事物黑暗的秘密”是诗人哨兵的使命,因此,“怀疑”是哨兵诗作的基本姿态。《对洪湖的十二种疑问》是历史谱系中的追问,他叩问道:“从公元前两千年起开始下沉。距地心多远了?/再过五千年,谁依旧感恩一张渔网、一滴雨?”诗中充满了对时光、变动、物种、人生无常的追问和怀疑。他的怀疑是一种叩问,同时也是一种内省。在《秋日札记》中,爱甚至于写作本身也成了怀疑的对象。
诗人直奔人类常态思维的盲点,以众多精妙的、破碎的细节,简捷、准确、有力地表达出了独特的生活体验,吐露着命运的气象,还原生存本质,提炼出普遍意义。在反复层叠的皱褶中,“破碎感”刺痛着诗人的神经,他的诗中有生命的碎块撞击的疼痛。《生活啊我坦白我交代》这首诗通过诗人所居住的楼一层层从下至上铺展开来,从对一楼到五楼的居民生活的叙述中,以及在从过去到未来的角度中,在心底畅诉着诗人从童年到老年的各个阶段的回忆与漫思。诗人在洪湖夹街头的所看所见,聚缩了他内心深处整个生命的气息。琐碎和庸众的生活刺激着“我”的神经,内心无法找到自由的空间,心灵在夹街头的缝隙中挣扎,心中敏感尖角处的呼吸是破碎的,“我”在艰难地喘息。
在对底层这一类人的写作中,诗人最明显的态度是谦卑,是爱和怜悯。在《溺水经历》中,他写了夭折之人:“在洪湖/夭折的人只需一片破絮裹身,在洪湖/那样的人像野草一样长满了高坡”。对于这些“像野草一样的人”,诗人有着深深的怜悯。《赤壁姑妈》追溯了一个老人的一生,“赤壁姑妈”含辛茹苦,却难逃被亲人抛弃的悲惨命运,“在赤壁/我姑妈,像农贸市场里一根贫贱的芹菜/五十八岁,独身。”《为渔民兼鸭倌小赵的焦虑而作》里,诗人对小赵这种“身份不明的人”倾注了极大的同情。《返乡》这篇叙事诗歌描写“黑五类的后裔”老渔民被流放到洪湖的人生经历,其终级理想便是希望通过不断的上访返回故乡上海。从一个少年变成患类风湿的老鳏夫,以病痛和一生的时间换来一纸户口簿,死后却选择归于洪湖异乡。老渔民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落差并不是特殊个例,而是整个时代的普遍性,并运用失声的四种“语言”象征来表达这个人物分裂而多重的无奈命运,以及无法言说的疼痛。既表现了底层人物的悲痛无奈,也表现出诗人一向的反叛传统的情结。而全诗的重点“返乡”一词,点出了现实与理想,精神与物质的胶着状态以及二者永不停止的相互张力。
在这个破碎的“夹缝地带”生存,诗人不无戏谑、又带一丝苦涩地写到自己的焦虑和疼痛感:结婚后我就一直住在这边湖靠江的/夹缝地。每日醒来,推窗,/总会碰上比妻子还能唠叨的/黑鸽子。但在这无路可逃的绝境处。”
单调重复的生活让人心生倦意,因此夹缝地带是“无路可逃的绝境处”。在《无性生殖》中,哨兵描述了生活中激情的消退:这位处长江和洪湖间的夹缝地带/是一个老妇的阴户。松垂,疲软,/撩拨不了我的半点激情。
对生活的反思、对人生的追问是哨兵诗歌中主题之一,他甚至有过“未曾出世,我们已经分担了世界的不幸”这样的感言,因此少有明朗清新之作,多体现出一种沉重和焦虑。在哨兵的诗歌中,处处可见“疼痛”二字。夹缝中挤压的疼痛感、被时代异化的疼痛感、对人的命运的疼痛感以及对诗歌创作的孤独与绝望的疼痛感。在洪湖的生活处处充满灰色的记忆和令人发指的疼痛。作为儿子,童年成长的疼痛记忆;作为丈夫,却无法挽留住自己的婚姻,看到的是爱情的堕落和沉沦;作为一个诗人,只不过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过客,隐秘在湖底的深处,倾听湖水深处水藻鱼虫的低吟。等待着生命的完结,孤独、终老。
哨兵意识到,在这个小县城里,世俗遮蔽了独立,流俗代替了坚守。但诗人仍然努力保持自身的纯粹性。他将自己在洪湖边的生活视做苦修。诗人为逃避喧闹的现实,愿意与江湖为伴,到江面和湖面听涛声,看帆影。希望可以在洪湖这个被世人遗忘的地方生存,“头枕水鸟叫唤入眠或者醒来”。然而面对着一天天被污染的湖面和江水,面对逐渐凋败的花草和逐日稀少的水禽,诗人觉得这个唯一可以安身的夹缝地带也逐日被商品化的时代所吞噬。因此,更是缩紧了身躯,在这夹缝中,隐忍的活着。在破碎的碎片之中写作,在疼痛中写作。
诗人在多首诗中反复提出自己生活在夹缝中。这不仅仅是指他所生活的县城新堤处于洪湖和长江的交汇点,同时也道出了现代诗人在文坛上的尴尬失语,被挤压,在排挤的夹缝中,忍着疼痛,挣扎的活着。“我每天和镣铐活在一起,有如卡死/的铁扣或齿轮,卡在江湖的夹缝里/但我不知道我的罪愆和刑期”。
哨兵对现实的认识虽然是灰暗的,但并不代表他消极沉沦。“我将紧随掀翻大湖的北风奔波跳跃/呼喊:春天快快来让冷却的血快快苏醒!/我爱的湖洪湖。即使严冬久久不散/我也不怕我将借用一把渔火/依次照亮事物黑暗的秘密。比如黑莲/包裹绿色的心淤泥深扎甜藕的白/我爱的湖洪湖。”(《颂词》)他描写萧瑟的秋天、寒冷的冬天和黑暗,将这一切视为自然,以毅力、勇气和理智正视它,平静地理解和正视命运的挑战,以深沉、执着、发自内心的情感去参与现实。
2008年,哨兵写出长诗《水立方》。这首诗把不同的时间叠加在端午节这一天,把2008年的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纳入这一天,整体形式上按照中国传统天干地支的计时方式,以十二个时辰的节奏展开诗歌的叙事。以屈原的《离骚》和艾略特的《荒原》为两个羽翅,在端午节这个属于祭奠一个诗人的节日展开对诗歌自身的招魂。有评论家认为这是2008年唯一可以存留下来的诗歌,并将之与当年铺天盖地的地震诗比较:“这首《水立方》超过了所有的地震诗——那些为地震而写的诗歌还是在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哀悼仪式中,情感已经集体化了,已经被驯化了,并没有个体面对个体的哀悼,也没有对哀悼本身之为不可能的绝境的经验,而《水立方》这首长诗超越了这个国家所动用的所有哀悼手段,是真正来自诗歌的哀悼,如同屈原对自己的哀伤中形成诗歌内在的法度,它发端于对诗歌本身的哀悼,是对这个时代以诗歌来哀悼已经不再可能的哀悼,而那些地震诗不过是应和时代并且与时代一道崩塌的碎屑!只有哨兵彻底质疑了时光中的祭祀,因为写地震诗的诗人们并没有触及到时代的情感已经成为生长的废墟,而《水立方》这首长诗则是对废墟的重建,是来自诗歌的内在摧毁与重建,如同从《荒原》借来的题铭所暗示的。”《水立方》和哨兵的洪湖题材诗作一样,在不为人知处设问,对公共认知质疑,在习以为常处反驳,直逼盲区,照亮黑暗。
2.摆脱“程序化的言语方式”
“但那些被命名的痛苦/江湖无法言说”(《风波亭》),哨兵视“未被命名”为写作的最高理想。但摆脱“被命名”的过程是艰难的:“但多数日子,沼泽却是咬住了脚跟的大甲鱼/下沉。下沉。没有上升。淤泥/已抹掉影子。而时光/是勒紧白练的帮凶/勒过他的脖子。”面对体制,面对世俗,面对泥沙俱下的日子,诗人选择了“孤立”,选择了“苦修”,选择了坚持。但胜利谈何容易:“离世时他不会留下半句遗嘱;哨兵,男/上世纪中叶生于洪湖,从没失败/也没有胜利”。
胜利无从谈起,但也不能讲其定义为失败——从某重意义上讲,选择的作出,已经是独立道路上的一大步了。但哨兵终究没有一直焦虑下去,在《无性生殖》中,哨兵却似乎找到了一种生存之道:
在这里
我早就顺应了命运,做县城里的野鹤
江湖上的好市民。我知道没有一个人
配得上我的爱慕,更没有一种事物
配得上我仇恨。而现在
时近盛夏,我也挤进壮年
我已丧失数朵水莲的花期,丧失了说爱
说恨的权力。在我的身上只有宽容、平静
顺从的不是世俗,不是自己激烈反对的东西,而是不可测的命运。此时的哨兵豁达了许多,“宽容”和“平静”取代了焦虑和烦闷。
“好奇心丰富了我的小城生活,也让我的写作与现实时刻都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若即若离。我要求自己的诗歌不要为现实代言,但得有强烈的在场感。”在价值选择上,对在场感的看重使哨兵摆脱了“自以为是”的价值观,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上,则摆脱了“程序化的言语方式”。
确实,对现有的价值秩序,哨兵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就像我,不是我/是孤立和怀疑。”哨兵不相信既有的判断,他不会“把那些未名的渔村,书写成/县人民医院,更不可能/把那个临盆的难产儿,书写成/顺利降生的命运。”(《命运》)只相信自己,这是哨兵诗歌鲜明的特色。然而,现实何其复杂,个人的价值判断往往会显得孱弱,这也是哨兵诗歌中常常出现焦虑,显得沉重的原因。
价值上的怀疑过程,本身就包括了对“程序化的言语方式”的摆脱。哨兵诗歌的语言本身,也有鲜明的特点。他喜用短词,词语本身是平常的,但组合起来往往有奇崛的效果。如:“……终生理想/不是成为渔民和诗人,而是/回到海边去。从渔村/到县城,再到省城,到首都/……然后,折返。重复。奇迹/终于发生。”(《返乡》)一连串的词语组合,有想象不到的效果。《生活啊我坦白我交代》的诗句抒写很大程度上将象征和暗示透明化,还原了生活事物的本来面目,缩小了受众与心灵的差距。这首诗歌的呼吸很平稳,因为诗人的内心也是在随着生命的延展而平稳诉说和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