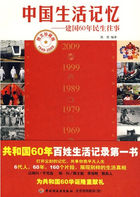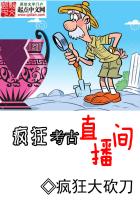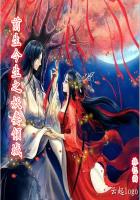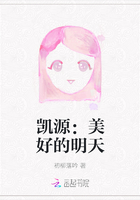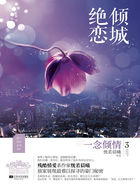郭万新
(李旭老宅)
吉庄流传着一句俚语:“光编筐筐不收沿”,就是说做事情下了功夫,最后却功亏一篑。其故事的由来,缘于李旭其人。
至今李旭家的老宅还在。一出土堡西门,村里人叫西门上,李旭曾经的住宅虽然有些破败了,但以前装饰的青砖雕花还看得很精美,不失大户人家的风范。
李旭其人,在民国二十多年很活跃,率先具备了资本运营的头脑,通过一定的财富原始积累,和吉庄村大南院二先生李会锦合伙在神头开办了票号,名号“同义源”,所印制的纸质银票称为“贴子”,相当于现在的支票,可以在朔县境内流通。如果顺利发展下去,或许就是另一个平遥“日升昌”票号。但可惜时机不利,又想投机一把,据说承包了全县的屠宰税,被有名的纪县长算计了一回,结果失策赔本,两位股东卖房卖地,一蹶不振。
李旭土改后全家十几口人占有水仓地的中等田地四五十亩,他本来又一次打算创出一个奇迹,雄心勃勃说:“代县有一家种果树的,一两年发了大财,我见过人家那处四合院,真是气派。听说盖房子时东房比西房差一寸,马上拆倒重来。财大气粗啊。”说到做到,他投入全部心血,将自家土地全部种上槟果,还养了一辆牛车。槟果是苹果的一种,当地都叫红果子,成熟时紫红色,个头就像核桃大小,气味特别芬芳馥郁,而且可以从中秋节存放到过年以后。在村民眼里,那就是最可触及的中秋节奢侈品,无论穷富总要购买,增加节日的气味,所以李旭瞅准的项目确实前景诱人。
眼看1955年,李旭见了收获,槟果开始挂果,只是数量还少,不能对外出售,但从果树的生长状况来预测,第二年一定可以大量采摘,待价而沽。谁知赶上了集体化,果树主人一朝被变成吉庄高级社的社员。村里评估时候,树叶偏偏起来虫灾,叶子都被啃花了,一棵树好像作价五角钱,也挂在账上。以后李旭的果子,村民年年每人能够分到几十斤,县里、乡里的干部也来要些,就好像村里的土特产礼品来源,李旭家分果子时与所有乡亲一视同仁,慢慢地年轻人吃果子也想不起种果子人。但村里人始终都公认,加入大集体最亏的就数曾经的票号老板李旭。
纵观李旭两次创业,一次开票号,一次种槟果,在乡下来说,谋的就算全是大事,却都没有取得应有的回报,其共同特征是艰苦创业有头无尾,半途而废,无疾而终。所以村民替李旭总结一下,以一个比喻来形容:“李旭,光编筐筐不收沿。”意思都是半成品,犹如唐僧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后没有取到真经、修成正果。村里人好像没听见李旭有过什么抵触情绪,他和四个儿子表面平静地接受了集体的安排。
如今李旭的孙子李清,担任吉庄的副支书。改革开放之处,李清家已是村里的穷困户之一。不过,李清依然具有乃祖的遗风,他凭借果断的一次承包,走上致富道路。
当年李清的父亲李守治为大队看守电话。因为家中拥挤不堪,晚上就睡在大队,李清也去陪伴父亲。猛地一天,很早大队院内吵吵嚷嚷,李清开门一看,全是村里的社员,都说今天大队召集开会,要商量包产到户之后处理一辆集体的汽车。听大家口气,如今允许个人跑运输,谁都想争先买下。李清忽然隐隐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回家时候,他碰上支书,问是否真的处理汽车,支书说:“今天开会确定呀。”李清说:“如果真卖,我也想买。”支书说:“那你就买上哇。”李清问:“要多少钱?”支书交底说:“起码两万出头。”
李清感觉有点贵,因为他知道那车原价才是两万三千元,卖两万出头算不上处理。随即他去石窑院转转,看见原来的司机李怀春正在那里鼓捣汽车,马上再返回大队,又听说李怀春准备购买汽车,胜算较大,只是具体价格还没有确定下来。不过支书宣布:“不管谁买,都得现金一次交清。”李清嘀咕说:“以前卖出过的车辆,难道都收回钱了?”支书说:“那是迟早的事。逐步往回来扣。”李清的倔劲又上来了,不管多少定要买下。他赶紧跑到司马泊连襟家,借来八千元的存折,拿去就交给会计,说是买汽车的款子。会计说:“不够吧?”李清说:“我再去凑。”会计迟疑着收下存折,李清买车等于实施了先斩后奏。他再到石窑院,发现钥匙居然就在车上插着,马上让懂驾驶的外甥女婿抢先把车开走,然后才到大队告知支书。看看木已成舟既成事实,支书也不说什么,但价格确定为两万三千元,就是原价。李清又和父子兄弟一起凑起三四千元交给大队,双方成交,由李清打条子拖欠大队一万多元,后来逐步还清了。
那一年,李清成为吉庄的运输专业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