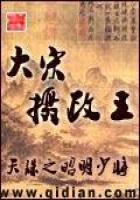在上一章说过,关注中国古代科学和艺术方面的种种成就是耶稣会士的共同爱好,此举旨在于中国历史年表这种赫赫在目的时间证据之外,以更加丰富和生动的细节来充实每一个时间,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古代中国文明。以这样的中国形象游说欧洲人,除了显得言之有物、确凿可信,更因为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对科学与艺术极为敏感,耶稣会士奉上一个文明昌盛的远古中国形象,可以事倍功半地唤起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和激赏。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正是对18世纪中期以前耶稣会士这种爱好的概括,我们已经从中窥知了耶稣会士如何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纵向脉络,本章则介绍耶稣会士所叙述的古代科学和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以便对耶稣会士的古代中国文明史形象加以横向铺陈。
在这里,我们也试着分析耶稣会士言论之所本,但与上古编年史部分不同,实际上很难判明他们究竟从哪里获得这些知识,只能指出什么样的中国文献记载了这类内容。在这里会看到,多数耶稣会士所转述的是中国人的常见观点,由此可以推测他们主要是凭借同时代中国人的一般性介绍或前代耶稣会士流传的成说来了解中国的科学与艺术。同时也能看到,耶稣会士仍在苦心孤诣地依从他们的主观意图来组织中国材料。
第一节 天文学
天文学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科学,而且中国古代天文学重观测,对各种天象有相当完整的记录,这些观测的准确性一直为耶稣会士称道,并且它们有助于确定重要的朝代或事件,是证明中国古代历史真实性的强有力证据。为此,耶稣会士普遍强调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杜赫德曾多次提到历法和天象仪,有些人更是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如宋君荣专心于通过日食记录来确认中国信史开端。从下面的介绍将看到,中国史上所重视的天象,耶稣会士都注意到了。
一、五星聚合
从第五章知道杜赫德谈起颛顼时发生五星聚合,这在卫匡国书中也有出现,不过杜赫德补充了一些新内容。他说这次五星聚合并非真正的五星聚合,中国人因为将五星聚合视为在位君主的瑞兆,故而常常将其他天象误会为五星聚合,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五星聚合中,错误者居多,王朝更替时这种错误尤甚。他还举例说,雍正二年发生了四星聚合,而这就足以使钦天监官员们按照皇帝的意愿当作五星聚合,来一个皆大欢喜。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究竟涉及些什么内容。
行星聚合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被高度关注的天象,它常常被系于人事,或兆灾异,或为祥瑞,历代《天文志》对这类现象都有详细记载。行星各种聚合方式的不同含义,按《史纪·天官书》之论,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则其下之国或“可以义致天下”,或“可以礼致天下”,或“可以重致天下”,或“可以兵从天下”,或“可以法致天下”,总之是有得天下之瑞。《汉书·天文志》亦云:“凡五星所聚宿,其国王天下……五星若合,是谓易行”。若是四星或三星交会则不然,《史纪·天官书》:“四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晋书·天文志中·七曜》:“三星若合,是谓惊立绝行,其国外内有兵与丧,百姓饥乏,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谓大阳,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之吉,四星、三星之凶,判若如此,则中国史上若真有杜赫德所说的伪造五星聚合,恐怕就不仅仅是为邀功,还为免灾。
杜赫德说中国史上记载的五星聚合错误者多,此说是否准确呢?检索《二十四史》记载的清代以前行星交会,五星聚合总计24次,其中上古2次,唐2次,北宋3次,南宋/金8次,明5次,商、春秋、汉、晋各1次(太初上元不计)。四星聚合总计14次,其中汉5次,晋4次,唐3次,北宋1次,明1次。五星聚合作为一种很不常见的天象,在清代以前发生次数几乎是四星聚合的两倍。这的确令人怀疑记载的真实性。
从总体上看正史记载的五星聚合发生时间并无规律可循,两次交会间的间隔长短波动很大。另外,图中显示,唐以前两次五星聚合的时间间隔很长,在300多年到600多年之间;在唐代,这个间隔骤然缩短,有记载的两次聚合仅相隔18年,这似乎表明唐代五星聚合发生得比前代频繁;两宋的五星聚合超前频繁,南宋时甚至有5年发生6次的情况;元代则没有这方面记录;明代发生频率也比较高,尤其是明初;清代五星聚合的记载则只有1次。按照史书历次对五星聚合的描述,该现象是指五行星聚于同一天区(星宿)。大多记录都说明五星聚于某星宿,但五星聚合频繁发生的宋、明时期却有多次记载不称会聚的具体位置。如北宋庆历三年仅书“五星皆见东方”,南宋乾道四年、六年、八年的6次只说“五星俱见”,金哀宗正大三年称“五星并见于西南”,洪武十八年、二十年称五星并见或俱见而已,永乐元年书“五星俱见东方”。这11次记载的含糊性令人怀疑其真实性,而南宋时期的记载格外让人生疑,因为除了记载潦草,这期间的多次五星聚合唯有一次被《宋史》和《金史》同时记载,即1186年那一次。除此之外,孝宗乾道年间的6次,《金史》于同一时间(金世宗大定八年、十年、十二年)却不载,金哀宗正大三年那次在《宋史》中也无记载(时为南宋理宗宝庆二年),这是最应推敲的7次。
出现这么多值得怀疑的记载,应该注意到一个原因是对五星聚合现象的定义有时代差异。严格意义上的五星聚合是五星聚于一室,《天官书》言“同舍为合”;但后来标准放松,只要五行星各居一宫相连不断就算五星聚合;清时又缩小范围,规定五行星的黄经相差小于45°才算数。上述模糊记载恰好集中出现在宋至明,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时期对五星聚合的标准放宽,将许多并非真正聚于一室的聚会现象也算为五星聚合。就此而言,杜赫德称中国史书中许多五星聚合并非真正的五星聚合也算有根据,只是这并非出于政治原因的肆意改动。于此可见,耶稣会士看待中国天文记载时不大在意中国天文学的历史沿革,也许是以欧洲关于五星聚合的标准来衡量。
与前代相反,清代关于五星聚合的记载极为稀少,截止雍正,仅有康熙元年(1662)一次,而同一时期却记载了33次四星聚合,其中顺治朝7次,康熙朝19次,雍正朝7次,这也许旁证了标准复又从严。清初不到100年间就有33次四星聚合记录,而从汉到明2000多年间只有13次记载,清以前的四星聚合记载既大大少于同时期的五星聚合记载,也大大少于清代的四星聚合记载,原因不该是四星聚合格外容易在清代发生,也不完全是五星聚合记载可能不实,最可能的原因是此前的四星聚合疏于记载。
杜赫德说雍正二年的一次火、金、水、木四星聚合被有意当作五星聚合,官员们因此受赏,这次天象被仔细记录了下来。这是需要重点辨析的一点,不仅杜赫德据此判断中国的五星聚合记载不可靠,后世汉学家在谈到中国人偶尔因为政治原因改动行星聚合记录时,所能举出的也仅此一条例证,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长久以来西方学者都听凭耶稣会士的一面之词,但是这条证据是否可信呢?杜赫德这条资料很像来自同僚苏熙业(Etienne Souciet)编辑的《耶稣会士在印度和中国所作的数学、天文和地理考察》(Observations mathématiques,astronomiques,géographiques……aux Indes et à la Chine,par les Pères de la Comp。de Jésus)第一卷,但他在引用时至少把时间搞错了,事在雍正三年而非二年。苏熙业书中原称,1725年3月(雍正三年二月)中国钦天监官员已将火、金、水、木四星的会合作为一种吉兆,奏呈皇帝,但宋君荣、雅嘉禄、戴进贤仔细观测后提出了异议。按照苏熙业的说法,中国官员奏报了一次未发生的四星聚合。不过费赖之书中的一条资料引宋君荣一封未刊信札称,中国官员把一次三星聚合当五星聚合奏报,这次发生的是地、金、水、木接近,中国官员妄奏天呈祥瑞、五星连珠,帝命史馆记录,戴进贤虽欲纠正而无效。四星聚合和三星聚合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凶象,应该不会把“四星聚合”作为吉兆奏报,而把“三星”奏为“五星”恐怕太悬殊了,所以苏熙业的说法和费赖之的引文可能都不准确。
再看中方记载。据《清实录》,当时的确发生过奏报五星聚合之事。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九,“钦天监奏,谨推得本年二月初二日庚午,日月合壁以同明,五星联珠而共贯,宿躔营室之次,位当娵訾之宫。查亥子丑同属一方,二曜五星联络晨见,亘古罕有,为此绘图呈览,请敕下史臣,永垂典册。……所奏著付史馆,并颁示中外”。二月一日,“据奏,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壁,五星联珠,为亘古难逢之大瑞,请升殿庆贺等语”。二月二日“庚午,卯刻,日月合壁,五星联珠,并见于娵訾之次。是日,诸王大臣等再奏,请皇上升殿受贺”。
但是,《清史稿》却没有记载雍正朝有五星聚合,只记载雍正元年和三年有四星聚合:元年十二月土、木、金、水聚于星纪,三年正月和二月木、火、金、水有三聚。
比较耶稣会士、《清史稿》、《清实录》的记载,可以判断出事情真相是,雍正三年事实上发生过木、火、金、水四星聚合,而此次聚合曾被钦天监官员预报为五星聚合,并在事发之前便录于史册,事发之后仍向皇帝奏称五星聚合如期发生。不过,如果说钦天监官员有意取悦皇帝而把四星聚合报为五星聚合,则未免失之武断,应该注意到,钦天监是在一月底预报了五星聚合,而预报很可能不准确,可是既然已经报呈“五星聚合”,当实际上发生的是“四星聚合”时,钦天监官员很可能是出于免罪避祸而将错就错。因此当钦天监的耶稣会士要求中国官员更改记录时,由于害怕承担欺君和失职之罪,他们当然不能公开接受这个建议。《清实录》中是事先记载下的,他们自然无权也不敢要求史官更改。然而他们实际上还是忠实记录了天象,否则《清史稿》中就应该有一条五星聚合的记录而不是“四星聚合”。另外,《清史稿》中雍正元年十一月和三年正月的四星聚合,《清实录》都没有记载,可见如四星聚合、三星聚合这类“凶象”,钦天监一般是不会向皇帝奏报的。反之,如果他们故意要把四星聚合报为五星聚合请赏,机会实在不少,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这也可以证明,此次事件主要是由于推算错误所致。可以想象,他们一再看到四星聚合,当推算出将发生一次五星聚合时会多么急于向皇帝邀功,只可惜推算错了。这么看来,钦天监官员的确有弄虚作假的成分,但不得已的因素居多,而不像耶稣会士所说的曲意逢迎。耶稣会士在对这次事件的报告中刻意突出了自己的正确和坚持真理的精神,在贬低中国官员能力的同时也贬低了他们的品质,这事实上反映出他们的优越感和对中国科学的内心态度。而前面列举的耶稣会士的三条叙述口径不一,多少也说明他们未必如他们自认的那样正确和公正。这样看来,杜赫德由此事件推出中国历史上的五星聚合记载多是伪造,纯属信口开河。而耶稣会士当年带有偏见的言辞竟然在200年后仍然误导西方学者。
杜赫德还说,中国王朝更替时对五星聚合的错误记载尤其多,此话同属臆断。五星聚合和四星聚合中,商、春秋、汉这三次五星聚合被认为是预示了江山易代、明主兴起的典型,汉元年那次尤其著名,《史记》、《汉书》、《宋书》都强调其先验性,《宋书》更是4次说起。然而,其他的五星聚合并没有发生在朝代更替之际,反而是发生在朝代更替之际的四星聚合并没有被刻意篡改为五星聚合。如汉晋的9次四星聚合都被认为是随后发生之兵乱的征兆,兵乱之后往往也是改朝换代,西汉平帝元始四年的2次对应王莽之乱和东汉光武兴复,西晋怀帝永嘉六年那次对应刘聪、石勒之乱和东晋元帝兴复,东汉献帝初平元年的2次对应董卓、李傕及黄巾、黑山之乱,建安二十二年之后则是魏文受禅,东晋太元十九年、义熙三年和九年这3次则兆示宋有天下。同样,《宋史》中所记靖康元年的四星聚合,在《金《金史》中并未以五星聚合的面目出现。应该承认,中国史书中所载五星聚合可能有不实之处,比如南宋时期,五星聚合频繁得令人吃惊,二星合、三星合也都有详细记载,却独独没有四星聚合的记载,这种巧合未免难以全信。但杜赫德所说的错误集中于王朝更替时期却并不正确。而且,现代西方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五星聚合大部分很可靠。
总之,从杜赫德表达的这些观点中隐约可见耶稣会士对中国科学常有的那种矛盾态度,一方面赞赏其悠久的历史和古代取得的成就,一方面将其与欧洲科学相比时又总持有优越感,挑拣中国天文记载中的错误也算是表达优越感的一种手段。产生优越感的原因除了是基督教文明的固有表现,也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献无法吃透,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缺乏真正了解,在这种文化隔膜之下,对只言片语的一知半解就很容易形成偏见。说到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感,我们在前面提过,耶稣会士在中国实行适应政策是对传教士和殖民者在其他地方所表现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纠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华耶稣会士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或基督教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样在中国耶稣会士的潜意识中占据着牢固地位,只是与其他地方欧洲人的表现形式和表达程度不同。从耶稣会士的行为和叙述中常常可以看出他们在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之间出入游移的痕迹。
二、日食、彗星、客星
18世纪中期,一位法国前耶稣会士德·马尔绪(Fran?ois Marie de Marsy)出版《中国历史》,在此书中赞同昔日同僚们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也引述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来说明,至少中国人的天文学知识由来已古,因而中国历史的真实性不容诋毁。此书材料取自耶稣会士的各种作品,所以通过它可以得知一些我们无法见识原本的耶稣会士作品中的内容。在天文学部分,德·马尔绪似乎依据宋君荣的《中国天文史略》多一些。德·马尔绪比较关注日食问题。他说《书经》中谈到,夏代有两位天文学家羲(Hi)与和(Ho),因为没能预报出当时发生的一次日食而受处罚,此事意味着那个时代中国人已经知道如何计算日食。这里说的是《尚书·夏书·胤征》的记载:“(仲康时)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辰指日月所会,日月不合于房宿即日食。羲、和没能预报这次日食,惹来杀身之祸,“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这次日食的时间,史籍中或以为仲康元年,或以为仲康五年,汤若望则计算出这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2155年。其实若按照卫匡国的年历,公元前2155年并非仲康时期,而要比仲康时期晚20多年,或者说卫匡国的年历中要将中国历史缩短20多年才符合这次日食的情况,但20年之差对4000多年的历史长度没什么影响,这是18世纪耶稣会士和其盟友们的一般态度,对德·马尔绪来说,能够证明中国人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已有计算日食的技术,这就说明问题了。关于这次日食在中国上古史争论中意义,第三编还会论述。
德·马尔绪还说,孔子在《春秋》中提到36次日食,根据宋君荣和其他博学的耶稣会士计算,这些日食中有32次确在孔子提到的时间发生,余下4次中有2次错误,2次存疑。而这几次不准确的日期据中国人说来自汉代编写的几部天文书,也即这是偶尔插入的后世的伪造,而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的真实性无可质疑。这表明,中国人在2000多年以前已经熟悉太阳年长365天零几小时,知道太阳和月亮的周日视运动(apparent diurnal motions)自西向东,并能通过日晷投影测算太阳子午圈高度,知道天体的赤经和中天时刻,他们同样也知道五行星的公转周期。中国人虽然没有关于行星逆行(retrograde)和“留”(stationary aspect)的星历表,但他们的观察接近正确。德·马尔绪又引一位精通中国史书的著名耶稣会士数学家Frigaut神父称,中国人的天文观测始于大洪水之后不久,但早先他们没有计时方法,故而完全通过度数计算。他们不仅能够确定日食发生的年月,还能确定是哪一天,但他们不注意日食从初亏到复圆的时间和食甚程度。
注意,耶稣会士提到《春秋》中载36次日食,但实际《春秋》中有37次记载。36次之说源出《史记·天官书》:“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列出这36次日食:
隐公1次:三年二月乙巳(前720)
桓公2次:三年七月壬辰朔(前709),十七年十月朔(前695)
庄公4次:十八年三月朔(前676),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前669),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前668),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前664)
僖公3次:五年九月戊申朔(前655),十二年三月庚午朔(前648),十五年五月朔(前645)
文公2次:元年二月癸亥朔(前626),十五年六月辛卯朔(前612)
宣公3次:八年七月庚子朔(前601),十年四月丙辰朔(前599),十七年六月癸卯朔(前592)
成公2次:十六年六月丙辰朔(575),十七年七月丁巳朔(前574)
襄公9次: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前559),十五年八月丁巳朔(前558),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前553),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前552),十月庚辰朔(前552),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前550),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前549),八月癸巳朔(前549),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前546)
昭公7次:七年四月甲辰朔(前535),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前527),十七年六月甲戌朔(前525),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前521),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前520),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前518),三十年十二月辛亥朔(前512)
定公3次:五年三月辛亥朔(前505),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前498),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前495)
首先需要纠正张守节与《春秋》经文不符的几处错误,(1)宣公八年七月的日食发生于甲子而非庚子;(2)成公十六年六月的日食发生于丙寅而非丙辰;(3)成公十七年的日食发生于十二月而非七月;(4)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的日食误为三十年发生。其次需要说明,《春秋》记月,常标“王×月”,表明是周历,张守节略去“王”而直书月。在此书法基础上可以看出,张守节的日食记录乃依《左传》而列。证据之一,僖公十二年的日食,张守节记为三月,《左传》和《公羊传》都记作王三月,《榖梁传》记作王正月;证据之二,定公五年的日食,张守节记为三月,《左传》记作王三月,《公羊传》与《榖梁传》都记作王正月。可见,张守节的日期只有与《左传》完全吻合。
张守节遗漏的一次日食发生于哀公十四年(前481)五月庚申,获麟在十四年春,这次日食恰好在获麟之后不久。《公羊》与《榖梁》都止于获麟之时,惟有《左传》止于孔子没时,因此最后这次日食于《春秋三传》中仅见于《左传》。司马迁既然谈到左丘明撰《左氏春秋》,应该不会没参考过《左传》,却不知为何要少算一次日食。张守节释司马迁的“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为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获麟,最后这次日食虽然在获麟之后,但也在获麟之年,在他所说的“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看来只能理解为司马迁和张守节都严格以“获麟”之时为界限。就史书而言,司马迁这一说法不够严谨,不过它偏偏代代相沿。《汉书·天文志》首先加以继承。张守节分明据《左传》而录日食,却也无视哀公十四年的日食,只迁就司马迁的三十六次之说,也不注明此外还有一次。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亦称《春秋》日食三十六,但他又称有甲乙者三十四,即有确切日期的三十四次。但是,《春秋》所录日食中有3次没有确切日期(桓公十七年十月、庄公十八年三月、僖公十五年五月),如果按总数36次算,应是有甲乙者三十三,既称“有甲乙者三十四”,则应是按总数37次计算的结果。如果说王应麟遗漏了桓公和僖公中的一次(庄公十八年那次被他提到),那简直比遗漏哀公十四年那次更不合情理。如果说他实际上统计了37次,而言说时只提36次,那么又为何如此拘泥于《史记》之说呢?元、明、清是否有人翻案,尚不得知。据笔者所知,1930年代中国学者关于日食的研究专著中才提出《春秋》中记录了37次日食。这也许可作为权威之影响力的一个案例吧。
在36次日食还是37次日食问题上纠缠这么久,其实是为了说明,耶稣会士采36次日食说表明他们或者没有认真阅读《春秋》本文,仅仅袭用了后世史家成说,即使是具体研究日食的人如宋君荣也可能只是挪用张守节或其他人总结出的日食时间;或者他们的确读了《春秋》,却受到自《史记》以来形成的一个根深蒂固观点的强烈影响,所以不依《左传》,或看了《左传》也舍弃获麟之后的事件。
至于德·马尔绪说,4次日期有疑问的日食,其日期来自汉代编写的几部天文书。这句话太粗略了,我们无法凭此查证究竟是指什么书。除日食之外,德·马尔绪还提到,中国人比欧洲天文学家更注意观察彗星和新星。新星在中国史书中称为“客星”。彗星与客星在中国一向被认为不祥之星,指示灾异或奇变,自然会备受关注,《春秋》中“彗星三见”,春秋时期亦有关于客星的记录,后来历代史书对彗星与客星出没都有详细记载。
附带提及关于二十八宿的记录。利玛窦的遗著中说道,中国人把天空分成几个星座,其方式与欧洲人采用的有所不同。这是耶稣会士关于二十八宿天球坐标体系的最早介绍,并且还与欧洲的天球坐标体系加以对比。此后安文思在1668年写作的《中国新志》也谈到了二十八宿,并说明中国人如何以天区与地理相配合。他说中国人“把天空划分为二十八星宿,每个星宿被分配去表示中国的某些地区,并以星宿名称呼,正好一个不落的都对应上了”。
安文思所叙述的内容在《史记·天官书》中就能找到:“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于鸟衡。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淮南子·天文训》和《星经》对此也有详明介绍,但《星经》恐怕不是耶稣会士容易看到的书。
通过以上这些介绍,我们发现,耶稣会士固然知道了不少关于中国天文学的知识,但很多情况下可能是道听途说,只有肤泛的认识。个别有能力真正读懂中国文献的人也未必查阅原典,而是寻求捷径(比如看类书)。如此看来,耶稣会士之间互相奉送的,或当时和后世其他人赠与的“博览中国典籍”、“精通中国文献”之类的帽子其实有夸大成分。而且我们再一次看到,当他们宣称某些叙述出自某书或介绍某书头头是道之时,他们未必真的看过这些书,既然如此,我们怎能轻易相信他们自称的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又怎能奢望他们能给欧洲传递一个忠实原型的中国形象?
第二节 文字与书籍
一、文字起源久远
从利玛窦开始,耶稣会士就称呼中国字为“符号字”(characters),并认为中国字与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字形很像。利玛窦说的是他当时看到的中国文字,卫匡国则进一步称,中国古文字比当代文字更像埃及象形文字,一是摹画事物形状以指示该事物这种表达方式类似,二是字形类似他在欧洲见过的埃及象形文字。这种说法启发某些欧洲人尝试借助中国文字释读埃及文字,也使当时欧洲出现的中国人起源于埃及这一推测多了一项证据。而中国人的起源问题实则也是从中国历史古老性问题中延伸出来的。
耶稣会士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且都能找到自己的史源依据。较多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文字为伏羲制造。曾德昭1640年写《大中国志》,首次公开谈论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起源时间。他说中国人的语言很古老,许多人认为它是巴别塔事件之前的72种语言之一。中国人的书籍证明,他们使用这种语言已超过3700年。据史书记载,中国文字是最早的帝王伏羲创造,距今(1640年)已有3700年之久,看来跟他们民族本身一样古老。最早的文字完全是象形的,后来形状变化,产生四种不同字体:古文(古篆)、行书、搨碑(Taipie)、缩写(草书)。卫匡国继曾德昭之后,也说中国人认为文字是伏羲发明以代结绳之政。但第四章曾经说过,卫匡国还擅做主张称中国人认为文字是天皇发明。
李明独树一帜,对伏羲造字一说显然持有异议。他认为伏羲之时使用的是象形文字(Hieroglyphicks)而不是符号文字(Characters),与其说他们在写,不如说是在画。真正的文字即符号文字是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由黄帝发明,黄帝还编纂了关于天文、数算和医药的书。杜赫德没有提黄帝造字,也未明确说伏羲造字,他将伏羲造八卦与书契两件事混为一谈,有八卦而无书契,又将飞龙氏作书契的“书契”解作“书”(book),这在第五章已经讲过。
伏羲造字或黄帝造字,在中国史书中都是比较常见的说法。前者称伏羲作书契,并制象形、假借、指事、会意、转注、谐声六书。后者认为黄帝史官苍颉造文字。还有一种更仔细的说法,称黄帝史官苍颉、沮诵观鸟兽之迹而作鸟迹篆,分类象形而生,故谓之字,字有象形、假借、指事、会意、转注、谐声六义。至颛顼时,睹蛞虫之形而作科斗书。还有人试图调和这些不一致的记载,认为伏羲制书契,黄帝又制书契,这并不矛盾,“古者书契未一,用字亦希,故随时而作,务在应用,所以周有史籀,秦有李斯,皆一时制字之人也”。
这段话并不否认伏羲始制书契,认为后世的制作重在增加文字和改变字形,这与胡宏称黄帝制鸟迹篆而颛顼又制科斗书倒似表达了同类观点。
多数耶稣会士更愿意接受伏羲造字说,这大概是因为孔安国《尚书序》首句就提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文籍由是生焉”,格外重视《尚书》的耶稣会士想必也因此信服这句话,同时接受伏羲造字说有助于说明中国文明的古老。但有个别耶稣会士更进一步,提出第三种观点,称中国文字是天授之物,上帝所造。这是一些被呼为“索隐派”(Figurists)的耶稣会士,典型者如马若瑟。
马若瑟在《六书实义》中假托一位名“温古子”的老先生说,文字或曰伏羲造,或曰苍颉造,莫衷一是,无可靠记载,故不知是谁人所造。但他又说,按照“河图洛书”之说,文字出于河洛。天堂的神灵通过将图书交付国王们而创制语言,最早的国王们得到天授文字,他们又将其代代相传,渐渐推广,所谓“字”实际上代表了天道。河洛之书与《易经》之文都是极其古老的贵重宝藏和上帝的神秘形象。马若瑟这套观点基本上以《路史》的材料为依据,他自称“河图洛书”一语乃据《路史》,而《路史》还有“天出文章,河出马图”之句,想必也启发了马若瑟。不仅如此,《路史》称苍颉受河图绿字,制古文虫篆,但不以此苍颉为黄帝史官,而以为伏羲之前的帝王。按《路史》之说,苍颉即史皇氏,为禅通纪首位君主,伏羲则是禅通纪第17位君主。马若瑟由此发现,因天而造字的苍颉生活在伏羲、黄帝之前几千乃至几万年,这说明中国文字在伏羲之前已经存在很久,这对渴望将文字起源上溯至最为古远之时的马若瑟来说,不啻雪中送炭。马若瑟甚至认为六书系统本身就蕴涵着上帝的指示,更说明中国文字是上帝所造。对“六书”来源的看法虽然主要是他研究《说文解字》、解析汉字结构的心得,但也未尝不受《路史》影响。《路史》引孔颖达称,苍颉虫篆“至今字体虽变,而六体之本古今不易”,也就是说字之六义在伏羲之前成千上万年时就存在了。
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尽管中国史书中称“六书”三代以前即已存在的比比皆是,但象形至假借等六名原为刘歆所造,索隐派的立论之本原就站不住。索隐派致力于将中国文字史推及上帝,自有其特殊目的,这在第八章还会谈到。总之,耶稣会士中存在着对中国文字历史的第三种观点,这也是论证中国历史古老起源的另一种结论。这种观点在耶稣会士中是少数派,其所依据的中国史家之论亦属旁支。
二、五经来源
文字与书籍总是相因相成,耶稣会士们经常以中国文字和书籍之古老互证,比如前述曾德昭以中国书籍之悠久说明中国语言至1640年已使用了3700多年,李明则以黄帝撰写历书、算书和《方书》表示中国文字在公元前2600多年时就存在。而“五经”几乎是耶稣会士用以说明中国文明悠久时必不可少的证据。“五经”的权威性既在于其古老性,也在于它们是中国自然和道德哲学的典范,因此耶稣会士称“五经”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圣经》在欧洲的地位,其他许多有权威性的书都是脱胎于“五经”,比如“四书”。既然如此,对“五经”的来源、内容和意义的评介也是耶稣会士们的必要工作。
绝大多数耶稣会士都提到,中国人认为《易经》是第一位帝王伏羲所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书,曾德昭和德·马尔绪则有更详细的说明。曾德昭说,《易经》论述自然法则、自然哲学,用数字、图象和符号表示哲理,并把这些用于德行和善政,最早是伏羲、神农和黄帝使用的神秘方式,后来在公元前1123年由周文王和周公编成书刊行。德·马尔绪介绍,伏羲原本的作品仅是六十四卦,是一张由象形符号组成的图表。书中还有对这些卦的演绎和评注,出自各位博学之士,尤以孔子为著。孔子是率先解答《易图》之谜的人,他将卦与五行之性、道德说教和政府规则结合起来解释,从这些玄义中推导出一个规则系统,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曾德昭和德·马尔绪关于《易》之流变的介绍反映了中国最通行的意见,即《易》之爻卦之象起于伏羲之时,爻卦之辞则起于中古,先后有神农作《连山》,黄帝作《归藏》,文王、周公作《周易》;孔子又作《十翼》之辞,且“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后世《易》学主流都本于孔子,上述引文就出自孔子所作《序卦》。而耶稣会士的理解也算准确,孔子使《易》的方向发生重大转折,将卜筮之辞变为治国之道,服务于其政治和道德学说。
耶稣会士对《易》的内容有不同认识,普遍来说,既排斥又想肯定,因为它既是迷信之书,又是孔子那充满理性的道德学说之一部分。曾德昭和德·马尔绪强调《易》的社会管理功能,另一些人则毫不掩饰对《易》迷信性质的轻视。安文思只承认书中偶有一些可能出自伏羲的崇高道德格言和戒律值得阅读和景仰,其他内容则是后人冒添,不值得相信。李明认为,《易经》是中国人根据伏羲创作的一些关于自然的晦涩诗歌编写而成,后人没有的足够的理解能力以及该书本身极度晦涩模糊导致它任人解说并引发诸多迷信。龙华民(NicolasLongobardi)竟提出伏羲就是巫术发明者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易经》就是这位巫术之王的巫术大典。
与上述两类都不同的是索隐派耶稣会士,他们对《易》极端迷恋,但迷恋的不是孔子的解说,而是据说源于伏羲之时的那些卦象,其根本意图与马若瑟推远中国文字起源完全一样,认为《易图》是天赐之物,蕴藏关于上帝的信息。比如马若瑟以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口吻说,《易经》“是一本纯粹象征性的书,是我们这个可见世界的形象。无知的人在其中只看到感觉到的东西,天、地、植物、动物等等。圣贤的人在其中发现了其他妙不可言的东西”。
耶稣会士这种矛盾态度是他们自身的理性标准和极度推重孔子的态度相互作用的结果,更进一步说,是他们的信仰和为在中国立足而采取的权宜策略间抗衡的结果。这种冲突伴随耶稣会士在华的整个时期,但具体到每个时段,哪种意见占上风则有些细微区别。不管怎么说,耶稣会士们都承认《易》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籍,也是证明中国古老文明的有力证据。
关于《尚书》,耶稣会士称《书经》是中国最有权威的书,而他们于“五经”之中也对《尚书》怀有最高敬意。他们介绍说,《书经》是关于古代帝王的编年史,内容包括尧舜时期和夏、商、周三代,重点讲述尧、舜和三代帝王们的德政,有许多指导生活的优秀格言警句。安文思干脆说《书经》就是关于尧、舜、禹、汤、武王这五位帝王的编年纪,这当然不符实情。《尚书》的诞生时间比《易》明确,其古老性和真实性更加无疑。安文思说仅夏、商、周三代就延续了近2000年,几乎与秦至清初的总长一样,此话暗示《尚书》至少已存在3800年左右。李明更进一步,称距1696年近4000年前,即黄帝以后300年左右,中国人收集格言,写了一部关于尧帝的历史,这应该是指《尧典》。而后,舜和禹制定的祭典和各种法律,商、周时期有益的训诫和规定都分别被写下来,以留传子孙。于是,中国人将上述这一切都汇集起来,编成一本叫做《书经》的书。李明等于宣称,《尚书》的记载可上溯至公元前2300年左右,也即中国的信史至少可上溯至此。在耶稣会士眼里,《尚书》的权威性不仅来自其古老和真实,还在于它保存了许多关于古代宗教的内容,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谈论。
18世纪中期以前的耶稣会士大都对《诗》的态度比较冷淡,因为他们习惯于从道德内涵而非文学角度评价《诗》,可是他们又没有从《诗》中看出中国人所赋予的道德训诫意义,所以他们对《诗》之所以还不大肆恶评,大概也就是冲着孔子的面子。曾德昭最早提到《诗》,泛泛而言其中的古代诗歌都有隐喻和诗意,表现人类天性和不同风俗,这种说法还是遵照中国人的意见而发。李明谈到《诗经》系周朝时编写,描写各地诸侯的行为与习俗。他说,孔子怀着极大的敬意提到这些诗,然而当前所见《诗经》中却有一些非常荒谬乃至有渎圣之嫌的内容,两者对比可以推测,这些诗歌在漫长年月中混入一些不好的篇章,以至于被败坏。德·马尔绪说,《诗经》中的古代诗歌部分是宗教性的,部分是非宗教性的;有些是道德的,有些是非道德的;绝大部分是颓废作品。但中国的博士却极力维护这部书,辩解说它遭亵渎神明之手破坏歪曲方才至此。马若瑟很简单地将《尚书》与《诗经》相提并论,称前者描述伟大帝王们的英雄事迹,后者则用诗的形式歌颂同一主题。安文思算是比较详细和客观地介绍了《诗》的内容,他大概是想按照《诗》之“六义”——风、赋、比、兴、雅、颂——来介绍,但不知受什么影响,他说《诗经》内容可分为5类,将雅、颂算为一类,没有赋,而加入佚诗(Ye Xi)为第五类。他说佚诗就是被剔除或分离出的篇章,因为孔子曾审阅这部书并剔除那些他不喜欢或认为难以置信的内容,但佚诗仍然被引用而留传下来。
由上可见,耶稣会士们谈到《诗》是周朝作品,曾经孔子评阅删削,中国人认为《诗》富含隐喻,但耶稣会士发现《诗》的实际内容与此声誉不符,而中国人试图解释这种名不副实。耶稣会士这些认识来自中国一些最通行的说法。《诗经》之诗起于周文王,而“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了然此纲是读《诗》的起点,持此纲领则可以解释耶稣会士所谓《诗》中所夹“非道德的”和“颓废作品”,即变风、变雅。按中国人的解释,文、武之时风、雅兴,成王之时颂声至盛,此为《诗》之正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变风、变雅为“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孔子录这些诗旨在作后王之鉴,“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因而变风、变雅原是“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变风的基本特点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朱熹谈到雅之辞气、音节皆为周公制作时所定,并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后来出现变雅,那也只“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这似乎也是在委婉地捍卫《诗》的价值,暗示《诗》的纲领自文、武、周公确定以来并无实质变化,虽有变雅,仅变事而不变乐,中国奉行礼乐治国,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套解释听起来挺圆满,中国人是习以为常,但耶稣会士显然不大认同。虽然他们经常提到中国人自己如何说,并以此向欧洲人证明什么,但他们本身却难以置身中国的观念系统中来看待中国人的说法,而时不时引入自己的判断坐标。《诗》对他们而言最鲜明的意义或许仅在于,这是一部公元前1100多年时已开始形成的书。
至于《礼记》的来源,安文思说原作者是周公(Cheu cum),但书中也有一些其他人——如孔子的门徒和其他注疏者——的作品。德·马尔绪则说《礼记》是孔子所编。这两种说法都有正确之处,又都不准确,将其糅合起来方较接近中国人的说法。按《礼记正义》之说,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黄帝,自遂皇至周,代有其礼,相互又有继承关系,周公所制为周代之礼,即《周礼》(《周官》)、《仪礼》,《周礼》为体,《仪礼》为履。《礼记》的来历,孔颖达解说非常详细,“《礼记》则总陈虞、夏、商、周”,“其《礼记》之作,出自孔氏。……至孔子没后,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公孙尼子所撰。郑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卢植云:《王制》,谓汉文时博士所录。其余众篇,皆如此例,但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看来《礼记》中有周公所制之礼的内容,但并非周公原作。安文思的说法若让中国人点评,则不是评他将《礼记》与《周礼》、《仪礼》烩为一团,就是责他轻下结论。按孔颖达说法,《礼记》与孔子的关系在于,是孔子的门徒乃至再传门徒根据流传下来的孔子言论编纂而成,因此只能含糊地说“出于孔氏”,到底与孔子有多大关系实在还有疑问,毕竟有众多篇目不能确知所记之人,而孔颖达列出的4位作者中,一出于秦,一出于汉,与孔子之世相隔久远。可见,德·马尔绪说《礼记》是孔子编,可能是一知半解之故;安文思说部分作品出于孔子门徒和其他注疏者,倒是接近权威论断。不过,我们应该想一想,耶稣会士对《礼记》作者到底是真的只知皮毛,还是尽管知道孔颖达这样的解说,却有意含糊其辞,采用折中说法,以便尽量将此书置于古代并归于有威望之人?中国人承认《礼记》的权威性,并不完全依据其实际作者和产生年代,而更在于它是现实生活中所运转之规则体系的重要依据,在于其实际作用,所以中国人可以既明确说明《礼记》非直接出于孔子又依然奉之若圣。但出于种种原因而好古的耶稣会士却不能这么“务实”和“豁达”,在依据一切可见迹象将中国人推崇的东西推及古人和孔子这一点上,他们也许比中国人更急切。
耶稣会士一方面称《礼记》与孔子有密切关系,一方面又对《礼记》评价不高,这种矛盾态度同面对《诗》时的态度如出一辙。类似于《诗经》的名实不符,耶稣会士同样在《礼记》中发现许多无法令他们接受的内容。但这一点只有安文思指出,他说《礼记》中有不少令人生疑、难以置信的内容,应慎重阅读。这大概是暗示《礼记》中的祭天祭祖仪式有偶像崇拜意味。其他耶稣会士虽然言不及此,但他们介绍《礼记》时仅寥寥几笔的冷淡态度也许蕴涵了什么。曾德昭秉持其一贯口吻,笼统介绍说《礼记》论述古人的典礼仪式,也涉及宗教和祭神。李明和德·马尔绪保持了这种客观的口吻,但出口的内容却有主观的调整,他们只说《礼记》是关于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礼仪、风俗、合法典礼、公民义务的书,没谈到《礼记》中有宗教内容,颇有为贤者讳的意味。马若瑟说《礼记》制造了一些礼仪来规范外表的行为动作,但这部书耶稣会士们不易接受。安文思虽揭了《礼记》的短,但也以类于李明等人的笔调强调中国人之所以重视《礼记》,因为它诞生较早且是中国法律、习俗和礼仪的基础。安文思的话已经显示出,成书时间对耶稣会士来说的确是个不可忽略的理由。进一步看,他指明《礼记》中有出自后人的篇章,这恐怕也不只是如实而述那么简单,而是为《礼记》中存在偶像崇拜内容提供理由——乃出后人添缀。
耶稣会士对《春秋》的介绍格外简单,也没有什么评论。耶稣会士们都说《春秋》是孔子编纂,此说不错,“《周礼》有史官……诸侯亦各有国史……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李明补充说由其门徒们评注,这应指《春秋三传》而言。按照一般说法“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又据耶稣会士时代中国尚普遍流行的说法,“公羊子名高,齐人,受经于子夏。……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因此三传作者都与孔门有关,李明称为孔子门徒也无大失。乾嘉学者虽证明《公羊传》出于汉代公羊寿,但已是后事,耶稣会士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的一般意见。耶稣会士说,《春秋》是一部纯粹的历史书。曾德昭言其述中国历史并叙若干古代国王的功业,以资治世,这正如《春秋左氏传序》所概括,“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李明说《春秋》记载了一些国王的品德、恶行和治国格言,此说合《春秋》大义之一,“‘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彰”。
尽管其笔法“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但毕竟书写善恶之事、劝戒后人。德·马尔绪称《春秋》是作为《书经》的续篇而写,这实际上反应出中国的主流观点。从作《春秋》意图来看,孔子以明周公之志自著,作书法旧史遵周公。从时间上看,《尚书》虽然插入关于公元前627年崤之战的一篇,但基本上终于周平王初,即公元前770年左右,《春秋》则始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杜预言:“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11.
三、五经座次
通过上述分析,首先看到耶稣会士在介绍“五经”的起源和基本内容时,无法判明他们究竟祖述何书何人,他们仅仅是反映当时中国士林的通识,而又往往在细节上失真。这使我们有理由推测,耶稣会士在了解中国典籍问题上也类似于了解中国科学,多数人并不曾阅读学习过原典,而是从中国老师或其他耶稣会士那里获取必要信息,甚至于他们的言辞是经过数重转述之后的结果。其实目前能够证实的只是利玛窦曾规定以“四书”为基础教程,指导新来的耶稣会士学习中国文言和正确文体。至于耶稣会士经常挂在嘴边的“五经”,除了几几位曾经翻译过《尚书》、《易》、《诗》、《礼记》片段的耶稣会士,其他人很难被认为当真翻阅过这些经典,阅读这些作品所需要的中文造诣并非人人能得而备之。鉴于这种情况,不难想见欧洲人通过耶稣会士看中国宛如隔雾看花。但这还不够,尽管耶稣会士未必知晓中国典籍真义,另一方面他们却坚持用自己的筛子来过滤中国而后去愉悦欧洲人的耳目。
耶稣会士谈论“五经”时出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他们以“第一”至“第五”的顺序来介绍“五经”,然而每个人所排定的顺序并不相同。曾德昭是首位完整介绍“五经”的耶稣会士,他依据中国人自称的“五经”的诞生次序介绍,依次为《易》、《书》、《诗》、《礼》、《春秋》。但后来的耶稣会士就不同,安文思的顺序是《书》、《礼》、《诗》、《春秋》、《易》,李明的顺序是《书》、《诗》、《易》、《春秋》、《礼》。德·马尔绪综合耶稣会士的介绍后又恢复了《易》、《书》、《诗》、《礼》、《春秋》的顺序。这个排序不尽依照中国人的传统,而且体现出时间差异,它并非随意为之的简单排序,而是一个蕴涵了他们关于“五经”价值判断的等级序列。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顺序介绍“五经”的两部作品,一部问世于礼仪之争爆发前夕,一部诞生于礼仪之争结束以后,而重新为“五经”定序的两部作品都恰好在礼仪之争风起云涌的阶段写作和出版。还应注意到,耶稣会士几乎一以贯之地以自己的标准判断“五经”价值,状其亲疏好恶。前面已经一一提到耶稣会士对“五经”的态度,可以说,他们对《尚书》的口碑一致很高,对《易》普遍有排斥心理,对《诗》和《礼记》在中国享有的声誉颇不以为然,对《春秋》则不置可否。排序和评价两下对比,一者变一者不变,反映出耶稣会士对“五经”的基本态度和利用“五经”的需求长期不变,而其具体表现形式和处理方法则曾受制于礼仪之争。
他们内心关于古书的判断标准其实很明了,那就是这些书与基督教教义的离合程度。在耶稣会士眼里,《尚书》“谈到的政治状况类似摩西和先知们在犹太人中的状况,它也谈到有关崇拜上帝和宗教形式的问题”,它最有助于论证中国古代宗教与基督教同源。相反,《易》是最具危险性的书,不仅因为它迷信,而且因为中国人极度重视,并称其为中国最古老的书,那么中国的古老文明岂非源于异端!《诗》与《礼记》则包含着一些不道德甚至偶像崇拜的内容,因此被耶稣会士质疑。《春秋》是地道的世俗作品,故而无甚可说。耶稣会士对“五经”的真实态度既然是这样,那么最有价值最神圣的书和最荒谬的书同时成为中国人的“圣经”,这种状况也许让他们深感棘手和困惑。然而“五经”的悠久历史在中国不容质疑,至少作为展示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的例子具有很大说服力,因此他们赞扬中国古代文明时又根本无法舍弃“五经”,这成为他们尴尬的症结所在。耶稣会士以基督教立场为取舍中国文献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在分析《中华帝国全志》的帝王事迹时已经揭示出来。如果说该原则在介绍帝王事迹时为隐含性的,那么在评价“五经”时则直白得多,到了第八章将要涉及的古代宗教部分已经是昭然天下。除此根本原则之外,他们的叙述方式还受到礼仪之争进程的左右。
耶稣会士论证中国有不同于欧洲而又古老灿烂的文明,根本意图在于获取欧洲支持他们那种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政策。在没有礼仪之争的压力时,尽管他们对“五经”自有理解,但主要意图是展现历史,因此直接搬用中国人的说法,依问世年代对“五经”排序,既是最合理的,又显得真实和客观。然而礼仪之争干扰了这一进程,它带来的一个现实压力是,迷信/非迷信、有神论/无神论成为敏感问题,中国古书的性质此刻必然要引起关注。于是由“五经”的历史和性质所揭示出的难题就显现出来:中国有古老的文明,而这文明自始就充斥迷信。如果这样的命题成立,那么不独“五经”,对中国上古史的所有论证都因此而成烫手山芋,因为越证明中国的历史悠久,便越说明中国的异端传统根深蒂固,这岂不坏了礼仪之争的大局,也坏了他们适应政策的基础。而若有人因此进一步追问,既然存在这样一种可以上溯至人类之始并自成体系,与基督教社会有本质区别的文明,那么圣经关于世界历史的说法是否还可信,这样就不仅是拆耶稣会士的台,还要动摇教会所宣扬的上帝真理了。
但即使有上述难题,礼仪之争毕竟又不能替代和取消对中国古老文明的论证,何况这些论证殊途同归,都服务于他们的传教政策,耶稣会士或还冀望于这些论证相待而成。耶稣会士显然意识到这种困境并试图寻觅出路。安文思和李明的书中根据他们的价值判断安排“五经”的座次,正体现出他们既要继续利用“五经”为证,又要小心回避中国人重视不健康古书这一事实,同时也强调只有《尚书》才是真正有价值和可依凭的古代文献。不管怎样,通过“五经”座次的略微改动来达成既客观论证中国文明古老又满足礼仪之争的需要,这还是瞒天过海式的被动应战。与之相反,将中国古代历史与古代宗教环环相扣地结合论述,以将中国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在源头上相衔接,则是为了从根本上平息礼仪之争和推行适应政策而精心策划的长期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