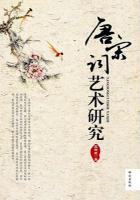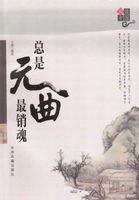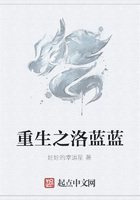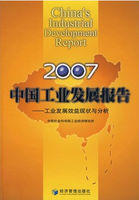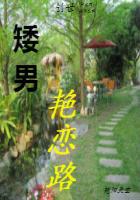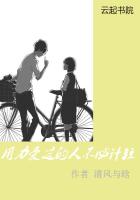文学史,通常是不完备的。
第一,它不可能包罗万象,因为篇幅有限。第二,它是一部很无情的书,同时也是一部很势利的书。它的眼睛只盯着名人和名作,那是让非名人和非名作欲哭无泪的事情,可你也只好没脾气。而且,这部文学史成书的年代越近,其著作者加以评论,予以取舍的功利程度,更多的要掺入非文学的考虑因素,也就越明显。于是,有些假冒的名人,有些伪劣的名作,很可能挤进文学史,在这部书里的哪一页,哪一节,露出那张真小人、假大师的肉脸,作人五人六状。所以,对一百年内的文学史,你最好本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半信半疑地看过去为妥。
至于我讲的这个距今不足百年,既非名人,也非名作,肯定进不了文学史的故事,录以备忘,为文学史的一个注脚,也不无裨益罢了。因为,一部当代文学史,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是一部文人伤心史。在当代历次文学批判运动中,凡在劫难逃者,受到批判而大倒其霉者,那痛苦,无论落到名人身上,还是落到非名人身上,疼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的。
也许这多年来,那张善良的被整得“神气尽矣”的文人面孔,始终在我的记忆中不能磨灭,因此,我对我们中国的评论家,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的评论家,在那个以笔为刀枪,评论与权杖画等号的年代里,对于作家体无完肤的“爱护”,对于文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就忍不住愤慨。尽管很多置人于死地的评论家,已经亡故,或者,即使活着,也风烛残年,但想起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总是怀疑民谚所云,“不是不报,时辰不到”,其实是一句空话。
那是1945年8月,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我军,也就是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进入了张家口市。当时,远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接管北平为第一要务,哪里顾得上远在口外,盛产口蘑的张家口。于是,在蒋介石鞭长莫及的缝隙中,于敌后坚持抗日八年的共产党政权,有了第一个像点样子的城市。我在短篇小说《月食》中,写过这些即将进城的干部,那种欣欣然,那种对于美好将来的向往。
这样,张家口这座其实不大的城市,有过两次解放的经历。自然,在八路军中吃小米饭的文化人,也就随着部队进城。这其中,应该有刚以短篇小说《我的两家房东》脱颖而出的康濯,有后来写《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的萧也牧,以及我要讲述他故事的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丁克辛。那时,他们都很年轻,二三十岁,精神焕发,情绪高涨。
我在想,命运要是给丁克辛展开一点笑脸的话,评论家(特别是身居要位的,掌握文艺方向和政策的)不那么神经过敏、小题大做,不那么过犹不及、杀一儆百,尤其,不以作家首级为自己晋身之阶,此人,本该是解放区的一流作家,或者,退一万步,至少会写出不亚于解放区那些名家的作品。他比较早地跳出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简单化的写作定式,是比萧也牧,起码要早好几年的写个性、写人性、写感情、写男女之爱的老区作家。因此,早得多的遭遇到评论家的“光顾”,便命中注定了。于是,我也不由得哀叹,老天总是偏护强者,而欺侮弱者。对整人的人,“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使其逍遥法外;对被整的人,“时辰一到,一定要报”,绝对不会放过。
丁克辛成了评论家的靶子。
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篇文学作品被点了名,对作家来说,有点像剑侠小说中,被武林高手点中死穴一样,顿时昏厥麻爪,立感天日无光,眼前一片漆黑,下场不敢想象。这种痛苦莫名的体会,不佞也是亲身感受过的。甚至到了解放以后,都在铁道部系统工作,有机会认识这位丁克辛,早年被整肃过的惶惶然,还时不时在他脸部阴影中流露出来,这你就不得不感叹,评论一旦等于权杖,是多么可怕了。
坦白讲,我也是侥幸活到七十出头的人了,虽然被评论的权杖,打得七荤八素过,但贱命之人,倒也耐得作践,至今仍在文坛厮混。不过,在夜里做身陷恶狗村的噩梦,倒是永远不变的主题,说明那些年里权杖式的评论,对于作家威慑力之深远,保质期竟达好几十年之久,到达下意识中,至今,每一念及,犹不寒而栗。估计这被狗狺狺然吠叫出一身冷汗的梦,非要做到死不可了。
可我为丁克辛抱憾的一点是,那么早就被批了,那么早就挨整了,从此,一生的写作魂魄散了,但解放以后,他还想振作,1950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丁又写了《父子英雄》,发表在《人民文学》,结果被那时一言九鼎的周扬扣上“个人英雄主义”,再次跌落到谷底。由于在张家口对他的批判,传播的范围,充其量,仅仅是晋察冀边区而已,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周扬的批评,又是他点的一串名中最后一个,小拨拉子而已,既达不到延安时期对王实味《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那样影响巨大,“青史”留名的程度,也不及建国后历次文艺界的批判运动那样大张旗鼓,家喻户晓。虽然臭得从此抬不起头来,却没有遐迩皆知的臭名,有点冤。
加之,腾出手来的傅作义,开始包围这座城市,很快我军就撤出了。于是,丁克辛在张家口的这一段文学经历,也随着城市的易手而尘封起来,再也不被触及。现在,除了熟知者外,无人了解丁克辛的这段往事,甚至连他后来的去向,也少有人知悉,更不知道应该有八十多岁年纪的他,仍否健在?现在回想起这样一位被文学史淡忘的作家,那怆然若失的眼神,那无可奈何的表情,真是很伤感的。
一个有才华而不得施展的文人,不甘沉没却又只能赍志饮恨地活下去,那是多么艰难的岁月啊!
现在可以想象,这些穿着二尺半长的灰布军服,裹着绑腿登着布鞋的知识分子,随着部队进入城市,走在平坦的马路上,那种自豪感是不用说的,甭提有多少的诗情画意,涌上心头了。很显然,对那些一直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共产党、八路军来说,需要熟悉城市,熟悉工厂,熟悉工人阶级,那么,得风气之先的文化人,又是刚经过整风运动,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自然以深入到群众中去,体验新的生活,接触新的人物,寻找新的素材,创作新的作品,为当务之急了。
丁克辛到了宣化龙烟煤矿,他没有想到在那里写了他一蹶不振的作品《春夜》。前年我编《五十年短篇小说选》,选过萧也牧那篇让他一劫不复的《我们夫妇之间》,为他写“作者小传”时,知道他那时也在张家口铁路站段,当工人纠察队的队长。可以想象,当时有很多文化名流,知名作家,文工团的表演艺术家,聚集在张家口。才子风流,士女妩媚,歌声嘹亮,舞姿婀娜,可谓人杰地灵,极一时文气之盛。顺便要提一下的,康濯时任副主编的《北方文化》杂志,也是在这座城市中出版发行。现在,谁要拥有这本战火中的文学杂志,肯定是奇货可居的珍藏之物了。
1947年,丁克辛在《北方文化》上,发表了他深入龙烟煤矿写出来的短篇小说《春夜》。
如今,当我们能够以文学角度探讨文学作品的时候,平心而论,丁的这部描写矿工感情生活的作品,实在构不成任何罪状。你得承认他写得真实,你得承认他写得别致,你得承认他的小说具有文采,最后,你得承认他这篇作品的主题的积极性。当时,解放区文学,很多还停留在配合任务,图解政策,宣传形势,教育群众的阶段,因此,在当时许多意识大于形象,政治大于文学的作品中,他的这篇《春夜》,别开生面,一支独秀,风靡一时。
故事讲述了那些在矿主的盘剥压榨,在把头的欺凌蹂躏下的下窑矿工,旧社会穷得连媳妇也娶不起。贫穷与落后,落后与愚昧,愚昧与无知,无知与罔顾羞耻,总是相伴相行的。于是,作品描写了矿井中,坑洞里,出现了类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述及的发生在原始社会的“普那路亚婚”。一个同样穷得无以为生的女人,成为同住在一个窝棚里多个走窑汉共有的妻子。
但是,共产党的光辉照亮矿山的同时,也给矿工带来了新的世界,在随后的民主改革运动中,这种悖谬人性的婚姻,无论一夫多妻,还是一妻多夫,都是解放区法律所不容的。于是,在工作队的帮助教育下,这个女人与其中她更喜爱的一个老实男人,组成家庭,过合法夫妻的生活。这就是在那个还很冷冽的北方春夜里,重新得到人的自尊的这对男女,相亲相爱的故事。
我在编五十年短篇小说集期间,希望能找到这篇《春夜》,可惜,未能如愿。但据当时阅读过这本杂志、这篇小说的朋友告诉我,这是对他进入文学之门的一部启蒙意义的小说。他还告诉我,当时,懂得一点文艺政策的人,知道一点延安整风的人,都为作家大胆的文学追求,捏一把汗,为他写人之不敢写的勇气,担一点心。因为大家都很聪明,按照中国人的中庸思维定式,迈出一小步,其他人也许尚可忍受你的激进,迈出一大步,而且触动了什么,影响了什么,妨害了什么,那就必然要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即使你既不触动,也不影响,更不妨害,握有权杖者,和握有权杖之笔者,看你不顺眼,看你太个别,看你走出队列远了一些,等着吧,肯定会有好果子让你吃。
接下来,丁克辛所遭遇到的,便是大家可想而知的事了。就冲这一条责询――在解放区,有那么正面的、健康的、光明的、积极的东西不写,偏要把目光盯在矿井里七八个男人共娶一个老婆的故事?这是为什么?我想他肯定瞠目结舌,回答不上来。后来,我认识了他,一直想跟他探讨,他的这个构思,最初是不是受到高尔基《二十六个和一个》的启发?但经过多次批判的他,“曾经沧海难为水”,竭力回避谈论文学。
文学,成了他的禁忌。
当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文学批判史。其实,我在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从西方文学引进“评论”这一种文体,与中国传统的《文心雕龙》式、《诗品》式的经典评论,以及李卓吾、毛宗岗、金圣叹式的点评式的随机评论,其目的,是要将评论和创作,构成平行的,缺一不可的,文学之车上的两个轮子。无论胡适、陈独秀,还是鲁迅、刘半农,都没有打算使评论相当于检查官的公诉书,使评论家扮演作出终审判决的法官那样的角色。
评论家和作家,有其天敌的矛盾一面,但也有互为因果,彼此推动的共生一面。新文学运动早期,文坛活跃状态的形成过程中,作家和评论家的互动,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也与“五四”以后的大部分文人,其学养,其教养,其素养,其涵养有关,他们程度不同地在身体力行着这个初衷。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五四”时期,那大家风范,真是令人怀念。
以鲁迅为例,作为一位作家,他被别人评论过,作为一位评论家,他也评论过别人。尽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论争史,说到底是一部文人打架史,尽管鲁迅打别人的时候,可谓“一棒一条痕”,相当地不客气。同样,别人打鲁迅的时候,也是“一掴一掌血”,相当地不服气。所以,鲁迅在论敌的挑战下,硬译了好几部外国理论著作,以充实自己;同样,他的对手如陈西滢,如梁实秋,如林语堂,也由中而西,由西而中,积累学问,以便对阵。
即使这样,鲁迅的“丧家的乏走狗”、“洋场恶少”、“四条汉子”……诸如此类的评论,对某些作家起到“定谳”的作用,但评论就是评论,评论只不过是评论,如此而已。与落在丁克辛头上,落在萧也牧头上,落在五十年代“右派作家”头上,那一篇篇血风腥雨的声讨,有着天壤之别。鲁迅的文章再厉害,对手詈其为“绍兴师爷”的刀笔,有置人于死地的“歹毒”,又如何呢?未见鲁迅将谁关起来,给谁戴上帽子,把谁送去劳改,宣布谁的作品为毒草。这也许是新文学运动早期,先是北平,后是上海,出现的大活跃,大进展,构成今天我们称道的现代文学的大繁荣。不能不看到二三十年代,作家和评论家的碰撞、冲激、互动、砥砺,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文学的自由气氛,作家的平等精神,争论的民主风度,宽容的思想境界,是古往今来,文学得以繁荣昌盛的起码条件,文学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后来人以史为鉴。
我不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界,是以什么为准?那是史家的课题了。但窃以为,从文学评论,具有决定作品生死,决定作者存亡的权杖作用起,只要这个最鲜明的批判特色存在,便是当代文学。因此,丁克辛在张家口的这段经历,虽然发生在解放前夕,与更早一点的,于1943年延安整风对丁玲、王实味的批评,基本上已经属于当代文学的先声。因为,那手法,那动作,那措施,那政策,在近半个世纪里,没有什么改变。后来,我也渐渐懂得,为什么后来有那么众多的喊着不破不立,实际光破不立的勇敢者?因为立,需要学识,需要经验,需要实践,需要真知灼见,比较麻烦。而破,是一件无需乎学养、教养、素养、涵养,很容易做到的事,只要有权;哪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权,可是能在评论中“左”得可怕,“左”得吓人,只要不在乎别人眼中自己的那面目可憎的形象,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评论的权杖作用,发展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达到顶峰。江青为姚文元正告天下,他是我们党的“金棍子”,结果,和这根金棍子一起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没完没了地破下去,一直破到中国成了一片文化沙漠为止。评论等于权杖的美好日子,也就走到了头。谢天谢地,文学史上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故事讲到这里,不禁呜呼,真为最早倒在评论权杖下的丁克辛、萧也牧之流抱屈,如果他们减去五十岁,给他今天这种写作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我想,他们会万分珍惜,绝不会写时下流行的拆烂污文章、下三烂的作品,这也是经过严冬的人,定会把握住明媚春光的必然。
不过,我也替他们担心。虽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评论家最光辉,最得意,叱咤则风云变色,跺脚则地动山摇的权杖时代,一去而不复返;但评论家与物质利益挂钩,与商品经济挂钩,与五张老人头或者十张老人头的红包挂钩,与赤裸裸地讨价还价,要么上床,要么付费的交易行为挂钩的时代,正堂而皇之、毫无顾忌地到来;这两位老同志能适应么?
我不知道,吃供给制的、口袋里只有几张边区票的丁克辛、萧也牧,是不是打点得起当下那些要桑拿、要小姐、要KTV包间的评论家?
擅长写什么,不擅长写什么,你能够写什么,不能够写什么,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有的人,一出娘胎,就基本上定型了。即使求新图变,也不是吹一口气就成的事情。更有的人,一开始写,便是镜头一般地定了格,无可救药,只能永远依样画葫芦,直到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