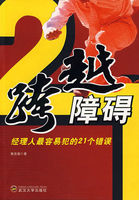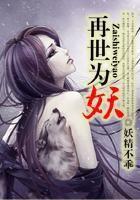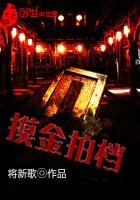余秋雨这个名字似乎从来都没有寂寞过。从文化大散文的走俏,到被后起的文化学术明星们指摘为****余孽,从被荣耀的光环笼罩下的作家学者,到两次对簿公堂的原告,余秋雨以自己的不寂寞一直荣幸地成为文坛瞩目的焦点。
平心而论,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的确开辟了中国散文的新境界,这从早期有关他的评论可以看出来。但为什么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的余秋雨先生,会屡屡成为诸多批评家的批判靶子呢?
在考察了有关的所有批评文字以后,我发现余秋雨之所以成为不能安静的学者,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学术文化明星身份。如果余秋雨能够一直以一个真正的学者的心态来面对批评的话,他不该也不会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二是拒不认错的执拗性格。余秋雨一直没有勇气承认余杰等人对他的批评,也不承认古远清等对他的文章的贬斥,更不承认萧夏林对他的人格指摘。这些都说明余秋雨的不肯轻易承认错误的执拗性格。考察所有批评余秋雨的声音,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余秋雨自己对此似乎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批评我的就是两点,一个是历史问题,一个是差错”。
在戏剧舞台,名角都有头牌欲,我以为余秋雨多多少少也有这种欲望。正是这个累人累己的头牌,让他一直处于各种事件的漩涡中心。在头牌欲的驱使下,余秋雨一直执拗地努力着,试图建立一个崇高的形象,可惜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一,从“记忆文学”和所谓历史问题看余秋雨的矛盾心态考察余秋雨头牌欲望下的执拗性格和矛盾心态,我们不妨从他所谓的“记忆文学”和历史问题说起。
《借我一生》被余秋雨命名为“记忆文学”,作品首先在老牌名刊《收获》
部分连载,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据余秋雨说“这本书里写到的,全部可信”,但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记忆文学”的主观性:“我强调这个作品的主观性。在这本书里我不是历史学家,不能总结(“****”)这个历史过程”。这里就有了一个矛盾,作为主观记忆的《借我一生》到底可不可信?到底全不全面?
从余秋雨的话中我们读解出来的是余秋雨只对自己的主观记忆负责,他拥有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权利,因为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为“我强调这个作品的主观性”。如果是这样,余秋雨更应该强调《借我一生》的文学性,而不应该过分宣称它的真实性。
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出余秋雨的性格矛盾来,他总是给我们一种遮遮掩掩“欲说还羞”的感觉。关于《借我一生》是否真实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按照余秋雨的说法,《借我一生》是他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所知的经历。但《新京报》刊文说《借我一生》有很多地方不真实,“比如他说自己是编教材,什么是教材编写组?我们学校去了好多人,那是去编《辞海》,并不是与余秋雨相同的‘编写组’,他们没有一个人回来受清查、复查的”。
也许正如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所说的那样:
“余秋雨《借我一生》所述的记忆只属于他个人,作为历史事件,总是有许多人共同经历过的,但各人对事件的表述却必然不完全一样,因为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所处的地位、视角及所经历的片断各不相同。人们在表述这事件时,所表述的不仅是事件本身,而且在表述过程中赋予事实以一定的意义,故每个人对事实的表述都具有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包含着个人的价值判断、伦理判断、感情、利害关系和他的审美判断。所以当事人判断不可能做到完整而又真实。”
由此看来,余秋雨所宣称《借我一生》里的真实也只能是他自己的“记忆真实”了。这种真实毫无疑问是一种伪真实。
余秋雨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存在什么历史问题,许多人都有一个疑惑:余秋雨到底参没参加过“石一歌写作组”?他到底有没有写出什么粉饰******的文章?
《新京报》记者张弘在他的采访手记中说,在余秋雨身上,我看到了他的复杂性。总的印象是,一方面,他对于种种批评、指责有着深深的无奈;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之间,总想把过去已经发生的那一段历史隐瞒起来,或用自己的文字来进行“修正”。
也许张弘的感觉是对的,余秋雨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一直就是这样。我觉得对余秋雨应该两面看:一是他确实参加了“石一歌写作组”,所以他一直想隐瞒一些东西;二是从目前所能够发现的材料来看,余秋雨确实没有写出什么“粉饰”******的文章,他所发表的那些文字基本上还是属于正常的学术文化范畴之内。清查工作组当时给余秋雨下的结论也是“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因此我们对他应该宽容。
余秋雨的历史问题不能说没有个人的恩怨在里面,余秋雨自己曾经三次上书******,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余秋雨的问题还遭到了清查小组三番五次的复查,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陈恭敏在谈到余秋雨被复查的背景问题时说:
“复查与老干部的反映有关系,所谓“讲清楚”到底讲清楚还是没讲清楚,当时我认为他是属于没讲清楚,而且他是重点,否则为什么要复查他一个人?他在学校里的影响太大了,工军宣队都很重视他,他已经是党委了。那个时候教师里面他是唯一一个党委委员,工宣队一直对他很器重。”
对于学校的复查,余秋雨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事情。也许这是实话,因为复查工作当时完全有可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对于当事人,可能完全是个秘密。但是余杰和古远清对余秋雨的指责也不是空穴来风,据说他们手头上确实掌握着一些可靠的“清查材料”,而且这个材料来自某个清查积极分子之口。
但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余秋雨在参加上海****写作组期间可能确实没有做出“出格”的事情,他自己说“我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只在******、******主政期间为复课编过一点教材,写过几篇学术论文,尽管质量不高。”我想这也许就是余秋雨之所以遮遮掩掩的理由之一,对此有许多人不能理解:“这不是你能遮掩得住的,因为了解的人太多了,大多数人还活着。”
对于传媒对自己的攻击与质问,余秋雨曾在《南方周末》给予还击,包括以上两个问题在内,余秋雨说了一些解释和反诘的话。在我看来,这些话说得相当“愚蠢”,看完了这个长篇“说话”,我的直觉是余秋雨又在真诚地作秀,试图重建自己的崇高“头牌”形象。
平心而论,余秋雨质询传媒发出自己的“七问”不是没有道理,这几年传媒在对待余秋雨的问题上,的确存在着让余秋雨感觉十分委屈的理由。在质询最后,余秋雨说:
“我今天的质询也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反弹,我不会在意他们,却会密切关注他们活跃的平台。如果我们的文化传媒永远这样下去了,那么我今后连这样的质询也不会提了。”
这一点余秋雨很聪明,但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根本不该在抛出《借我一生》的敏感时期,在《南方周末》上说出这些话,这只能让读者感觉余秋雨还是不能离开炒作和作秀。也许对于余秋雨而言,这个时候最好的质询方式就是沉默。尽管这有些委屈,但总比让读者感觉自己在继续作秀强。而且从余秋雨此后对待朱健国对他的发言来看,他也并没有做到真正沉默。余秋雨说出了一些不很厚道的话。比如在评价别人对他的批评时他说:
“我很清楚有些人在写文章骂我,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想对我好的人,如果我去拉拉关系,就什么也没有了,可是作为文人,我不能那么做吧。例如湖北的那位古先生,他对我的吹捧已经到了世界上都少有的地步呀!我拒绝这种吹捧,不久他就开始骂我。还有北京的萧编辑,大学毕业刚工作,在电话跟我说什么“中国文人里面我最讨厌的是王蒙和王朔,最佩服的就是张承志、张炜和你余秋雨,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之类的话。我说王蒙是我的朋友,王朔是很好的作家,你刚刚从大学毕业,不要这样看问题。后来他就开始骂我!我想了很久,发现这个现象就是国外的‘破坏心理学’。”
这样的话从余秋雨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文化明星的口中吐出来,真是让我们汗颜。且不说这样的话所具有的隐私性质,就是公开披露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这样,只会让读者感到余秋雨这位学术文化明星的“不厚道”。
二,从“挂牌”大师透视余秋雨的“头牌”欲望
余秋雨的头牌欲更为突出的表现是他竟然“荒唐”地同意上海市教委成立“大师”工作室。
我们先来看上海市教委为其“挂牌”大师的理由:
“余秋雨先生早在三十年前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独立自主地着手建立全新的世界戏剧思想史、中国戏剧史、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一系列基本学科,所编写的著作和教材长期被很多高校使用,并获得了全国和上海市的多个最高学术奖项。近二十年来,他又以亲身历险的方式走遍了中华文明和人类其他古文明的遗址,具体而又雄辩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生命力及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在阐释过程中,他又创造了“文化大散文”的文体而开启一代文风。近十年来,他不断地应邀在美国各大名校、国会图书馆和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演讲中华文化史,还通过电视媒体向国内民众讲授,产生巨大影响。总之,余秋雨先生是一个集“深入研究、亲自考察、广泛传播”于一身的完整型文化学者。他在历史转型期出色地承担起了守护和解读中华文明的使命。多年来他在国内外获得极多奖项,还被全国网民投票评为“2007全国十大学术精英”第一名,又被亚太测评系统评为‘影响世界一百年的百名华人’。”
对这样一段夸张溢美之辞,我们暂不置评,只先来考察一下余秋雨这个“大师”的头牌神话是如何一步步架构的?总的看,余秋雨“大师”的架构过程先后经历了“三个苦旅”阶段:一为学术苦旅,二为文化苦旅,三为作秀苦旅。下面分而述之。
1.学术苦旅
多数人都很了解余秋雨的文化明星身份,但对于他此前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并不熟悉,可以说余秋雨在成为文化明星之前曾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段学术苦旅生涯。这个阶段以戏剧研究为主要标志,应该说此时的余秋雨(不包括****写作组经历,事实上那时余秋雨的文章也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是比较踏实的,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学者的严谨。
余秋雨早期的艺术理论著作,也不是没有得到过学术界的承认,只不过相对于后来的文化大散文来讲,要寂寞得多。他在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的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由此可见,其学术研究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
余秋雨学术生涯之所以没有像今天这样红得发紫,一方面是学术工作本身的冷清,另一方面也是他所从事的专业所限。戏剧研究相对比较偏僻,恐怕只能在行业内为人所知,要想走向大众,文化大散文的路子不啻为一条捷径。余秋雨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可能。这一点从余秋雨“参加”****写作组可以得到证明。谢泳也说:“余秋雨生活的时代,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想要出人头地,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现成的道路,这个道路我们姑且称为是‘两个小人物的道路’。这两个小人物就是五十年代因批评红学家俞平伯而成为学者的李希凡和蓝翎。”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对一个在文史和写作上有才能的青年来说,他们都希望能走一条“两个小人物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简单说,就是有强烈的企图在一夜之间成名的渴望,所以他们通常选择的心理动机都是以能让最高领袖突然认可为旨归的。恐怕这也是余秋雨为何要(被动?主动?)加入****写作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他后来选择文化散文明星学者的路子,也和这样的心理有关。谢泳说余秋雨看起来是一个什么好事都赶上了的人,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又可以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他总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妥协,这是他的最大优点,也是他的最大局限。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当代”的作家和学者,不大考虑“未来”。
2.文化苦旅
这个阶段是余秋雨成长的最为关键的时期,可以说没有“文化苦旅”就没有余秋雨的“今天”。这个阶段以余秋雨在《收获》开设“文化苦旅”专栏和出版《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文化散文著作为主要标志。
从余秋雨学者角色到作家角色的转变来看,《收获》杂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那时巴金老人还担任着这本杂志的主编,《收获》因此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崇高,可以说是最权威的纯文学期刊了。不过巴金年事已高,杂志具体工作由其女儿李小林先生主持。余秋雨那时的身份还是学者,《收获》为何会在当时选择他在杂志上长期开设专栏呢?
现在看来,余秋雨“文化苦旅”专栏的开设真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彼时学者散文写作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收获》要开散文专栏,余秋雨被选择可谓是占了天时;其次,《收获》杂志在上海办刊,余秋雨则在上海戏剧学院,由上海学者在本地大刊上开设专栏正可谓占了地利;第三,据余秋雨自己说,他和李小林是大学同学,同窗之谊不仅仅意味着近水楼台,更意味着相互了解,知根知底,容易促成专栏的开设。因此余秋雨在《收获》
杂志上开设专栏,又可谓是占到了人和。
文学大刊《收获》的作用不可小觑,出版的打造更是威力无比。有了发行数量庞大的《收获》专栏的铺垫和渲染,加上时代氛围的需要,余秋雨系列文化散文的热销与流行一点儿都不令人意外。
有人说,“余秋雨现象”处于20世纪最后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急功近利病的爆发期,有很大的传染性,是全国上下“一切向钱看”在学术领域里的一种产物,它有市场,能欺瞒人,能名利双收,所以才会畅行无阻。
此说法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余秋雨“文化苦旅”流行的背后,还有不明就里的吹捧文字的推动。随便举个例子,在这些文字当中,就有笔者的一个朋友的“推动”,他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因为看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就写了一篇极力称赞的文章《大中华的文化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印象》,并在本校学报上发表。之后,这篇文章又被当年的《新华文摘》转载。于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这个命名随着这篇文章以及其他研究文章的传播被学术界广泛知晓。虽说一篇研究文章可能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此文毕竟传播广泛。直到现在,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余氏散文所显现的中国当代散文的大灵魂、大气派、大内蕴、大境界”以及“余氏散文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等等论断,还不时被作为余秋雨的一个标签。
总之,经过几轮的“吹吹打打”以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终于被广为传诵,并风行一时。
3.作秀苦旅
这年头,一味吹捧能让一个人广为人知,但并不能让其大红大紫,要想达到红得发紫的地步,必须要有争议,要论争,甚至还要对簿公堂。余秋雨成长的路线图就大致如此。当然,后来发生的一切也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但因为此前对余秋雨的过度“拔高”,直接导致了这之后一系列论争的产生,直至诉诸法律。余秋雨因此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了一段法律(论争)苦旅。考察余秋雨的这一段苦旅,有四个人最为关键,即萧夏林、余杰、金文明、古远清。
萧夏林是《北京文学》的编辑,也是一位耿直的知识分子,看不惯文坛上那些蹦蹦跳跳的两副面孔的人,他为此主编了一本批评余秋雨的书《秋风秋雨愁煞人》。萧夏林因为在文章《文化中的文化》中提到余秋雨“为深圳扬名,深圳送他一套别墅”而“惹怒”余秋雨,被其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而余秋雨此后状告武汉学者古远清的案件又成为其一系列所谓维护名誉和版权官司的“诉讼表演”。从此,余秋雨借助于法律(由此借重媒体的宣传),更加推广了其全国知名度,向着更加大红大紫的方向一路狂奔。
一方面是主动对簿公堂,另一方面是被动应战,此时期的余秋雨可谓是全面出击。围绕余秋雨****期间的“历史问题”,以及余秋雨不忏悔的死硬态度,那时被标榜为“精神界战士”之一的余杰对余秋雨痛下“忏悔”杀手,掀起了热闹一时的“二余之争”,在客观上为余秋雨的神话创造做了不大不小的“贡献”。此外,还有金文明一本22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引爆了余秋雨散文中126处文史差错,这是第一本全面梳理和考察余秋雨散文文史错误的专著。据说,为了这本书的出版,金文明先生当时费了不少周折,因为余秋雨的名气太大,出版社都不愿意惹这个麻烦。书稿送给上海某出版社时,遭到拒绝,以后又连续遭到了六家出版社的拒绝,直到最后找到山西书海出版社才见了天日。由此可见余秋雨“大师”的威力。
此外,余秋雨借助“自传”(2004年)、“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2005年)、“获选中国十大学术精英”等契机,不断引起争议,其“大师”塑造的神话速度像中国铁路一样一再提速。
纵观余秋雨神话的全过程,作秀之旅差不多贯穿了他的所有“旅程”。最典型的当然要数其在青歌赛的“秀场”表演。余秋雨每次在电视上露面,几乎都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不管是争议还是吹捧。电视上的余秋雨侃侃而谈,展览会上也有他的身影,他对着雕塑作品、摄影作品、绘画作品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就连他的搬家,也会有电视台跟踪报道。余秋雨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挑战大众的审美疲劳。
更让人明显感到做秀的还有余秋雨的一再“封笔”之说。据网友统计,余先生至今已经有过三次宣布封笔的不凡经历了,第一次是他宣布不再写关于戏剧理论和美学研究的著作,要走出书斋,踏勘文化现场,触摸文化余温,建构文化人格。第二次的封笔宣布让余先生毁誉参半,声讨之音此起彼伏。他宣布《千年一叹》之后不再写散文,从此再也不为盗版集团做义工。谁知后来余先生去了欧洲一趟,《行者无疆》又雨后破土,隆重推出了。接着他又一鼓作气翻炒出了《笛声何处》,还创造性地出了一本“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余秋雨说这是他最后的文章,此后将永远地告别文坛。大家怀着无比悲壮的心情购买了这部带着最后的“余温”的大作,同时也都在心里嘀咕,这回该是真的了吧?哪里想到不久以后余秋雨又要把在电视上做节目的讲稿拿出来出版。无论如何,“大师”是有标准的,最起码应该有一个底线。武汉大学原校长、教育基金会会长刘道玉认为,衡量“大师”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是“巨大成就”,这显然不是指一两项发明或几本著作而言,非“著作等身”或“学富五车”的学者是绝不可能企及的;二是学术成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人所宗仰,不是一部分人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所景仰。具体来说,大师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学术上博大精深,博古通今,是学术多面手,重要学术著作丰硕;第二,要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其成果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革命性作用;第三,必须是一个学派的首领,桃李满天下,拥有众多的拥戴者;
第四,作为大师不仅学问高深,而且道德、人品堪为人师,对后人具有楷模作用。
按照这样的标准,真正能称之为“大师”的季羡林先生生前却坚决要求摘掉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大师、泰斗和国宝。他说,自己不是研究国学的,充其量只是个国学小师,所以这些称谓对他都是不实事求是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高尚品格和君子之风。也许,季羡林先生对炒作“大师”实在是看不惯了,所以才表明要摘掉人们给他戴上的三顶桂冠。
对于挂牌“大师”,据说余秋雨也谦虚过,但最后还是半推半就地“从”了。与季羡林先生的低调相比,余秋雨被“挂牌”为“大师”更像是一场众声的喧哗,真正的大师往往是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经常处于舆论喧嚣之中的往往不是什么“大师”。在“大师”稀缺的年代,靠挂牌是挂不出大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