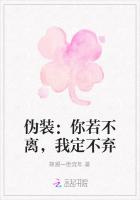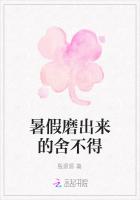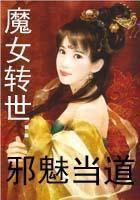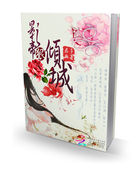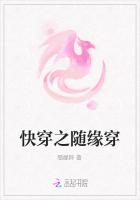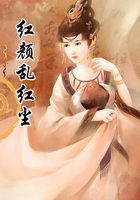诗歌精神的重建――一份提纲
我们正在重建诗歌精神。
这不是由于某种使命感,某种设想或者研究思考的结果。
我们已置身于另一时代。
过去时代的诗歌精神,一言敝之:呐喊。鲁迅,是过去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呐喊,作为那个时代的主调,作为一种狂飙突进的,青春朝气的,号角般的,英勇悲壮的,爱憎分明与中国政治生活相濡以沫的浪漫主义,造就了许多杰出的歌手和黄钟大吕之作。它最终声嘶力竭成为单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在七十年代走到终极。作为自己时代的逆子,北岛们是那时代最后一批诗人。
北岛们的作品因充满暗喻而朦胧,这与其说是基于一种先锋意识不如说是一种中国式的幽默,是他们与自己时代相知甚深的结果。“我不相信!”最后一声呐喊,悲壮而引人注目。
中国五四以来的新诗,到北岛们可以看成一个连续的时代,以呐喊为基调,经历了建立――肯定――衰竭――否定的过程。
研究一个时代的诗歌,应当分析它的语言。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客观、公正地把握住时代诗歌的精神。过去七十年诗歌的语言,完全适合于呐喊。
过去时代的诗歌,其结构是单向选择的、封闭的、垂直的、判断式的(是或者不是,批判或者歌颂,怀疑或者肯定等等。)其创作心态是指令性的,当局者式的。其修辞方式与辞汇随时代政治生活的变化从一极滑向另一极;明喻或者暗喻,直抒胸臆或者曲折隐晦;光明向上,健康明朗、积极热情的或者黑暗激愤,忧郁悲哀、诅咒怀疑的。其语音层往往韵律齐整、响亮,用得最多的是洪声韵。标点符号,无论标出与否,最大量使用感叹号。(以上根据对《写作范文丛书?新诗歌卷》、《五人诗选》、《中国新诗选》等书的研究统计。)过去的时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我们以下一代人的眼光去挑剔它,自然会看出许多荒谬可笑之处。例如笔者对它的诗歌语言的分析,在当代诗人看来,似乎是一种讽刺。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整个传统诗歌的背景上去考察,它无疑是最革命,最富于先锋精神的诗歌。正是这些诗歌,正是它们七十年来时而悲壮,时而激愤,时而乐观,时而庄严,时而滑稽,时而恐怖的呐喊,方使中国新诗,有了坚实的根基,得以在庞大无比的古典诗歌之旁立稳,得以沉静下来,成熟起来。
新的时代,正是它的深处呈现出一片伟大而庄严的静穆。
但至少在表面,过去时代的影响并未完结,仍然支配着人们的诗歌观念,这种支配,恰恰不是形式上的,已经无人问津的诗歌写法这类的东西,恰恰正是那个时代渴求轰动效应,把诗作为“教化”工具,以“兼济天下”的历史惯性,暗中支配着一大批诗人――年轻或不年轻的诗人们的“探索”、“先锋意识”。面对新的时代,面对将来那陌生的、难以预测的岁月,诗人们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和巨大的失落感。诗人们悲哀地看到,往昔的理想主义,道德观念,审美经验,乃至生活方式都与那时代的英雄面具一起,日益成为一些再也难以依附的泡沫,时代从天上回到了地下,窗子打开了,世界的风吹进来了,千千万万的生命欢欣鼓舞,人欲横流,这时代似乎坠落了。习惯号令众生的诗人们,骤然间失落了自己的号角,纷纷落水。他们拼命想抓住随便一块木片,以支撑自己日益下沉的缪斯。时代的开放暂时成全了他们,诗人们纷纷逃向从前被囚禁的大师们的阴影下,寻求那种永恒的诗的净土的庇护,在此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着人类审美经验的认可,在此地俯拾皆诗,一根鹅毛就可以浮起来。又安全,又高雅,又时髦,又现代,又深刻,又吓人,诗人们在过去时代诗歌精神的“高尚与纯洁”压抑下的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自卑感,迅速成为一种偷吃禁果,“自甘坠落”的快感,于是寻根诗、文化诗、嬉皮诗、翻着精神病学写自白、存在主义、人类末日、荒涎、西部牛仔、流浪……一时间热闹非凡。这一切如果说是代表了时代的潮流的话,那么,它们恰恰代表了一种逃避时代,对已往审美经验的盲目追随的潮流。这些表面看起来是对传统深恶痛绝的东西,实际却是对诗歌传统最恶劣部分的模仿。这些东西试图让读者背弃自己的生命,背弃自己已置身其中的生活,成为白日梦者。去相信只有过去的、遥远的、神秘的、原始的、古典的或西方的,不可企及的东西才是美的,诗的。因而日常生活总是灰色的、丑的、非诗的。过去时代的理想主义,被这些诗人弄得面目全非,俗不可耐成为一些苍白无力的白雪公主、流浪汉和嬉皮士们的闹剧。这些诗作由于完全缺乏内在的精神气质而充满着小聪明的、油腔滑调的文化实习证、读书心得、注释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结构松散、毫无才气、胡乱拼凑一些意象积木,五光十色却不见生命迹象,反而把诗人们心急火燎的功利欲暴露无遗。这些东西当然无力影响读者,因此受到冷落,这正是中国诗坛一段时期自生自灭,无人理解的原因,真正倒霉的是诗人这一称号,比起“作家”来,它贬值了许多,在当代中国,在一些场合,诗人,乃是指一些罗曼帝克的,玩世不恭的,言必西方,性死亡、人类末日之类的,神经质的,动不动要自杀或者出走流浪的,喝咖啡的,玩深刻的,故作多情的,不值得与之交往的可怜家伙。
过去时代已经成为传统。然而,如果传统这种传诸后世的惟一方式,只是追随上一代的方式,盲目或怯懦地拖住上一代的成就不放,那就应该断然抛弃“传统”。(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我们时代的诗歌精神,可以说是一种使命。
重建一种新的诗歌精神,远比对一个时代已经确立的东西进行反动要困难得多。诗人既要面对大批旧的审美风尚熏陶出来的读者,又要面对鱼龙混杂,是非莫辩的诗坛,而后者常常淹没了这时代真正的东西,使天才们寂寞一生。例如:一种由观念更新所达到的“深刻”,与一种个人心灵历史积淀并由生命本身呈现出来的深刻是有本质区别的,而前者往往善于“寻找”一种最时髦的“自我”,例如,西尔维亚?普拉斯式的自我或庄子老子们的自我而盅惑诗坛。而后者却常常由于诗人自己的自在与自信因而淡泊于名利而被价值尺度至今仍然非常浅薄势利的诗坛所忽略。
但无论如何,这时代深处那些真正的东西必定要凸现出来,进而影响、改变一整代人的思想观念,审美风尚和生活方式。诗作为人类精神最敏锐的触角,它当然会最先把新时代的精神透露出来。在对当代诗坛的大量作品,包括被称为“实验诗”、“新诗潮”、“第三代人”以及一些“朦胧”诗人的作品进行研究之后,我可以说:中国当代诗歌,虽然一度受到评论家们的冷落,但它仍然为文学史所证明的那样,在一切文学样式中走得最远,达到的最深刻,具有真正的先锋精神。
当代诗歌已经可以见到这样一些作品,它们体现出一种开放的,实在的、坦率真诚、客观冷静、亲切朴素、心平气和,通晓大度与人的生命,人的内心历程,人的生存壮志息息相通的精神。
诗人们意识到,诗歌精神已经不在那些英雄式的传奇冒险,史诗般的人生阅历,流血争斗之中。诗歌已经达到那片隐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底下的个人心灵的大海。诗人们自觉到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内心历程的探险开始了。诗人们终于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体验。哪怕它是压抑的,卑俗的甚或变态的。个人生命不再躲在人格面具之后,它裸露在世界面前,和千千万万的生命相见。这时诗人依托的是个人生命的实在,由此他感到实在和自信,由此他能够客观、冷静地把握世界以及他自己――他的生命,他的意识,他的内心状态都作为审美对象。一首诗就是一次生命的体验,一首诗就是一个活的灵魂,一首诗就是一次生命的具象。
在传统诗歌中,诗人注重的是个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生的关系和社会、政治生活、伦理道德的关系。诗人吟风弄月、笑傲山水、感叹人生、批判社会、讥刺时弊,诗人努力将个人生命的真相掩饰起来,以求和那种符合公共价值标准的人格面具统一起来。诗人们或忧国惑民,或风流倜傥,煌煌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何曾有过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又何曾有过一部惠特曼式的自己之歌?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生命的压抑、束缚,使中国人的生命变得如此虚伪,如此之丑,以及当诗人们终于敢于正视自己内心真相时,他不得不写着“丑的”“非诗”的诗。当代诗人拒绝再与那些少得可怜的所谓高尚的人格面具认同,拒绝凭借那些在传统观念上所谓“美好的东西”来掩饰个人生存状态的真相的自觉,使他们在新诗兴起七十年后,终于开始从本质上与传统决裂。如果中国已持续十年的改革,最初几年还只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显示巨大影响的话,那么诗歌中这种个人内心生活向世界的开放,恰恰预示出我们时代开放求实的伟大改革,已经进入到更深的层次。个人生命的自觉,是西方文学早已丧失的大陆,而中国,千年来这块大陆是封闭的。而今天,中国诗歌对这片大陆的探险已经开始。
这些诗歌看起来似乎是:自虐的、反讽的、黑色幽默式的、陌生化的。这种结果与其说是诗人们故意为之,是一种写诗原则不如说它是个人生命的自觉与传统人格面具、审美习性相冲突的结果。中国传统诗歌的审美风尚强大到这种强度,以至只要诗人照相式地描述一下内心生活的真相。就使诗人被人们视为最具有先锋意识的现代派。
在这些诗歌中,我看到一种冷静、客观、心平气和,局外人式的创作态度。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他是读者的朋友,他充分信任读者的人生经验、判断力、审美力。他不指令,他只是表现自己生命最真实的体验。这些诗歌表面上看来是冷漠的,非抒情的、毫无意义的,然而它在那些好的读者看来,却是有生命的,有意味的,它的客观性使读者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呈现一种多义的审美效果。
这些诗使诗再次回到语言本身。它不是某种意义的载体。它是一种流动的语感。使读者可以像体验生命一样体验它的存在。这些诗歌是整体的、组合的、生命式地,一成流动的语感。它不可分割,也无法破译,如果你除了它本身,仍然感受不到什么的话。在传统诗歌中,一些句子是另一些句子的仆役,人们因而得以编《名句选》一类的东西。这些诗以一种同时代人最熟悉、最亲切的语言和读者交谈,大巧若拙,平淡无奇而韵味深远。它的韵律是自由、平实的、交心似的,它和诗人内心的节奏息息相通。在这些诗歌中,语言的领域被扩大了,尤其是“非诗”的领域。诗人决不偏爱或者拒绝某一种语言方式,他是自由的,一切决定于个人生命的体验。
如果在个人生命自觉这一点上,这些诗歌完全偏离了传统的话,那么在审美趣味上,这些诗人似乎对中国古典中那些优美的东西,例如:大巧若拙,平淡中见深远,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贲象穷白,贵乎反本等显示出浓厚的兴趣。
当代诗歌中这些现象,我并不认为就完全代表着我们时代的诗歌精神。它们或许只是未来精神的一些部分,一些苗头,一些抛砖引玉的东西,甚至于它们根本不是。但我为这些诗歌那种冷静客观,坦率实在的精神所打动。我相信我们当代诗坛需要这种精神。
已经有许多评论家注意到诗歌上的这种现象。由于这种现象夹杂在众多的诗歌泡沫中,因此这些诗人大多数是默默无闻的。但我还是愿意建议读者参考一下这些书籍和刊物。例如:《当代实验诗选》、《新诗潮诗选》、《探索诗选》以及1986年以来的《诗刊》、《诗歌报》和已经停刊的《中国》。
我最后要提醒人们注意一下这些诗人中大多数人的生存背景,即:他们往往缺乏传奇式的人生阅历,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过去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局外人。十年动乱那种无法无天的气氛,使他们惯于漠视权威。这些人由于置身于普通人平淡无奇的生活,由于长期被忽视,而变得心平气和,耽于内心生活。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歌精神。
一些时代,诗只为自己时代所用。
另一些时代,它的诗歌以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穿透于一个又一个的世纪。
“神的巨大的威权是在柔和的微风里,而不在狂风暴雨之中。”
“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就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泰戈尔《飞鸟集》)1988年春天于云南西部边境关于未来的神话
在云南某小镇的一面土墙上,刷着这样一条标语“轻视过去迷信未来做彻底的革命者”。这条标语可以肯定是写于二十世纪的五十或六十年代,已经有些模糊,土墙周围是牛屎、干草堆和牲口。作者或写标语的人已经杳无踪迹,这可能是某位乡村知识分子领悟了时代精神创造的作品,不像是规定的口号。这样的思想,能够如此清楚、如此准确地表达,并出现在远离中国文化中心的云南高原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偏僻小镇,说明这种思想在中国已经是多么深入人心,多么地影响普遍。
我以为要把握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核心,根本不用去读多少书,研究多少历史,知道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个环境中有这么一条标语就够了。
如果摧毁过去是具体的行动,那么迷信未来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精神支柱,一个永远不能证伪的神话。未来已经成了一个总是可以“更某某”,总是背着一个装得满满的口袋的魔术师。它从那只口袋里拿出任何东西来都不会遭到怀疑,却立即被迷信,并且成为摧毁旧世界的新籍口、成为最正当的理由。回忆一下,这个未来的袋子拿出来的任何东西,我们怀疑过什么?包括最近刚刚拿出来的“网络世界”。我们总是立即欢呼,马上抛弃,全身心投入,“面向未来,拥抱新事物”。
人们再也不相信永恒。再也不相信那些不变的事物。乡村依然是不动的,但这不动并不是由于它代表着未来,而是因为它落后。一个在路上的世纪。在路上,当然是民族活力的表现,但可怕的是,路已经被理解为只有一个方向。凯鲁雅克们的“在路上”是没有方向的,它重视的是存在的重新被感受到。而“在路上”在中国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未来”,即使这个未来已经遮蔽着存在本身,人们依然义无反顾,那是一个永远的神话。对过去经验世界的轻视,具体到个人,似乎仅仅是一次次的搬新家,而最终被抛弃的东西,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些住处,而是故乡。“去终古之所居”。
未来是无法证伪的。因为它一旦到来,立即过时。“生活在别处”,未来只存在于想象中,它助长了中国诗歌的一种现代美学,这种美学的特征是诗意化,其全部功能就是对未来的升华式的想象,彼岸、远方……未来是一个永不具象的东西,因此现代美学通常是一种比赛想象力的美学,象征、隐喻。这种美学的庸俗在于,它总是从生命的庸俗类比方面去想象未来,例如它必然是某种“春天”的东西、向上的、蓬勃的、明亮的、越来越高大的、“更某某的”。在这里未来其实已经被先验地设定为某种东西,这种设定恰恰与未来一词的含义是矛盾的。而且这种设定其实是来自对经验和历史的价值判断。未来的意思如果是“各种可能性”,那么关于秋天和死亡的各种象征为何从来不被纳入现代美学的想象系统中去呢?未来主义是没有最后的,它没有昔日世界所恐惧的“永恒”“千年审判”。它就是最后。它就是最后的审判。一个永远在前进的“最后”。时问的鞭子抽赶的苦役犯,就像西绪弗斯,永远在推那个叫做未来的大石头,刚刚到达未来的山顶,又滚下来了。永不到来的戈多。而人们总是在恐惧“过时”。后怕,害怕后面,后面已经被全面地宣判了死刑。最古老的后面是什么,大地。而人们的口号是改天换地。